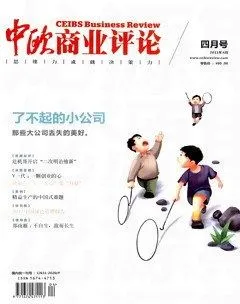笃信价格=刻舟求剑
有的经济学家只用模型,不问条件;有的经济学家只顾效率,不讲公平;有的经济学家只看货币,不谈感知。但在行政垄断的有限供给这一特殊国情之下,如此笃信价格,不是刻舟求剑吗?
早已习惯了经济学家呼吁价格浮动,顶着千夫所指为民众普及价格理论。而针对前不久刚结束的春运买票难问题,部分经济学家更是大力主张以铁路票价、公路票价自由上涨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认为,限价会造成供不应求,“黄牛党”或依靠出售“权力”牟利的腐败分子所牟之利都会附加在商品价格上。那些与“黄牛党”和腐败分子的交易也会产生附加在商品价格上的交易成本。总之,这两部分额外的成本,最终都会成为购买者的负担和国家的损失(溢价本来应该由国家赚),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如让价格自由浮动,让购买者以货币竞价,愿意出高价的,证明他们的确需要;不愿意出高价的,证明他们还可以忍受。如此一来,“黄牛党”和腐败分子们没有了生存空间,溢价可以由国家收回;此外,买不到票的消费者受此激励,会以原本用于竞价的精力多挣钱,使自己能够负担高价车票。春运一票难求、公路拥堵不堪的局面也就能顺利解决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经济学家对科学主义的坚持碰上民众对人文关怀的渴望,自然是火花四溅,但吵了一轮又一轮,却好比贝利和乔丹赛球,场面热闹,但频道不对,是非难分。
两个天真的臆想
经济学家相当一部分关于价格浮动的观点笔者是赞成的,但是,对于想在行政垄断的有限供给下使用市场定价的天真臆想,本人却难以苟同。
经济学家的第一个臆想认为,付给“黄牛党”和腐败分子的溢价无意义,如果单纯主张这部分溢价由国家收回,没有问题。毕竟对于消费者来说,只是转移了支付对象,并没有损失。但如果消费者只是以自己的体力和坚持参与竟价呢,比如春运熬夜排队买票?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并没有求助“黄牛党”和腐败分子。此时,涨价就会转移他们的财富。
诚然,倘若市场中竞争充分,替代品充足,不买这家的火车票可以买那家的,只要商家没有合谋,均衡价格自然足够低。即使有高价,也是因为商家创造了足够吸引消费者的“租(rent)”,这也就是消费者肯花十几万买个爱马仕的原因。但在单寡头市场上,“铁老大”、“公路老大”们凭什么转移大家的财富,就因为身上有个“国”字号么?
第二个臆想是:竞价行为无意义,不如把原本用于竞价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工作中,用多赚到的钱去购买高价商品。首先需要厘清两种竞价行为。如果说求助于“黄牛党”和腐败分子的竞价行为毫无意义,那么依靠自己的体力和坚持进行的竞价,却可以立即变现。这个以春运铁路票价为例再清楚不过。倘若真的等到农民工用排队的时间和精力赚到“足够”的钱,恐怕早就赶不上春节回乡的列车了。
其次,即使用竞价的精力服务社会,也要考虑其变现的可能性。依靠体力和坚持的竞价者,大多都是怀揣梦想,埋头苦干的人。他们缺乏财富主要是受到环境和际遇的限制,而不是因为不努力。另外,他们在明明知道即便通宵排队也不一定能买上票(即多次“试错”)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排队”竞价,而不是把所谓竞价精力用于赚钱,其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前者更加划算。经济学家主张农民工用竞价所使用的时间去赚高价所需的财富,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效率≠公平,等价≠“等效”
笔者承认,由于总供给不变,放开价格后,没买到商品的人数的确不会增加。但经济学家的观点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谁应该买到商品?提倡货币竞价,本意是激励人们更多地创造财富,通过良性竞争获得更好的生活,是~种效率的价值目标。而用到这里的意思是谁在过去更努力,谁就会在现在获得更大的回报,这种价值观本来也是被现有社会所认可的。
但我们要考虑贫富差距的成因。如果贫富差距是因为穷人不努力,那么他们理应受到制度的惩罚,活该买不到商品。但倘若是由于环境和际遇呢?譬如,一个城市的孩子和一个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难道在其成长过程中,机会都是均等的吗?在不公平的机会下,以不公平的结果来分配刚性消费品,不是二度的结果不公平又是什么?
与其如此,不如将此类刚性商品的竞价限定在一个范围内——打造专有的结果公平。首先,赋予其特殊的机会公平意义,即限定低价,允许消费者以同样的体力和坚持竞价,这等于重新拉平了起点;其次,保障程序公平,限定大家都只能以这种形式参与竞价,而非通过“黄牛党”和腐败分子。当然,我也认同张五常教授的观点,“限价后,富人总能买到好东西。”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此时通过限价传递倡导公平的信号,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
笔者也承认,也许消费者付出中介成本和交易成本后的总价,与商品价格自由上涨后无异(甚至更高),但经济上的“等价”绝不等于管理上的“等效”。假设学校的学生有贫富两类,对富人收费10000元,对穷人收费7000元。收费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告诉学生学费是7000元,但富人多收3000元;另一种是告诉学生学费是10000元,但穷人少收3000元。两者经济上“等价”,但结果上绝不“等效”,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限价的确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但在消费者的感知上,却不一定会计量体力和时间这部分成本。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消费者至少是获得了形式上参与竞价的公平机会,这样一来,竞价失败时他们大多数会进行相对积极的外部归因和内部归因,而不会完全埋怨制度,而他们也会始终保有一份对于未来的希望。而这,似乎也是有限供给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于刚性产品,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放开行政垄断,增加供给,再让价格自由浮动,只有这样,民众才能买到质优价廉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