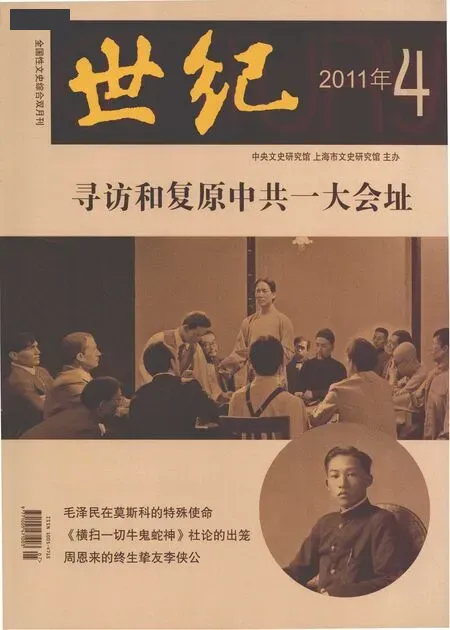当代“列传”
■ 过传忠
拜读了陈四益先生在《世纪》连续发表的两篇《笑谈》,欣赏之余,勾起了颇多的联想。
两篇文章,一篇谈“成份”,一篇谈分配,都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题目。然而,陈文与众不同的是:内容首先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真实可信毫不虚构;同时,在叙的基础上不断穿插议论,从丰富的多年积累中抽取出相关的史实、世态、文件甚至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夹叙夹议,史论结合,不仅把问题谈得透彻、深刻,而且使读者感到真切有趣。希望“笑谈”能继续写下去,作为杂文与回忆录结合的一个新品种,当是会受欢迎的。
如今回忆录铺天盖地,有自撰的,有口述后别人整理的,也有经采访或由相关资料中提取内容另行“创作”的。只要不杜撰歪曲,不增删文饰,作为历史和社会这大海中的一滴,总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是,真正好的回忆录,则必须在真实之外,更要写出些特色,写出些独特感人的东西。
近日从上海市文联主办的刊物《海风》上读到有关著名翻译家、学者王智量先生的回忆文章。这里仅向大家介绍文中提及的一个小小细节——
1958年的5月,就在已划为右派的王要被送往山区改造的前一天中午,他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碰到”了何其芳。他回忆道:
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看他,可是我忽然感觉到,他一定是何其芳!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可是我不敢。他是所长,是所里的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我动也不敢动,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而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走掉……
让王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何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我国还没有理想的译本,而30岁还不到的王却能用俄语背诵其中的诗句。了解这一点后,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就鼓励他把书译出来。谁知只译了60多节,大难临头,他被定为右派,译书当然无从谈起了。没想到在厕所里,而且似乎是特地有意地所长仍关照他译书。何其芳的这句话影响了他一辈子。王先生日后当然译出了这部名著,但我觉得,从回忆录的写作来说,这样的精彩片段真是会给人的心灵以震撼的力量。关于正直、善良、勇敢,关于人性的复杂,关于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带规律性的揭示……小小的篇幅值得挖掘的东西太多了。
不由得想起了《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为什么至今仍是众望所归的楷模?前辈专家王伯祥先生在《史记选》的“序例”中说:“这书的内容丰富灿烂,生动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会的复杂生活”,使它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莫大的影响”。《史记》这方面的成就,集中地体现在70篇“列传”中,不论是描写各个人物生活的“专传”,将彼此有关人物多人合述的“合传”,还是把“以类相从”的人物归并在一起的“类传”,都刻划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的还成为戏曲剧本的重要素材。
在我看来,陈四益、王智量先生的回忆文字就大有“列传”的风范,只是所包含的议论已超过太史公的“论赞”,展开得更加充分。不单是陈、王,其他如画家贺友直的《生活记趣》,甚至前些年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以及韦君宜先生的回忆文章,都可以视为当代的“列传”。
对于现、当代史,尤其是涉及到比较复杂、敏感的某些部分,人们的写作与研究总有些举步维艰。其实,可以不忙完成“本纪”、“世家”,“表”、“书”也要逐渐积累,倒是“列传”,普通老百姓、广大群众的生活,可以先收集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基础。当然,必须同虚构的文学创作区分开,那是自不待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