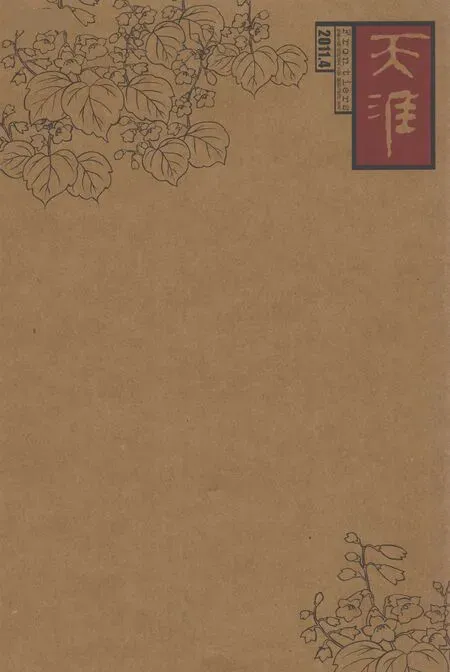奶妈(外三首)
□杨键
奶妈(外三首)
□杨键
母亲回忆起五十年代她在芜湖做奶妈的事情,
她说,在赭山
当她登上振风塔,看见
整个城市如同一片荷叶浮在水面。
她因第一个女儿不幸夭折,
被城里的一位母亲请来做奶妈。
孩子两年后断奶,
母亲回到老家。
两天后,这位城里的母亲
带着儿子火速赶到我母亲那里,
大哭不止的孩子紧紧搂住我母亲的脖子,
他紧紧搂住的小手引起母亲内心长久的悸动。
现在,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悸动一直在她心里,
她讲给我听,却并不知道
这是一切优秀文学的源头。
夕光
小时候,我在大堤上奔跑的时候见过江水上
渐渐西沉的落日,
长大后我才知葬身于它
又有何妨?
葬身,这大概就是我幸福的源头了。
当然,灵魂也可以细腻地存在,
比如墙头上枯草丛中的一只古瓮,
灵魂靠瓮盖上的一眼小孔,
靠暮晚时分的一缕夕光,
存活下来。
老柳树
归来的女儿看见父母的背驼得跟家乡的河流
平行,她在心里喊:
“谁来救我爸爸?谁来救我妈妈?
谁来救我的父老乡亲?”
“你啊,老柳树,你要来救他们,你要将他们的柔韧
救出来,你要毫不留情地动摇他们的软弱,压抑。”
石灰坑边站着四个戴着白口罩默不作声的村民,
坑上的布谷鸟越飞越远,越飞越远,要救走他们。
孤寒、贫瘠
这样孤寒、贫瘠的画面是否是暂时的呢?
一个穿黑棉袄的老妇人在田里弯着腰,
一条大黑狗在她晾晒的破棉絮下大喊大叫。
我只是看见她的孤寒没有看见她的灵魂。
我只是听见她家黑狗的叫声,
而没有看见这条黑狗的灵魂。
我只是记录了它的叫声,
而没有记录它的灵魂。
我的祖先发明语言不是为了鞭挞,
而我偏偏用它来鞭挞。
白天,我虽有眼睛,但等于瞎子,
夜里,当我睡去,祖先在我梦里啜泣。
用他们为我们建造
而我们将它废弃的文庙,
用他们为我们栽种
而我们不再仰望的古柏。
这样孤寒、贫瘠的画面是否是暂时的呢?
一个穿黑棉袄的老妇人在田里弯着腰,
一条大黑狗在她晾晒的破棉絮下大喊大叫。
我只是看见她的贫瘠没有看见她的灵魂。
杨键,现居安徽马鞍山。
——我是如何演绎《北京人》中的陈奶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