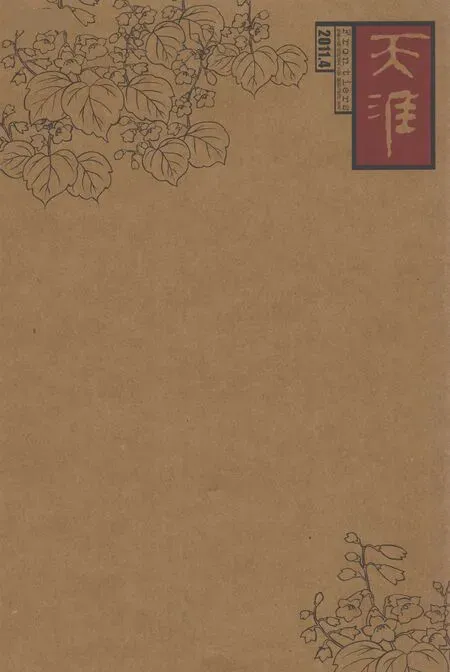遗失的眼睛
陈年
遗失的眼睛
陈年
一
那些温暖的春天,草芽儿悄悄地张开眼,探头探脑,看着我们。
甜甜的甘草活了,像细麻绳一样的根藏在深土里,要用铁锹、铁铲等大工具来挖。挖甘草根不仅是个力气活,还要胆量,传说甘草根是死人头发长成的,所以挖甘草根是男孩的专利,他们在四月里拎着尖锹,成群结队地忙碌在荒山野坡。小女孩怕鬼,不敢跟着去挖,就在小路上等那些英雄的男孩。黄昏时,金子一样的夕阳下,男孩子们拖着一地金色,腰里缠着几匝甘草根,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威风凛凛地从街上走过。谁的甘草多,谁的甘草根粗壮,谁的身后就会跟着听话乖巧的小女孩。
我和兰用尖石头块挖一种叫麻麻草的根,这是春天最早钻出土的能吃的草。麻麻草的叶子紧紧地贴在地面上,要一点点小心地掘,才能挖出整根的草。兰儿手里握着尖石头,先把麻麻草周围的土刨松了,再用尖一点的石头往深挖。我两只手使劲地往外刨土,边刨边喊,快了,快了,就差一点了,再使点劲儿。草根乳白色,细细的,和老鼠的尾巴一样。吃到嘴里微微有一丝苦,过后就是麻丝丝的滋味。我现在也不知这种草有没有毒,但那时是我们的美食。
兰的父亲是井下一线的工人,有国家补贴的干粮证,能领到月饼、面包、花生等稀罕吃食。我们下学后,常去她父亲下班路上等人。兰的父亲很丑,脸上有很大的一块煤斑。听大人们讲,那些黑斑是因为煤粉嵌进了破损的皮肉里。我很怀疑这些说法,长大后,知道了纹身刺青,才明白煤斑是煤矿工人另一种永恒的纹刺。我管兰儿的父亲叫大爷,从大爷的手里我分到一小把花生豆,或是一块油汪汪的月饼。淡粉的花生衣被油浸出一种深红,上面沾着几颗细小的盐粒。不舍得一下子吃光,先含在嘴里吮干净盐味,再嚼着吃,仍香得让人喘不上气。月饼用一张干净的纸包上,只一会儿,油浸透了纸,纸片变得又薄又亮,隔着纸,麻油味儿直钻鼻子。
五月槐花开,一串串槐花挂在绿叶间,整个矿区都浸在花香里。我们闻不到花香,我们知道又有可吃的东西了。我们把槐花叫作白花,男孩子爬上树吃,女孩子在树下拣落花吃。槐花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吃在嘴里寡淡淡的,大把大把地嚼,才能嚼出一点甜味。
那天我和兰儿把拣来的花,一朵朵地放进嘴巴里,等攒多了大口大口地嚼。阳光从树叶滤过,闭一下眼,眼前浮起一段红色的膜。这时兰的哥哥哭着跑来,兰的父亲在井下被支柱砸死了。兰嘴巴里塞满了黄白的槐花,大张着嘴半天哭不出声来。
后来我常梦到兰的父亲把一把红皮的花生放在我的手心,憨憨地笑着。母亲说梦到死人赶紧唾三口,鬼就缠不上身。我怕鬼,但我不怕大爷,我爱吃他手里的花生豆、月饼。
六月野地里有了乔瓜瓜、马茹茹。七月有了野杏野桃。八月地里能吃的东西都熟了。孩子们忙着烤玉米、烧山药、啃甜杆……吃是我们最快乐的话题,草可以吃,花可以吃,鸟可以吃,虫可以吃。
生活所迫,兰没有读完初中,十五岁时缀学,成了女矿工,每天穿着窑衣在选煤楼拣矸石。我下学时,看到兰黑脸黑手黑衣走进矿上的公共浴室。兰不和我说话,低着头一闪而过。
岁月烟一样地散开,我趴在刚刚泛绿的田野里,手里轻轻拔着一根青草根,嘴里念着一个咒语,鸡蛋青,鸡蛋黄出来哇!草黄白相间的嫩芽,一点点从土里露出来,像是一双孩子的眼睛,惺惺然茫然四顾。已是成人的我,在草冷漠的眼神里涕泪横流。曾经那些青涩的日子和萌动的草芽一样,打碎我煤乡所有的记忆。
二
煤是有眼睛的,它躲在黑暗中终年沉默着,它忧郁的眼神,忽然散在白亮亮的太阳光下,可以灼伤每一个矿区长大的孩子。
临时户区建在矸石场附近,高高低低的石头屋沿着矸石场慢慢伸进山里。简易的小铁轨从临时户区穿过,也穿过我们的生活。
临时户区的男孩女孩都有一个拣炭的铁丝筐,扁圆或是椭圆。假日里我们背着或挎着小筐,沿着铁轨,走进离家不远的矸石场。煤矸石是煤的副产品,和煤一起被开采出来,经过选煤楼女工的手,作为废弃物倾倒在矸石场。在煤矸石里总是多多少少混些煤块,孩子们用铁丝爪子不停地翻拣着大块的石头,希望能找到大的炭块。可矸子里的大炭很少,即使有也被大人们拣走了。我们只能拣一些碎煤籽。混在矸子里的煤籽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刺眼的白亮,而是乌亮,就像一双双黑黑的眼睛散在石头缝里。数不清的黑眼睛悄悄地眨着眼,那种眼神黑得看不见人的手指。我们把碎碎的煤籽拣进筐里,黑亮亮的眼睛挤在一起,清澈冷洌。手不停地动,黑和亮一层一层地垒起来,垒成一个小馒头山。垒起来的还有我们的心事,属于孩子的心事,不让大人看见的心事。孩子们懂事的眼睛躲闪着大人询问的目光,把无忧无虑的笑容给他们。
籽煤生火最快,哗地一锹进去,就是一团红烈的火。冬夜里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烤火,手背上皴裂的血口子丝丝地冒着血。母亲取出一个小玻璃瓶子,从里面抠一块机器用的工业黄油,细细抹在孩子的手背上,然后靠近火炉边烤。不一会儿,手背烤得通红,黄油的油脂也慢慢地渗入肉皮里,钻心地疼。不声不响,火光在手指间跳跃,静静地在疼痛中感受自己的身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孩子们总是喜欢说虚岁,似乎这样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
作为表扬,孩子拣回来的炭块,母亲总是独自堆一个小堆,一进院门,就能醒目地看到。对于母亲无声的夸奖,孩子们更加勤奋地做事,这种勤奋落在心里有一种成长的厚重。我们稚嫩的双肩正一点点接过父亲母亲沉重的生活担子。
没有倒矸石的铁牛车时,我们沿着铁轨踩道木玩。丁、剪、包,猜大小定输赢。输家往后退一根道木,赢家往前迈一根道木。手指藏在衣服的后面,变换着我们小小的心机。退一步,进一步,我们用手势决定着位置。那时我们还不懂命运的沉重,还不懂输赢背后的玄机。亮亮的铁轨上反射太阳的光,刺得人张不开眼。
我和军愉快地做着游戏,为手伸出的快慢争吵打闹。我出包,他出丁。他输了退一步,我进一步。那挂铁牛车藏在军的身后,幽灵一样地行走。军的尖叫闪电一样地划过天空,在闪电下我看到军的一只脚一只胳膊落在道木边让人恐惧地跳动。
夜里,倾倒煤矸石的铁牛车沿着简易铁轨轰轰地驶进孩子的梦,孩子愉快地做着藏猫猫的游戏。
在梦里他们遇不到煤黑幽幽的眼睛。
三
我看不懂父亲的眼睛。他默默地出门进门,上班下班,挑水劈柴,干着家里所有的重体力活。和临时户区所有的父亲一样,我们的关系是冷漠的、生硬的,甚至于陌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语言。如果哪天我们有了肢体接触,那一定是父亲的脚。父亲打孩子时,一律用脚踢屁股。
我小心地做事,小心地说话,小心地躲开跟在自己身后的眼睛。并不是怕肉体的疼痛,而是内心的一种羞耻,约束着自己不去犯错。
母亲总是对我说,别忘了你的身份。这句话鞭子一样抽着我的心,时时提醒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我没有城镇户口。老师在计学生户籍时,总要让没有矿区户口的同学站起来。我和少数同学羞怯地低着头,让老师记下名字。
少年的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自己在矿上生活了十几年,却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矿上人说我们是农村人。而在遥远的乡下,我们是已经出去享福的矿工家属。我们没有参加过村里的劳动,我们也不能无耻地享受村里的福利。我们不是农村人,我们只是一群寄存在乡下户籍上的名字。
在矿上,户口房子工作,都不属于我们。矿上任何的福利都没有我们的份。已经是初中生,班里不喜欢学习的男生,大声叫着“大不了老子以后当个窑黑子”。而临时户区的孩子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这样叫的,因为我们连下井的权利都没有。
我们的名字登记在临时户籍里,我们的房子作为违章建筑建在倾倒矸石的荒山坡上,我们是矿上的多余人。我们必须自觉地躲开所有的福利。
想起临时户这个卑微的身份,总是想起润子哥悲伤的眼神。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考学是临时户区孩子的唯一出路,但矿上不让临时户的孩子参加矿区的升学考试,他们必须回到原籍报名考试。农村的孩子不能挤占了矿上孩子的指标。生活在矿区,而没有一个属于你的身份,内心是羞愧不安的,好像是在做贼,偷的不是东西,而是偷了别人的生活。既然这样,人家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甚至会处罚这个“贼”。老师对于没有户口的学生从来没有好脸色,成绩好也不行。因为再好的成绩不能归于矿区。
润子每年夏天都要回乡下参加中考,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去,又把失望带给整个夏天。到开学的时候,他父亲就忙着找补习的学校。他不想他唯一的儿子回到乡下做一个辛苦的农民。那就只能是一年年的复读。五年,整整五年,润子读同样的课本,做同样的习题,已经没有学习的快乐和兴趣,只为一个可以在矿上生活的户口。
后来,又有一个政策,如果父亲退休后把户口开回乡下,那么他的儿子就可以接班成为一个煤矿工人。润子就这样艰难地成为一个矿工,润子当工人后,对我说,我爹当了一辈子工人,为了我又回到农村。他说,他一定要找一个有户口的姑娘做媳妇,要不就对不起他爹。我转身离开,因为临时户的身份没有权利爱自己喜欢的人。没有户口,我连做一个矿工妻子的权利都没有。
我后来的工作是净化生活污水,生活区所有的脏水归集到我所在的单位,用药物处理沉淀过滤后,再排入十里河。化验室里晶亮的玻璃器皿,粉红的化学药水,一排排先进的仪器,在干净和明亮中我总是想起父亲那双眼睛。很多的时候我坐在高高的曝气池上看蓝蓝的天,我总觉得天上有一双眼睛看着我。它忧郁的眼神让我不敢和它对视。
四
矿区最长的路是铁轨,拉煤的火车沿着这条路开进来开出去。火车的嗓门很大,喊一声,地动山摇。火车的力气也大,一长串车皮轻轻松松地拉着就走。我们一直奇怪火车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火车停在铁轨上时,一般都在等着装煤。我们欣喜地看着火车,争论一番人坐在火车皮里带不带小板凳的问题后,数火车皮玩,数到十再重头来数。那个年纪只认得这么多数。报名上学,学校的老师也就让孩子扳着指头数十个数字。
矿上真正坐过火车的孩子没有,坐火车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我们把火车叫作铁龙,龙是一个神物。在孩子中一直传唱着一个开火车的谣:开哎,开哎,开火车,一矿火车也要开,往哪开?五矿开。五矿火车也要开,往哪开?八矿开。
星期天,母亲会带着孩子们沿铁轨去另一个煤矿逛街,虽然同样是煤矿,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新鲜的。商店似乎要大些,东西也全点,人也多点。小孩子们还发现,在那个煤矿,铁轨也是最长的路。
没有火车时,铁轨是沉默的。那种沉默很亮,明晃晃如同灯盏。我们收藏着那些亮,在内心深处,那些亮就是我们的理想之灯。每一个孩子都装着一个出走的梦,那个梦沿着铁轨到达一个遥远的城市。
表姐和所有矿山女孩子一样,梳着两条长长的发辫,在选煤楼做一份临时工。工休时去一次矿务局,最远的地方就是大同城,买回晴纶秋衣尼龙袜子小面镜面友油便宜的香粉还有悄悄藏起来的裹胸。直至有一天,表姐成为一个矿工的妻子。爱情在当时的矿上是一个奢侈的词,只要双方大人没有意见,那么两个孩子也就没有意见。表姐的婚礼请了很多的人,八大件都摆上桌了,两个新人还没有露面。我的肚子饿,偷着出去找吃的,听到表姐他们在争吵,表姐一直在哭。回家后我对母亲说,表姐是不幸福的。虽然我还不懂女人的幸福是什么,但我当时是这样对母亲说的。
果然,表姐失踪了。表姐失踪后,那个男人总是到舅舅家找茬,他说,是舅舅把人藏起来了。大概是两年后,邻居家糊顶棚,看到旧报上一则寻尸启事,觉得有点像表姐。舅舅到铁路的公安处认尸,尸体早没了,只留下一串家门钥匙,用钥匙开门才知道表姐已经死了。表姐是卧在铁轨死的,她一定是想沿着这条神秘的路走到一个更遥远的地方。那里鲜花盛开,爱情甜蜜。
我沿着铁路疯狂地奔跑时,总是想起表姐的眼睛。她是眼睁睁地看着铁轨上的火车一点点逼近,还是闭着眼,心中默默地数着枕木的根数?
那时矿务局一中每年要从矿上招生,我和春发誓一定要考上局一中,我们数着枕木,说着自己的心事。不知是谁说如果不能考中那么就去死。现在想起这句话,还是冷的感觉。太渴望离开偏僻落后的矿山,没有命运的火车,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自己的火车头,用生命做一个赌注。
十七岁以后,我一直想着离开,我以为离开是我改变矿工命运的唯一方式,我沿着铁轨一次一次出走,又一次次失败而回。终于,还是做了一个女矿工。然后下岗,最后是真正地离开。
后来我用时间、金钱、学识,还有心情,准备着城市的日子。我认为一些轰轰烈烈的动作会改变命运中的一切。而其实无论是离开还是停下,都逃不出思想的宿命。命中注定。
有一些记忆根深蒂固,它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谁在说,“来,让我们唱开火车的歌谣。”我把脸埋起来,小声哭泣。
五
我相信房子是有生命的。门是它的嘴巴,窗子是它的眼睛,四堵墙是它结实的身子板。
父亲在他做矿工的日子里,不停地造屋,他以为只要他把房子建好了,他的儿女就能成了正当的矿山人。在我们居住的那个矿,父亲一共盖了三处房子。南山、北山、五九路东。这三处院落耗尽了他的心血,也代表了父亲的青年、壮年、中年。
南山的房子是父亲结婚时匆匆盖起的小南房,只有一间,又阴又冷。所以当父亲有一点经济实力后在北山的荒山坡上又盖起他的第二座房子,那一年正好赶上我出生。同样是手头紧,房子盖得挤挤巴巴的。第三次盖房时,我八岁,已经能帮着家里做活了。我记着父亲光着脊背采石头,也记着母亲挥锹铲土,还记着搬动石头块时,手指放在棱角分明的石头上钻心地疼。那些手指上的皮磨得又薄又亮,能看到里面蓝色的血管。夜里涨疼得难受,把手摊开,静静地贴在水泥墙上凉一会,然后睡去。不记得哭过,无论是被石头割开了皮肉,还是被扁担压肿了肩。沉默的有力量的父亲教给他的孩子们,坚忍是生活唯一的出路。
房子是父亲最得意的儿子,他亲手造了它们的骨它们的肉它们的精气神。父亲对那些房子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哪年盖了哪座房子,现在那房子谁住着,以前住过谁,在哪个房子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大事,都是一些零七碎八的小事,比方哪年在那座房子里添了锅,哪年添了桶,甚至孩子的一件新衣服也是历史。
我十七岁离开矿上,到外面工作,在城里人不屑的目光里,才知道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叫贫民窟。
走在首都繁华的大街,才知道煤矿工人是一个卑微的身份。
当“棚户区”这个新名词出现在矿区人嘴里时,临时户区作为改造重点工程开始被社会重视起来,电视新闻的镜头第一次伸进底层矿工的生活。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屋子里住着人,我把新闻换一个台,泪不知不觉流下来,谁能懂得,谁又能懂我们对临时户区的感情?
临时户区就像贫穷的母亲,她把最甘甜的乳汁给了那些孩子,从此以后它只是蓝天上的一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东奔西走的儿女们。
临时户区的消失,不仅仅是房子的消失,还有二代矿区人回忆的消失。多少年后,我拿着照片会对我的孩子说什么?说他的母亲在这座房子里出生长大,说我们曾经的欢乐痛苦疼痛,说那座小院里长着美丽高大的向日葵。可他们能看懂那道美丽的风景吗?
陈年,作家,现居山西大同。已发表小说《胭脂杏》、《生息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