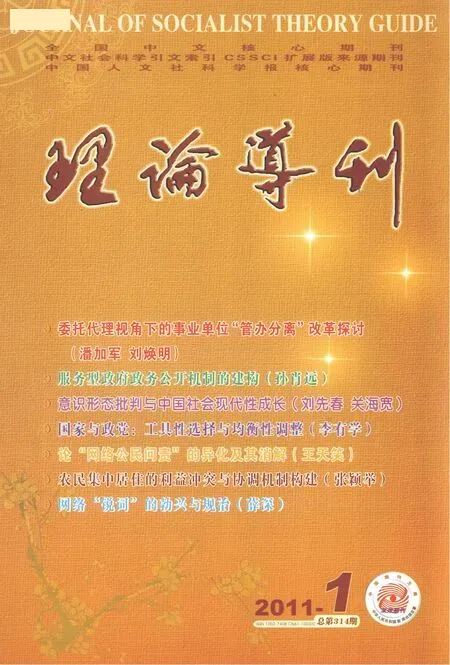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唐 兵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330031)
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唐 兵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330031)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并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灵活性,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并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提高治理效率。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构建的两条途径。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信任;信任机制
一、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概念释义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资源是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即它一旦被提供,便有众多的消费者共同对其进行消费,很难将其中的任何人排斥在外。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资源存量的有限性,一旦对该资源的消费程度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范围,便会诱发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公共资源因被过度消费而陷入耗竭性退化的“公地悲剧”。[1]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共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与优化配置,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中,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市场机制治理,主张公共资源产权私有化,将“市场”作为公共资源问题的解决方案。如罗伯特·史密斯认为,“无论是对公共财产资源所做的经济分析还是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论述,都说明在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问题上避免公共池塘资源悲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创立一种私有财产权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制度。”[2]另一种是政府科层制治理,强调在公共资源治理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角色出现。这是“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环境问题无法通过合作解决……所以具有加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它也只有在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才能做到”。[3]但是这两种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都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失灵:公共资源治理中逃避责任、机会主义以及“搭便车”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之下,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关注。
所谓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并在这一网络中,通过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及时的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换,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从定义中可以看出,首先,公共资源治理主体具有多元一致性,即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个网络成员虽然都有各自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但当面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公共问题时,如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不同的治理主体又会围绕着这一特定的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通过对话、讨价还价、协商、谈判、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达成共同治理目标,并形成资源共享、相互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建立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组织网络。一般来说,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公众是构成公共资源治理网络不可缺少的主体要素。其次,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互惠合作。“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以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和资源稀缺为分析的事实假设,因此,公共事务的完成是相互依存的管理者通过交换资源、共享知识和谈判目标而展开的有效的集体行动过程。”[4]公共资源治理主体之所以愿意结成治理网络,原因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利益上和资源上的相互依赖,并通过在网络中进行资源交换以实现各自或共同的利益。另外,网络中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存在着复杂的动机,利己与利他共存。在一个风险社会中,理性的行为主体往往会通过对话机制交流信息,来克服有限理性的缺陷;通过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将行为者锁定在利害相关的网络中,来达到减少交易费用和抑制机会主义的目的;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以提高适应风险社会的能力。博弈理论也告诉我们,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被认为是最利己的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为主体之间倾向于建立长远的互动关系,采取合作互惠的行动策略。因此,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互惠合作的行动策略是公共资源治理主体的基本行为方式。最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一个持续互动的政策过程,而不是单一中心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多中心、水平化的互动过程,成为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场域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资源共享、减少分歧,增进合作,最终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因此,为了维持与促进网络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持续性互动,有必要建立适当的规范和制度,实际上,网络治理的运行是建立在信任和多元行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之上。
二、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与信任机制
对于信任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定义,各学科对信任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管理学中对信任的研究是和企业的绩效、竞争优势、冲突的缓和与机会主义的减少相联系的;社会学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考察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经济学中的信任研究主要关注信任对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而组织学中的信任是被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消除交换关系中的机会主义,促进合作关系。Das和Bing-Sheng Teng(1998)对信任的定义做了三种不同程度的区分:一是信任被广义地定义为对被信任方履行何以行动可能性的信念和预期;二是信任被狭义地定义为,一方对另一方信誉和可靠性的评价;三是更局限的方法,认为信任是“在承担风险情形下,为尊重他方而对其动机的积极预期”,这一定义认为风险是信任的核心,只有在风险环境中信任才是恰当的因素。[5]总之,信任反映的是参与主体(包括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信任属性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信任主体,即是组织信任还是人际信任。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实际上是治理结构中各种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间信任。罗西瑙等人认为,组织间信任实质是指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意愿或行为的积极期待和接受意愿。也就是说组织间信任可以归结为在合作关系中的参与主体不会出于私利而做出有损合作关系的行为的期待。这种信任关系是相互的,在合作关系中的参与主体互为信任方和被信任方。当然,在信任的程度上各参与主体之间又不尽一致,也可能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必须对组织间信任进行必要管理,避免误信或过度信任。
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指出,“如果说价格竞争是市场的核心协调机制,行政命令是等级制的核心机制的话,那么信任与合作则是网络的核心机制。”[6]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信任是合作的润滑剂,信任是合作的感情基础”,与此相反,不信任破坏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将会失败。”[7]因此,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基础性机制,各种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及其信任程度,决定了它们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
然而,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基于网络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长期交往而产生的持久性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机制首先是公共资源治理参与各方在面对公共资源复杂的和不确定的未来时所表现出的彼此间的信赖,它能够确保参与各方以共同都能接受的行为对未知的环境做出相应的反应。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公共资源治理参与各方放弃对他方的控制,从而也决定了在合作伙伴中的参与者对整个合作的产出结果影响甚微,也即合作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力越低,就越需要得到另一方的信任。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政府是唯一拥有公共权力的行动者,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如果政府坚持依靠权威手段控制其他参与者,那么信任机制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产生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三、信任机制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作用
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它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信任“就像在经济交换中合作功效卓著的滑润剂,用它来化解复杂的现实问题,比采取预测预报手段、运用权威、或者通过讨价还价,要快速得多,省力得多”。[8]具体而言,信任机制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信任机制能够提高合作关系的灵活性。信任不仅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行动者之间合作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参与者合作关系灵活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治理网络的参与者之间信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往往会因为参与者之间缺乏互信,对环境变化后果的判断不一致,甚至相互猜疑,致使他们对环境变化不能做出及时反应,贻误最佳决策时机,使合作利益受到损害。相反,较高程度的信任能够促进治理网络参与者灵活、及时地行动,遵守合约,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矛盾,谈判和减少处理纠纷的时间耗费,使得网络中的合作关系能够及时地反映环境变化的要求。[9]
第二,信任机制能够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成本由信息收集、签订契约、监督和执行等一系列成本构成。当公共资源治理主体对彼此不了解或者对网络中的参与者所传递的信号不信任时,为了促使合作的产生,每个参与主体都必须发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获取其他参与者的各种信息,以做出适当的判断,因而存在大量的信息收集成本。信任机制则可以使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更有效,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会大大减少。另外,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由于参与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或信息的不完备性,各参与者之间总是存在各式各样的分歧和冲突,如果彼此信任,就可以形成一种自我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对彼此间所达成的口头或正式契约自我实施和遵守,不需要外部执行,如通过司法部门等第三方执行,由此减少了网络治理中的监督成本与执行成本,释放了更多的资源用于对公共资源的治理,也提高了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效率。
第三,信任机制能够促进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主要涉及两种知识的获取:[10]一是显性知识;二是隐性知识(如专有知识或技能)。相对而言,显性知识容易编码,能被复制和传递,且不丧失完整性,学习起来也比较容易。而隐性知识往往蕴含在组织实践和文化中,不容易编码,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描述,只有在一种没有沟通限制和障碍的工作关系中,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实现共享。由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密切交互作用是通过网络转移或学习隐性知识的一种有效机制,因此,基于信任的强大社会资本能够有利于在网络中营造自由开放的交流氛围,促使网络合作伙伴紧密接触,从而推动网络中的信息与专有技术的交流与转移,提高公共资源治理效率。
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的建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信任机制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信任机制的构建并不容易,它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正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帕克赫博士认为的,信任的生产有三种方式:[11]一是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生产。它依赖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合作伙伴是同一个组织系统中的成员;另一种制度安排是通过中间机制来产生信任,如合作伙伴自愿地通过某种活动或方式自我设限,向对方示以诚意;还有一种制度安排是通过有预见性的事后惩罚措施来减少采取机会主义的潜在收益。二是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生产。信任产生于对过去或未来的预期。如果网络过去有过合作,则合作关系越长,越有助于加强产生信任的社会心理纽带;如果没有合作过,合作伙伴长期积累起来的商誉很重要,名誉感越强烈,越有可能做出诚信行为。三是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信任生产。文化背景不同的行动者成功合作的关键在于求同存异,抓住主要问题并取得共识,通过一段时间相互学习和了解,就能逐步产生信任。
因此,一般而言,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的建立也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两条途径来实现。从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看,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任何参与主体,无论是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还是公众等,都应该重视正式的制度性工具在信任机制建立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应加强正式制度的供给,营造一个诚信的制度环境。如政府可以为公共资源治理主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以保障各类型参与主体的集体行动在一定的规范和秩序中正常进行。与此同时,政府还承担着第三方监督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为在公共资源治理网络中具有良好声誉的参与者提供信誉担保或奖励,使网络参与者之间能够更好地实现相互合作。当然,正式制度的供给本身需要一个诚信的政府,因此,加强政府信任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就成为实现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信任机制的重中之重。从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看,应积极发展公民社会,促进“信任”社会资本的增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12]因此,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公民社会的发展与“信任”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它通过协作的横向纽带把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参与者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横向的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网络随之发达,网络中各主体之间平等对待、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程度也就越高,并愿意遵守法律规章和社会道德准则,由此而达到社会互信,从而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实现。
[1]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8.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7.
[3]Ophuls,W.Leviathan or Oblivion[A].In H.E.Daly(ed.):Toward a Steady State Economy[C].San Fran cisco:Freeman,1973:228.
[4]孔繁斌.治理对话统治——一个政治发展范式的阐释[J].南京社会科学,2005,(11).
[5]T K Das,Bing-Sheng Teng.Between Trust and Control:Developing Confidence in Partner Cooperation in Allianc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1998,23(3):.
[6][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C]//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5.
[7][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82.
[8]鄞益奋.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J].公共管理学报,2007,(1).
[9]Jones G.R.,George J.M.The Experience and Evolution of Trust:Implications for Cooperation and Team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3).
[10]潘旭明.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J].财经科学,2006,(5).
[11]Arvind Parkhe.:Understanding Trust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98,33(3).
[12][美]罗伯特·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C]//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5.
G2
A
1002-7408(2011)01-0049-03
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网络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08SH39)。
唐兵(1978-),男,南昌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主要从事公共资源治理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