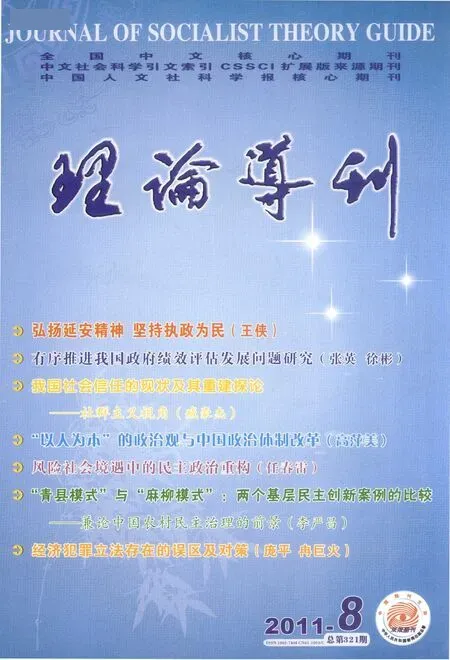试论张承志小说的民间情结
陈梦岳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陕西延安717200)
试论张承志小说的民间情结
陈梦岳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陕西延安717200)
民间情结是张承志小说标志性的特征。他的小说执著地演绎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其民间化程度之深、范围之广罕有人能比。这种民间情结的展示也在提示着我们对“文学第三世界”的关注。
张承志;小说;民间情结
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倡导“到民间去”,在这一文化运动中,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与民间亲密接触,但他们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大致有政治的、审美的、二元的三种态度。应该说,这是对民间较为完整的态度。张承志与民间的关系也是在认知中冲突,冲突中进一步认知。两相比照,发现一个当代作家的民间情结与“五四”知识分子的民间态度有隔代对应关系。本文以张承志小说为例,探讨他是如何演绎这三种态度的,以及他与民间发生联系后的最终结果。
一、政治的态度——带红卫兵情绪的知青与民间
一般认为,“五四”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上海大学的王光东却发现了“五四”的民间意义,概括出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与‘民粹派’思想相关的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政治符号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民间、农村、农民、平民的内涵是没有多大差异的,他们眼中的民间主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价值立场,民间是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1]
“五四”时期,李大钊最早号召青年到农村去。1968年底,毛泽东也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于是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变成了农民。张承志曾是一个“地道的红卫兵”,这种个人背景关系着作者在进入民间时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他们从小接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在带有“狂飙突进”性质的红卫兵运动的激励下,更是将领袖崇拜推向了极致,丧失了个人意志。“革命意志”成为他们行动的唯一准则。《金牧场》中有对这种红卫兵心理的入骨描写:“皮带上黯淡地闪着一层湿湿的光亮,它挟着一股狠狠的风……它灵捷快速。清脆的啪啪声中藏着一丝颤抖,我甩甩头,我蔑视这种颤抖……我觉得在狠的刹那间我跨越了一道关隘。‘呼!呼!呼!’我满腔仇恨而满心痛快。那颤抖声渐渐熄灭下去了,我逾越了一道人鬼不知的关隘。人要爱憎强烈,人也要有无畏勇敢的恨。”[2]
红军长征时,外号黑络腮胡子的副连长抢占了某农人的地,被农人愤怒地打了一拳。文革刚刚开始前来步行长征的红卫兵知道这一历史情况后,用皮带恨恨地抽这个农人。本来,“我”因为个人道德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丝颤抖。可很快,我就蔑视这种颤抖,并靠“爱憎强烈”、“无畏勇敢的恨”的革命理想顺利地“跨越关隘”,开了杀人之戒,并觉得“痛快”。可能正如詹姆逊所言:“献身政治与献身艺术有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有时都很‘刺激’,都可以得到很强烈的快感与享受。”[3]经历了这种“快感”的品尝,红卫兵就更矢志不移地坚守“革命意志”。
所以以这种带红卫兵情绪的心态进入民间,必然使得主体以革命的眼光打量厕身的民间,并竭力地抑制个人情感的浮出。他们喊的口号是“我们是红卫兵!我们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队部怀疑小刚借宿的主人乌力记是“内人党”并委任他做大队专案组长时,他尽管留恋这蒙古包里的温暖,但他仍坚定地想:“这是一场决定草原阶级命运的搏斗啊,一个红卫兵怎能模糊阶级阵线呢?走!搬起被褥,搬到队部去住!”他们甚至于寻求外在的相似,“我想要个意思和红卫兵一样的名字”。[4]23
二、审美的态度——审美的自由的民间
“五四”知识分子对民间的第二种态度是“以胡适、刘半农等人为代表,一方面充分肯定民间白话语言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以《歌谣》周刊为核心,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倡导中,发现民间文化形态、文学的美学意义并纳入新文学的构建过程中。他们对民间世界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他们所认同的民间是文化的、审美的世界。”[1]相对应,张承志小说所开拓的民间审美空间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1.民歌的借鉴和运用。民歌被称为张承志小说美的精灵。[5]他在多篇小说中成功地借鉴和运用了民歌。五四时期开展的民歌搜集活动,主要是从民间发现富有活力的艺术形式和来自于民间的精神。张承志认为“小说的构思在本质上与音乐和绘画是一致的”,[6]因此他的小说中穿插了不少的西部民歌。关于民歌的艺术形式,本文不做探讨,而民歌中所蕴涵的来自民间大地的品格却值得梳理。初略总结,有四个方面:强烈的命运和悲剧意识;流浪意识;热烈直爽;坚韧的乐观主义。
民歌的运用不仅给小说带来如诗如画的背景,而且与小说内容相映照,给文章音乐般的旋律和跌宕起伏的节奏感。更重要的是,民歌中所蕴涵的民族情感给人深刻的启迪,开拓了小说的民间审美空间。
2.浪漫主义风格。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其显著的特征:一是着力歌颂大自然,一是向往理想的文学精神。[7]
(1)大自然的赞歌。浪漫主义者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阅读张承志的小说,可以领略到蒙古草原的辽阔与广袤,天山腹地原生态的壮美景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改变了以往作家只是把自然作为单纯背景的写法,赋予自然一种人格化的力量。他也找到了将自然与心灵完美结合的方式——意象塑造。因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出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8]
张承志的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意象群有山、河、大坂、泥屋、太阳、草地、骏马、雪路、绿夜;似父亲般奔腾不息的黄河;埋葬着草原生命的青草味儿;阳光照射下的汗腾格里冰峰;奔驰在无际草原上的黑骏马;像大地的狰狞牙般的大坂……构成了一幅幅牧歌式的田园画。正因为意象是情理相兼的,因此每个作家所精心选择的意象都凝聚着创作者独特的思考和情感,被王蒙感叹的“河全被这小子写完了”的《北方的河》就既写了河,也记下了他的成长足迹:他在额河中知道了宽容;黄河中寻找到了一直缺席的父亲;湟河里发现了残缺也是一种美;永定河边走向沉静、含蓄;从梦中已在解冻的黑龙江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更让他领悟到:人生就是一条流淌的河,生生不息,不能轻言放弃。
(2)高唱理想主义。张承志“这位创造了‘红卫兵’称号的热血者,只是摒弃了那个时代的内容之后,实际上仍在‘红卫兵’这一形式的框架里。”[9]红卫兵突出的特色是革命理想主义,尽管他经历了向知青、农民的转变,但“‘知青一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在剥离‘革命’后所剩余的‘理想主义’。往往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品性’,而不是意义话语。”[10]这种带有红卫兵时代“情绪记忆”的“精神品性”与浪漫主义的“生活应该如此”的创作方法如出一辙,试图站在现实生活之上去追求一个令自己满足的极乐世界,虽然它像极限一样,可望不可及,但从来都不放弃这种怀想。小说《大坂》的知青“他”在接到妻子流产病危的消息后,毅然向称为生命禁区的大坂进军,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最终登上了海拔四千米的冰山,并获得了“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的启示,而他在坂顶却没有照相,“为已经粗显轮廓的论文——留下些缺憾吧。”这正是作者追求的人生意义:在路上的痛苦是无所谓的,富有缺憾却能保持继续向前的动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又有了《顶峰》、《雪路》等新的目标。
三、二元态度——认同与排斥的民间态度
“五四”知识分子对民间的第三种态度是“以周作人、鲁迅等人为代表,对民间文化形态持二元态度,既充分肯定和吸取了民间文化形态中积极健康的生命活力,又强调批判民间、提升民间以达到启蒙的目的。周作人对民间的这种二元态度与鲁迅是一致的”。[1]张承志的作品也如鲁迅“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一样,不仅有着“活泼民间”的生动与丰富,也有着“土地上的愤懑”。
首先,张承志以一种审美的态度发现民间文化的美学与思想意义,这在上部分已粗略论述过。这显然是记忆中的、浪漫的乡村民间文化,带有作家个人浓郁的情感想象的因素,与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透露着民间文化形态的某种情韵。
但由这种民间的情感化价值立场所发现的民间精神,有时却又经不起创作主体以一个现代理性思考者的眼光的审视。一旦他把眼光从浪漫的世界拉回现实时,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价值原则的冲突。因为“民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概念,只有厕身其间才能真正体会到民间的复杂本相”。[11]这个概念表明民间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场所,不仅容纳了属于民间特有的原始生命力、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更掩藏了落后、愚昧这些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污垢。张承志作为一个具备现代理性的作家,在反映民间生活时,也不能无视这种污垢的存在。《阿勒克足球》中牧民们对知识拒绝漠视的愚昧;《黑骏马》中的描述却最深刻也最撼动人心。当白音宝力格听说自己美丽纯洁的恋人索米娅被恶魔黄毛希拉奸污并怀孕时,他怒火中烧,提刀准备去杀希拉,而这时他的老奶奶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有什么呢?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啊。”[4]209这几句话写出了百年乡土中国女性的奴性内化,进而强烈地批判了民间社会的愚昧与残酷。自称为“草原义子”的张承志也发出了这样的无奈之音:“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尽管我爱它爱得那样一往情深。”[4]210此时,草原民间的“藏污纳垢”使张承志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意识到自己不属于那个群体,形成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乡土文学家那种与乡村的“在而不属于”的关系。白音宝力格也选择了“背离”这一弃否的方式,他是否会和鲁迅一样归来后再离去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法国的黎朋在《群众心理》一书中曾指出的:“个人一到群众里面,他的知识程度就不能不骤然降低。”更何况知青本就没多少可供抵制粗俗的知识积蓄,他们不像鲁迅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抵制民间的拉拢而保持独立的思考,故而被同化也就在所难免。另外一方面当然是鬼蜮般的民间社会所散发的气息,使带有红卫兵情绪记忆的毅然选择背弃的知青,臣服在它脚下,在各种充满矛盾的体验中,逐渐由排斥走向理解和认同。这一过程中,“草原用沉潜内蓄的阴性文化和不屈不挠的阳性文化共同哺育张承志。使他走向丰富和深邃。”[12]最能代表草原阳性文化和阴性文化的无疑是男儿之美和母性之爱。
第一,阳刚的男儿之美。民间是与“官方”对应的一个概念。当民间个体无法与强大的官方意志相抗衡,又不愿屈辱服从时,他们就会为了保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和精神品格的完整而选择自己的消解方式。对此,张承志在《刻在心上的名字》中的描述较为具体:小刚插队住的蒙古包主的儿子乌力记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冲击草原的时候,被污蔑为“内人党”、“叛国”,被公社专案组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乌力记一开始还以牧民的善良和真诚向小刚分辨,当他发现这无济于事时,他便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夜里,他解下腰带,在屋里自尽了……”[4]27这个举动是一场充满“血性”的完结,完全使充满红卫兵政治豪情的小刚彻底震服。《金牧场》中也有类似的描写:骆驼官桑结也被指为“内人党”,他最终以坐化归真了断生命。他们宁死也不肯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政治迫害,虽然放弃了生命,却维护了他们不愿舍弃的东西,就是那“牧人式的信念和自白”,用无言的沉默来对抗残暴。
张承志的一系列作品如《北望长城外》、《大坂》、《北方的河》、《美丽瞬间》中尽显男儿的阳刚之美:身体的受难甚至生命的丧失都是不足可畏的,只要心灵保持着独立。这不能不说是受了这种民间血性的浸染。
第二,宽柔的母性之爱。与阳性文化的阳刚、积极的外显不同,阴性文化更多呈现为宽柔、被动、潜在的特色。同样面对强大的政治风浪,阴性文化选择毫无芥蒂地宽恕、原谅。《刻在心上的名字》中乌力记自尽后,乌日娜嫂子和桑记阿爸来接小刚仍回他们的蒙古包居住,桑记阿爸还安慰他:“孩子!风雪的春天总会有死去的羊羔,可是羊群里的羊羔子还是越来越多……”并以长者的经验和智慧赐予他“阿拉丁夫——人民的儿子”的名字,教导他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该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使小刚终于将这个名字刻在了心上。
虽然桑记阿爸是一位草原上的男性,但他的行为却处处表现出阴性文化的特点,就像朱自清《背影》中母亲似的父亲形象。这种阴性的仁爱与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有惊人的相似。如“你打了我的左脸”我不恼,还把我的右脸也伸过去让你打,我还是不生气,笑着把自己的左手也伸过去……你终于明白:想征服我,让我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表面上,你获得了肉体上的胜利,可实际上,我的精神是坚如磐石的,你才是真正的失败者。所以,“你”最终屈服于“我”。小刚正是经历了这种由胜利向失败的顿悟,彻底信服了宽柔的母性之爱。至此,两种互补性文化的冲击,使主人公与民间的情感沟通有了根本的变化。当初的敌视与隔阂消失了,开始真正融入民间。并在《心灵史》等篇中最终找到了哲何忍耶这样的极端民间宗教作为自己的终极信仰,完成了心灵的皈依。
四、余论
张承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情感风景,他的道路尽管充满了曲折、坎坷、孤独,但惟其如此,才会让我们看到坚守者的顽强与执著,并对这执著满怀敬意。
周作人曾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认为平民的文学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的目的并非要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因此探讨张承志的民间情结也不是要让我们在各方面和民间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更不是将文本展示的民间给予展览。凝视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海洋,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草原、黄土高原、戈壁沙滩是那么的贫瘠,生活在此的一代代老百姓仍沿袭着简朴的生活方式,它穿过漫长岁月的暗道长廊,像历史的车轮缓慢向前转动。
我们也仿佛看到了一个民族百年孤独、负重前行的历史,他们蜷缩在第三世界里“文学的第三世界”,理应换来更多关注的目光。
[1]王光东.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五四民间意义的发现[J].当代作家评论,2000,(10).
[2]张承志.金牧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158.
[3]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5、151.
[4]张菜鑫.张承志代表作[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5]闫秋红.民歌,张承志小说美的精灵[J].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3).
[6]张承志.清洁的精神[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53.
[7]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246.
[8]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202.
[9]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6.
[10]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7.
[11]陈思和.民间的还原[J].文艺争鸣,1994,(1).
[12]黄发有.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1999,(2).
I207.4
A
1002-7408(2011)08-0110-03
陈梦岳(1961-),男,陕西延川人,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副教授,陕西省作协会员,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及汉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陈合营]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