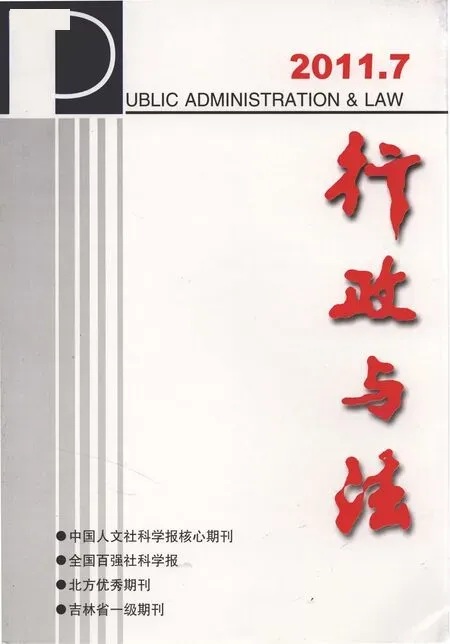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路径探讨
□ 荀福峥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路径探讨
□ 荀福峥
(吉林警察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以罪刑法定司法化为研究视角,突破了以往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司法者如何操作法律是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完备的司法体制与先进的司法技术,更需要司法理念的创新。在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中,刑事政策作为司法体制的特殊组成部分需要予以合理使用,法官的能动性是提高司法技术的重要环节。另外,司法理念作为思想保障,更需要确定形式理性的标准。从这三个角度探讨罪刑法定司法化实现的路径,不仅突破以往的研究方法,更是深入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方式之一。
罪刑法定司法化;形式理性;刑事政策;司法技术
罪行法定原则自1997年正式纳入刑法规范以来,《刑法》第3条的适用问题一直被理论界关注。罪刑法定立法化能够使得罪行法定原则有法可依,这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罪行法定司法化则是将罪行法定原则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罪行法定原则的效果。立法工作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相关的立法技术得到解决,但是实践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有学者认为“罪刑法定写入刑法12年来,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都证明了这个原则的彻底失败。”[1]尽管有些偏颇,但是不能不说罪刑法定司法化在中国的实践道路上障碍重重。虽然罪行法定的立法化讨论最终是要放到司法实践中去检验,但这也说明了,司法化的讨论必须是建立在立法化的基础之上。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回归到罪刑法定这一原点,进行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路径探讨。
一、理念支撑——形式理性之倡导
《辞海》将“理性”界定为:“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或能力;划分认识能力或认识发展阶段的范畴。”[2](p1350)可见,理性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从认定犯罪的角度来讲,可以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犯罪构成,进而选择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方式。形式理性是强调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按照刑事法律的规定,对某一犯罪行为作出是否入罪的推理,形式理性主义者是严格恪守法条规定的代表。不同于形式理性的论断,实质理性大多从规范背后的内涵入手,在具体认定犯罪上,实质理性宣扬社会危害性,类推的理论经常会得到运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有着复杂的关系,“立法是一个从实质到形式的过程,而司法是一个从形式到实质的过程。在司法环节上,实质正义吸引人们侧重考虑立法目的,强调价值判断,使规则的稳定性不断受到冲击。”[3](p272)实质正义必须以形式正义为基石,实质正义的实现必须以不破坏形式正义为前提,这也是处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重要前提。
罪刑法定原则一直以来与类推的理论格格不入,以社会危害性的视角来看,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反对运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去指导司法实践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质主义观念所倡导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过分宣扬了实质理性,忽略了认定犯罪的基本点,那便是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范,即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而形式违法性才是认定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形式理性“虽然牺牲了个案公正,使个别犯罪人员逍遥法外,但法律本身的独立价值得以确认,法治原则得以坚守,这就可能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4](p10)实质理性过分张扬了社会危害观,进而将类推的理论扩大到司法适用,阻碍罪刑法定的实现。“在罪刑法定的世界里,手段上的合乎理性是第一位的,它超越目标上的伦理性追求,或者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目标伦理的追求。”[5](p188)因此,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如果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将刑事违法性作为认定的出发点,进而选择形式理性,摒弃具有实质理性色彩的社会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好罪刑法定原则,进而通过法律的适用实现社会正义。
另外,从法的适用目标来看,法律效果始终是最基本的追求,实现社会效果固然会使司法活动的完美程度增加。但是,以社会危害程度作为考量犯罪的出发点,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便是将法律阻却事由类推为犯罪行为,进行入罪的评价。这样一来,社会危害性理念的确得到了“充分”运用,社会效果也有一定的实现,但这是否真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呢?当然不是,罪刑法定强调的是所有的司法活动都要在法律这一大背景下去进行,法律规定是首要的也是应当被最先考虑的因素。在司法活动中,尤其是在处理重大疑难的案件时,罪刑法定往往会被司法者本能地予以抵触,进而更加倾向于入罪的适用。“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中始终具有强烈的实质理性的冲突,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法治意味着一套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它以刑事理性为导向。罪刑法定司法化就是将定罪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因而它必然以形式理性的司法观念为先导。”[6](p68)抛开法律,强调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必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司法只对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进行惩罚,若刑法规范对某种行为没有做出入罪规定,那么这一行为便不认为是犯罪。“形式理性意味着只能在形式合理性的范围之内来追求实质合理性,追求实质合理性不得超越形式合理性。”[7](p5)所以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法律可能会允许这些行为人逃脱刑事处罚。作为恪守法律的代价,罪刑法定必须要忍受这些逃脱刑事制裁的行为。这同样也是维护社会相对正义和刑法规范确定性的必然要求。
二、体制保障——刑事政策之限制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甚至在有时候需要类推适用司法政策的有关规定加以辅助。“比附”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官审案不仅仅依据法条的规定,而且他们还往往身负强烈的伦理使命。在审理一些较为复杂的案件时,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那么此时法官便选择伦理道德去判断。所以,在这种浓厚的司法观念的影响下,罪刑法定往往被束之高阁,很难发挥应有的价值。由于体制的原因,刑事政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刑事政策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不可否认,在打击犯罪的效果上,刑事政策的运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处刑规定较为轻缓的刑法规范往往在“严打”时期被“依法从重”的政策予以替代。于是,罪刑法定的“法”便被“政策”替换,对于司法者来说,被动接受“政策”的指导,做出符合政治背景的判决。这样的审案方式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推定为“政策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与罪刑法定的价值内涵相违背的。这样类推的结果无疑导致了将违法行为入罪,使得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相混淆。
1979年《刑法》规定了类推制度,不仅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类推制度在我国扮演着重要的“调节器”作用。从我国司法者对于类推的适用情况来看,类推的适用可以界定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之内的类推,即通过法律规范之间的某种联系而适用类推制度;另一种则是法律之外的类推,即由于没有法律的规定而类推适用其他非规范性法律,在刑事领域,最常见的表现是类推适用刑事政策的规定。类推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但罪刑法定必须采用法律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了刑事法律的有限性,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允许在一定的阶段,人们认识犯罪行为是有范围的、有限度的。类推制度的存在暗含着在立法之外,刑罚权扩张的危险。这种扩大的刑罚权势必会构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刑事政策在作为“比附”的对象时,要保持克制,这不仅是由于存在刑罚权扩张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对于罪行法定的破坏。因为罪行法定的出发点是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刑事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形式。不可否认“没有刑事政策的刑法是呆板的文字,机械的记述和僵化的规训,”[8](p13)但同时应当明确,刑事政策只能作为刑法规范的补充来适用,“补充”应当是建立在对于出罪的基础上,对于入罪的条件,刑法规范已经予以明确说明了。严格恪守刑事规范的入罪标准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因而对于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类推刑事政策进而将入罪范围扩大化。如果将刑事政策作为入罪的标准进行适用,那么必然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政策应当出于排除犯罪的考虑,适用于认定犯罪的活动。
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行为对于案件的处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受现有体制的束缚,法官的作用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法官的行为受到行政权的侵扰而难以真正独立,依“政策”判案的方式往往比依法律定罪显得更为 “顺手”。于是,法官在选择审理依据的时候表现出较大的随机性。罪刑法定司法化要求的恪守法律规定,这种恪守并不是要求在实践中去呆板地适用,而是一种在严格遵循之下灵活适用。刑事政策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可以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其适用必须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当然在这种适用下,并不是要否定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方面所应有的作用,而是强调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去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刑事法律规范之外的行为是需要靠刑事政策调整的,“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是排除犯罪的依据,刑事政策不能将这块的行为入罪化。从另一角度来讲,类推制度本身在适用时也不能确保对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追究,这是因为社会危害性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操作者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无论是刑事政策的补充作用,还是类推的有限适用,都是需要在罪刑法定的框架之内完成,司法实践需要将刑事政策予以合理化的运用。
三、技术保证——司法技术之提升
司法技术是将罪刑法定融入司法活动的工具,工具的使用状况决定了罪刑法定司法化的程度,即罪刑法定的实践效果。司法技术包括刑法解释的方法、刑法规范适用的推理方法等。如果说刑事法律规范是一个有待加工的产品,那么司法技术则是一条运送带,通过它运送到司法实践的机器中加工,进而成为一个完成品。可见,司法技术在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中,是扮演着重要的“传送带”的角色。形式解释理论与实质解释理论的选择就是一个司法技术的问题。这种选择并不仅仅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就能够解决的,它会受到犯罪论体系的牵制。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也是一种技术条件,它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在这种犯罪论体系指导下,司法活动可以有效排除不符合该当性条件的行为,这种有效筛选会节省司法资源。将该当性作为首要标准,排除“犯罪行为”必然会促使刑事人权保障。“无该当性即无罪”正是契合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思想,这种司法技术的良好运用产生的后果不仅使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彰显了罪刑法定所倡导的限制司法权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法律解释本身就是一项适用法律的活动,法官在解释法律时需要发挥法官的能动性,“法官能动性的适当发挥、裁量权的适当行使是司法运作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心环节。刑事司法运作的优劣,将直接决定能否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而这一切都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9](p306)法的价值表现为秩序、正义和秩序,于此刑法解释有两种模式,即社会保护优先的解释模式和个人保障优先的解释模式。两种解释模式处于不同的价值考虑。社会保护的价值理念已经通过刑事法律规范加以确认了,那么对于没有被法律确认的部分,就完全可以通过个人保障的目的予以解释。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见到之前的这两种解释的问题,对此,可以分别对待,一方面对于已经通过刑事规范确认的行为,法官可以通过严格解释或者文义解释的方法加以认定;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法律规定的行为,法官可以选择客观目的解释的方法,对出现的行为加以认定。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突出权利的保障是规范解释的首要选择。权利的保障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于已有法律的严格贯彻,这种“罪行法定”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复杂情况。于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权利,需要对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作出更为慎重的处理。
如前所述,在法律没有相应规定时,不能出于打击犯罪的片面目的而忽视对于犯罪嫌疑、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作为刑法解释的指导理念,在刑法解释的司法实践中贯彻罪行法定原则,可以防止司法权被滥用。毕竟,罪刑法定与原心定罪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国家要行使刑罚权,除了要依据已制定的刑法规范之外,还要受到伦理纲常的制约。当然,在确定性程度上,刑法规范要远远高于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刑法中,处理刑法规范与道德规范紧张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将原心定罪制度化,并且通过法官的人格力量加以辅助。王安石说:“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10]可见,在适用刑法解释时,罪刑法定原则为刑法解释的适用提供了一个边界,边界的作用强调了作为司法化了的刑法解释必须接受罪刑法定的约束,不能任凭法官的意志去解释。
“法官制定的只是第二等的法律,并且它从属于立法者制定的法律。”[11](p4)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必须是建立在现有刑事法律规范基础之上的,讨论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路径也必须回归到现有的法律规范之上。权利保障理念要求在没有刑事规范时,刑罚权就没有适用的前提。刑事理念、体制和技术的探讨只是为罪刑法定司法化提供一个路径的指引,在具体的实践中,还要应对每个路径之下的多重问题,当然这也是罪刑法定司法化道路上需要面对的问题,不能不说在司法化的道路上充满荆棘,但是目标始终要明确,那就是坚定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
[1][3]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M].法律出版社,2009.
[2]辞海(第六版)[M].上海辞书出版社.
[4]陈兴良.刑事法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劳东燕.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陈兴良.法治的使命[M].法律出版社,2003.
[8]童德华.规范刑法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9]彭凤莲.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百年变迁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10]临安先生文集(卷82)[C].度支付使厅壁提名记.
[11](德)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商务印书馆,1998.
(责任编辑:徐 虹)
The Path of the Legally Prescribed Judicial Discussed
Xun Fuzheng
On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from the judicatur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has broken putting emphasize o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How to operate the law is the key to the foresaid topic,and it needs perfect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technique.In addition,the innovating of the judicial reasoning is very important.During the judicatur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criminal policy as a judicial system of special components should be reasonable,the judge's initiative is the important link for improving the techniques.In addition,judicial reasoning as mental indemnification,should be standard.Therefore,the way of the judicatur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sh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three angles,it not only for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but a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judicatur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formal rationality;criminal policy;judicial technique
D924.12
A
1007-8207(2011)07-0072-03
2011-03-29
荀福峥 (1971—),男,吉林白山人,吉林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