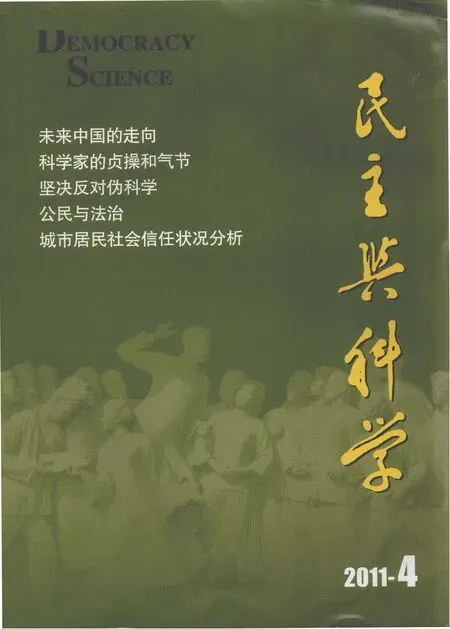政体重要,还是政道重要
■王绍光
政体重要,还是政道重要
■王绍光
与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理政之道,或更具体地说,是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在《论语·颜渊》里孔子说:“政者,正也。”因此,关于“政道”的思考也就是关于“正道”的思考。
中国的先哲为什么不重形式而重实质?道理也许很简单,从商周开始,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可以比拟。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亦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此,我们看到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管子等)一直到朱熹、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谈的都是政道的问题。
例如,孔子推崇“先王之道”,并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国家:有“道”就是仁与礼的和谐统一。他反复说到“邦有道”如何如何,“邦无道”如何如何,把“有道”与“无道”对立起来。又如,孟子严格区分了以德服人的“王道”与以力服人的“霸道”,力倡“王道”,力拒“霸道”。再如,荀子在承认“王道”是正途的同时,承认“霸道”的作用,这就是汉初所采用的“王霸杂之”的治理方式,采取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立场;而管子则一面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一面力倡和践行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霸道之治。
从《春秋》到《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再到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及《大同书》,历代中国政治学思考、讨论和针对的均是统一与分裂、土地制度、选拔考核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这些政治的真问题,中国政治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总结处理这些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建立起来的。务实的中国历代政治家,往往是在现实实践中操作的治理者而非柏拉图这种空谈的哲学家,布衣入卿相的平民子弟,更不会如孟德斯鸠那般迷信,凭一个理想的政体,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现实政治问题。
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历代的先哲往往将政道细化,进而分别讨论各主体的行为准则(如为人之道、为吏之道、为臣之道、为君之道)以及各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如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官民关系等),因为所有这些“道”都会影响理政。黄宗羲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的“家天下”,但翻开他的《明夷待访录》,满纸都是“君之道”、“人臣之道”、“师友之道”、“奴婢之道”。
不仅中国的思想家关心政道,中国的历史学家同样关心政道,于是有了一大批《资治通鉴》、《贞观政要》之类的史书。司马光就明确表示,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热捧此书,也是因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除此之外,一些君王也留下了自己对政道、治道的体会,如唐太宗李世民撰写的《帝范》、武则天撰写的《臣轨》、明宣宗朱瞻基撰写的《御制官箴》、南宋孝宗赵昚赐名的《永嘉先生八面锋》等。当然,还有从战国一直到清朝历代治理者们撰写的一大批标题各异的“官箴”。到清朝,它汇成了重要的政治文献教科书《皇朝经世文编》。总之,中国的先哲很清楚,哪怕政体相同,都是君主制,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可以非常不一样,其后果自然也会千差万别。因此,对中国的先哲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道,而不是政体。
有人会问,毛泽东不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过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吗?不错,他承认“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毛泽东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例如,他把其理想政体称为“民主集中制”。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决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做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同理,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当毛泽东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提到的“民主”并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主要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仅从政体上理解民主,这些话毫无意义。
我们之所以花这么长篇幅对比西方的“政体观”与中国的“政道观”,就是为了说明一旦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与发现。
从政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某一两项特征至关重要,例如,是君主治国还是贵族治国?是否存在多党竞争?似乎这几个特征即可以决定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表现。而从“政道”的视角看,则政治体制内形形色色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都非常重要,都可以影响政治体制的表现;某几种形式上的安排,未必能左右全盘。
从“政体”的视角看,复杂的政治现实会被化约为几个简单的标签,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等,仿佛它们决然不同、非此即彼。从政道的视角看,所有的政治体制都是混合体制,包含了各种成分,只不过成分的搭配各不相同。所谓“民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非民主的成分;所谓“非民主政体”,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民主的成分。
从政体的视角看,某些政体必然优于另一些政体。从政道的视角看,不管是什么政体,它们都面临着种种挑战,其中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因此,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治国之道,而很难说这个政体优于那个政体。
从政体的视角看,只要它所关注的那一两项制度特征(如是否有多党竞争)没有变化,其他政治体制的变化 (如决策过程的开放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以静态的眼光观察动态的现实。从政道的视角看,治国之道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切治国之道的变化都意义重大,这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现实。
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既然政体被看得那么重要,有人就会以为换个政体(如开放多党竞争),一切问题便都可迎刃而解。而从政道的视角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现存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而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或原则是: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世界。
(本文摘自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韩毓海执笔的《人间正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