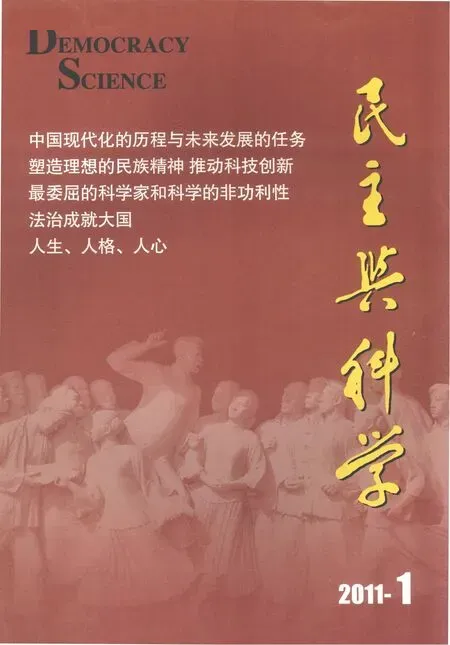值得商榷的“两个车轮”理论
■王长乐
值得商榷的“两个车轮”理论
■王长乐
火热于去年三月的“大学去行政化”争论,随着温家宝总理的“大学不应该有行政级别”的表态,以及大学“要逐步地去行政化”被写入《教育发展规划纲要》,而渐渐地归于平息,并且变得似乎不成问题。然而,参与讨论的双方都明白,在大学是否去行政化的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形成共识,一些围绕去行政化问题的意见,还经常地见诸报端。而关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同为大学活动“两个车轮”的理论(《科学时报》2010 年8 月27 日A1 版),可以说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
按照这种“两个车轮”理论的解释,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为承载大学活动的左右两个车轮,共同支撑着大学中的所有活动。这“两个车轮”作为推动大学前进的基本力量,既是大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也是可以相互协作而形成合力的。
从字面上看,这个理论无疑是两全其美的,其中既兼顾了人们呼吁大学去行政化、重建大学学术权力的要求,又肯定了行政权力的作用,安抚了大学中的行政人员,为其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同时,立足我国大学的现实体制和文化,可见这种理论是符合大学实际的,具有实践和制度的基础,不失为一种推进大学进步的渐进思路。
但作者对该理论的疑问是,这样的制度安排真的能解决大学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吗?能解决现实大学制度中隐含的教师权利和尊严缺失、进而导致的教师教育信仰缺失、教育责任感淡薄等问题吗?能使大学脱离行政化(也有人说是官僚化)的窠臼,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并产生大学应有的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影响和意义吗?作者对此深表怀疑。因为:
第一,大学历来是被称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和专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的,其学术权力来源于只有大学教师才有能力和资格承担培养学生和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性质。所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它源于大学的本质和宗旨,是始终存在于大学之中的。那么,我国现实大学中的行政权力是从哪儿来的,它的源泉在哪里?其在大学中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它有条件与学术权力相提并论吗?而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提并论,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能够消除吗?
第二,从世界大学的历史上看,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学术活动中衍生出的行政性工作中发展出来的。一方面,行政权力是必须用来为学术活动服务的。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相对于学术权力而言,是处于附属位置的。这种行政权力形态不仅是国外大学中的现实,而且也是我国早期大学中的现实。若以“两个车轮”理论的逻辑来设计大学中的权力结构,那是否可以说大学中所需要的附属工作,都可以上升到大学主导因素的位置,并因此再衍生出一些可以与学术权力相提并论的其他权力呢?比如:后勤权力,工会权力,妇女权力等。
第三,如果说将大学中的两种权力比喻为“两个车轮”,意在说明其可以使大学行进平稳的话,那么为其安上四个车轮岂不是更平稳。比如:是否也可以将一些大学总结的“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原则,概括为“四个车轮”理论呢?这样的说法虽然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安全的,但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对大学的实际进步有意义吗?如果这样的机制有效的话,人们还何必要提出“去行政化”的问题呢?温总理又何必说“要创造条件让教育家办学”的意见呢?因为人们严厉批评和诟病的大学行政化现象,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并引发了大学中的种种问题的。另外,任何比喻都是有局限性的。那如果将大学比作一个人,是否就能说“人可以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个心脏”呢?
第四,在国外的大学中,有“教授就是大学”的说法;在我国早期大学中,有“大学者,非谓大楼而大师也”的说法;也有“大学风气的好坏,全在于教授的质量”的说法。这些说法都说明教授是大学活动的核心,而保证这种教授作用的学术权力,也自然是大学中的核心。如果说行政权力可以与学术权力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说:“行政人员——抑或校长、院长、处长就是大学”呢?当然,这里所说的校长是指那些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校长,亦即是由行政机构按照自己的标准所任命的校长,而不是作为学术权力代表的校长,亦即是由教授会选举或董事会聘任的校长。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是“两个车轮”理论所难以回答的,但也是大学体制理论研究中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大学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问题,作者的思考是这样的:
一是大学活动是一种系统性活动,不仅需要基础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需要为教学和研究服务的行政工作和后勤工作。但这些行政工作和后勤工作,只能是为了帮助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得更好而提供的服务性工作,而不能“反客为主”地成为大学中的主导性工作,它们在大学中是处于附属地位的,不具备与教学、科研相提并论的条件。另外,大学中的行政工作在开展时需要一定的组织及规范,并在保证这些组织和规范时可能会衍生出一些行政权力,这是一种客观现象。但是这些行政权力只能是在行政活动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而不能扩展到大学的所有领域。这句话更明白一点说,就是行政权力只是对行政工作有效的,而不能扩大到学术领域。这与作为大学基础的学术权力在适用范围上是不一样的,因而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二是从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大学首先是作为一个教育和学术机构而延续和发展的,主导大学发展和变化的核心因素无疑是大学中的教育和学术活动。而大学中的行政工作及后勤工作,都是在大学教育及学术活动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外的大学中,还是在我国早期的大学中,大学中的许多行政工作都是由教师兼任的。而我国目前大学中的许多专职行政岗位,在那时也是由教师或学生兼任的。比如:系主任、教学秘书、教务处长等。这表明在一般意义上,学术活动是可以脱离行政工作而独立完成的。但行政工作则不同,如果脱离了学术活动,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决定与决定于、主体与服务的关系,而不是有人所解释的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关系。试想:学术权力怎么去“协作”行政权力?难道要教师和学生去迎合行政组织及其官员的要求吗?这种现象虽然在现实的大学中普遍存在,但并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方面,这正是大学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大学去行政化所欲消除的,也正是这种现象。另外,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学术人员可以没有障碍地去从事行政工作(这在社会学上被称为顺向转移,比如: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现在的许多专业人员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但是,行政人员能够没有障碍地来从事专业工作(这在社会学上被称为逆向转移)吗?所以,在以往的对大学活动的描述中,人们常说要搞好教学、科研两个核心工作,而没有听说哪个大学说要搞好教学、科研、行政三个中心工作。事实上,许多专职的行政工作人员在对待自己的工作时,都怀有一种谦逊的心态。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与教师的工作是有区别的,亦即教师的工作是专业性的,自己的工作是服务性的。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与教师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并非是一种人格歧视,而是一种由于工作性质衍生的差异现象。因为教师所得到的较多的荣誉和尊重,是以其较多的心智付出及高度的责任心为前提的。而仔细研究目前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一般的行政工作人员身上,而是出在行政官员身上。是他们中一些人对行政权力的滥用及以权谋私行为,才导致了大学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和泛滥,导致了大学风气的堕落和庸俗。在如何摆正行政权力的位置上,梅怡琦先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他常说:“我就是为教授搬凳子的。”(梅先生绝不会说:“我是为行政人员搬凳子的。”)以梅先生的声望和地位尚如此说、如此做,那我们今天的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掌握了大学行政权力的人,有什么资格对教师颐指气使呢?
三是在作者所阅读到的关于世界大学历史的文献中,并未发现世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时而相互搏弈,时而相互协作”的史实。与此相反,倒是看到过关于“学生的大学”、“教师的大学”的记录。而在这些大学中,行政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学生和教师兼任的,因而根本不存在行政权力的概念。同时,一部世界大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学教授们主导或决定大学命运的历史。因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比教授关于“教授就是大学”的声明,其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可见其是得到世界大学同行们的赞许和认同的。而综观一些作为大学美谈的故事,比如:哈佛大学解聘校长萨默斯、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等决定;牛津大学拒绝阿拉伯商人巨额捐款、拒绝邀请布莱尔首相参加校庆典礼等决定,哪个不是由教师们(教授会)作出的?又有哪一个是由行政人员作出的?这表明在世界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权力是起主导作用的,行政权力根本不具备与其相提并论的条件。
四是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研究语境中,显然存在着两种内涵的行政权力概念。一种如作者前面所述,是产生于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这种行政权力是由大学中的学术权力派生出来的,在大学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下位”的位置,是为学术权力服务的。一种是“两个车轮”理论主张者所说的行政权力,这种行政权力是由我国大学体制产生的特有现象,它不是发源于大学内部,而是来源于大学外部的政治机构的授受,是代表社会的政治机构来管理大学的,对大学拥有指挥、控制、主导、监督等权力。这种行政权力的表现虽然在大学内部,但其权力的源泉却是在大学外部,是大学没有能力左右的。因而不能看成是大学的内部权力,并且与纯粹是大学内部权力的学术权力并列来讨论问题。而“两个车轮”理论的主张者显然是混淆了这两种行政权力的概念,将后一种行政权力当作前一种行政权力来看待,从而出现了一些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理论与将现在大学制度等同于现代大学制度一样,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对现实教育体制的巧妙诠释。只是这种诠释只能起到为现实体制辩护的作用,而无助于大学问题的根本解决。因为授受于大学外部政治机构的行政权力,与授受于大学内部学术意志的行政权力,在活动的价值方向上是不同的。其中,授受于大学内部学术意志的行政权力,由于是由大学中的学术权力派生的,因而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方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就是它们的方向,为大学中的学术活动服务就是它们的职责。而授受于大学外部政治机构的行政权力则不同,它是有明确的价值方向和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学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以满足政治的各种需要。在这种大学行政权力形态下,大学的本质必须是政治性的,政治的目的就是大学的目的,政治的规则就是大学的规则,政治的逻辑就是大学的逻辑。在这种行政权力背景下,大学中的权力结构是反过来的,亦即不是学术权力决定行政权力,而是行政权力决定学术权力。学术权力的大小多少,则全在于行政权力的让渡,与此同时,学术权力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与行政权力相提并论的资格和条件的。在这样的大学管理逻辑中,大学中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将不能是一种自然而然、平心静气、宁静致远式的活动,而可能是在各种“规划”或“工程”驱赶下(还有物质或金钱引诱)的“大干快上”、“做大做强”、“跨越式发展”活动。而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不进行学术造假很难,出现学术造假则是自然的。而这也正是人们呼吁大学去行政化的原因。
与政府管理大学的不断要大学出政绩的思路不同,世界大学的历史表明:大学不仅注重革新,更注重对传统的继承。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特点,不是花样翻新的变化,而是多少年如一日的对大学理念的坚守,是沉稳、宁静、淡薄、坚韧地对传统的维护,是对规律、规则的近乎教徒式的敬畏和尊重。试看历届大学校长论坛上国外著名大学校长的发言,几乎很少有人谈自己大学的规划,而谈的都是大学的理念,大学的普遍原则。因为他们明白,大学只有在办学理念清晰、教育目的合理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和意义。而在大学理念模糊、教育是非不清的情况下,任何技术层次的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整体上落后的命运。而我国大学的问题,或许正在于此。
我国大学的泊来品性质,使其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而这些先天不足所导致的许多误区和陷阱,使我们常常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以非为是且不自知。而对人们长期沉迷其中,但不甚了了的一些虚假理论进行澄清,拨乱反正,是教育研究的职责,也是本文写作的动因。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