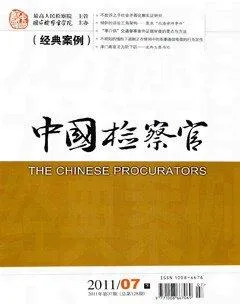从一起案件看窝藏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窝藏罪中“犯罪的人”既包括犯罪之后潜逃在外,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人;也包括正在被司法机关通缉、抓捕的人,还包括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判刑后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服刑的罪犯;帮助犯罪分子逃匿的行为,不仅包括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所或者财物。也包括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仅仅以不作为的形式容留犯罪分子在自己住处住宿的行为,不构成窝藏罪;对于亲友间容许对方在自己家短期居住的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因为没有超出日常生活范围。不应认定为窝藏。
[基本案情]2010年2月13日晚上8时许,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外甥刘某驾驶一辆轿车沿某县城关镇龙山大道由西向东行至经三路路口时,将行人董某撞伤。事故发生后刘某驾车逃逸。董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月14日,刘某来到李某家将其开车撞住人的事告诉了李某,并且说不知道人撞的咋样,当时车速不快,估计人没多大事。2月18日。刘某离开李某家回到自己家。2月23日,刘某听说董某被撞死,遂于次日到其姐姐家躲藏,在其姐姐的劝说下到当地派出所投案。2月24日。公安机关对刘某交通肇事案立案。
本案中,李某的行为能否认定为窝藏犯罪,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窝藏罪中“犯罪的人”如何理解
对于窝藏罪中的“犯罪的人”如何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意见分歧。主要有以下三中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的人”是经过法院审判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刑法之所以确定窝藏罪名,是因为窝藏行为侵犯了国家正常的司法活动。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法院最终判决无罪。窝藏者的行为就没有社会危害性,也就谈不上侵犯正常司法活动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的人”泛指一切有犯罪嫌疑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窝藏属行为犯,其侵犯的客体是正常的司法活动。司法机关在从事公务的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予以配合。无论犯罪嫌疑人最终是否被确定为有罪,都应当追究窝藏者的责任。窝藏明显无罪的人。也应当追究窝藏者的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的人”是在窝藏行为的当时,根据客观合理判断,足以推定为罪犯的人。这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颇为接近。但是认为窝藏明显无罪的人,不应追究窝藏者的责任。如果将明显无罪的人也包括在窝藏罪的行为对象之内,显然有为过分保护国家司法机关正常活动而侵害公民个人的自由之嫌。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司法机关的活动;第二种观点过于宽泛;第三种观点比较妥当。首先,对“犯罪的人”不应作严格限定。“犯罪的人”当然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罪犯”,但不是仅指已经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人。其次,已被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成为侦查、起诉、审判对象的人,即使事后被法院认定无罪的,也属于“犯罪的人”。最后,即使暂时没有被司法机关发觉并立案作为犯罪嫌疑人侦查的,只要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同样属于“犯罪的人”。
综之,窝藏罪中“犯罪的人”应该是触犯刑法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既包括犯罪之后潜逃在外,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人:也包括正在被司法机关通缉、抓捕的人。还包括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判刑后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服刑的罪犯。如果窝藏的对象不是实施犯罪的人,或者根本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只实施了一般违法行为,则不认为为“犯罪的人”。本案中,刘某发生交通事故的第二天到即李某家躲藏。虽然此时刘某还没有被司法机关发现。其交通肇事案也没有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其仍属于窝藏罪中犯罪的人。
二、如何理解“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
根据《刑法》第310条的规定,窝藏罪的行为方式应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但是如何理解“提供隐藏处所、财物”与“帮助其逃匿”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即提供隐藏处所、财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匿。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属于并列关系。帮助犯罪分子逃匿的行为,不仅包括为犯罪的人提供隐藏处所或者财物,也包括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二者是并列关系。窝藏行为的特点是妨害公安、司法机关发现犯罪的人,或者说使公安司法机关不能或者难以发现犯罪的人,因此,除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外,向犯罪的人通风报信,指示逃匿的方向、路线、地点;提供交通便利等,帮助其逃匿的,也属于窝藏行为。另外,窝藏行为方式之提供处所,并不要求所提供的处所一定不为人知。将犯罪人留宿于家中;为犯罪人租赁房屋;介绍至亲友处住宿等等,只要其为犯罪人提供处所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犯罪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均应认定为窝藏。本案中,李某没有帮助刘某逃匿,只是客观上为刘某提供了住处,但是由于“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和“帮助其逃匿”是并列关系,提供处所并不要求以帮助逃匿为目的,所以,如果仅仅从行为方式来看,李某的行为符合窝藏罪提供隐藏处所这一方式。是否最终构成窝藏罪,还要看其行为是否符合窝藏罪的其他构成要件。
三、不作为方式是否可以构成窝藏罪
为了保护人类的自由,刑法以处罚作为犯为原则。处罚不作为犯为例外。处罚的不作为犯的前提是负有作为义务,或者说不作为和作为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通说认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有如下四个方面: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行为人职务、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行为所产生的义务;行为人自己的先前行为具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危险的,负有防止其发生的行为。如使他人跌落水中有溺死的危险。即负有救护义务。
就窝藏罪而言,若肯定不作为也能构成该罪,那么首先就得肯定行为人存在作为的义务。行为人发现犯罪人后。存在积极举报犯罪或者积极向司法机关移送犯人的义务,这显然是对行为人的过分要求,也是对作为刑法基础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而且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识也认为,行为人没有检举犯罪的义务,除《刑法》第311条明文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构成犯罪外,单纯的知情不举不构成犯罪。知情不举是指明知是犯罪分子而不检举告发的行为,因为其主观上没有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窝藏行为,故不构成犯罪。
在没有特定义务来源的情况下,若认为不作为也能构成窝藏犯罪的话,就必须肯定行为人的不作为和以作为方式实施时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而对于窝藏罪来说,难以认定消极的不作为和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窝藏具有等价值性。
我们认为,由于行为人缺乏积极的作为,又不存在作为的义务,仅仅以不作为的形式容留犯罪分子在自己住处住宿的行为,不构成窝藏罪。本案中,李某既没有向司法机关检举揭发刘某的义务。其容留刘某居住在自己家的行为也不具有和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窝藏具有等价值性,故不构成窝藏罪。
四、中立帮助行为与亲属间的窝藏行为
中立的帮助行为,通常是指,日常生活行为或者业务行为本来与犯罪无关。但恰恰客观上对犯罪起了帮助作用的这样一种情形。原清华大学06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陈洪兵先生认为。中立的帮助行为大致分为日常生活行为和业务行为。而日常生活行为又大致可以分为契约型和非契约型两种类型。契约行为是指存在债权债务等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如借贷、租房等民事行为。非契约行为,是指不存在契约关系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如提供吃住、饮食等行为。提供饮食的行为是属于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行为,通常不应认为制造了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不具有帮助行为性;对这种行为评价为帮助犯是对行为自由的过度限制,提供饮食的行为通常不符合帮助犯的客观要件,故不成立可罚的帮助。同样,亲友间为对方提供短时间的住宿、赠与少量财物的行为也不宜评价为犯罪。
所以,对于亲友间容许对方在自己家短期居住的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因为没有超出日常生活范围,不应认定为窝藏。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其外甥刘某到自己家后,容许刘某居住四天的行为,因为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范畴,不属于刑法上的窝藏行为。
综上所述,就本案而言,李某虽然知道刘某可能涉嫌犯罪,而且客观上为其提供了食宿,但是李某既没有检举揭发刘某的义务,也没有使刘某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其容许作为自己外甥的刘某在自己家居住的行为,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范畴。故李某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上的窝藏行为,不构成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