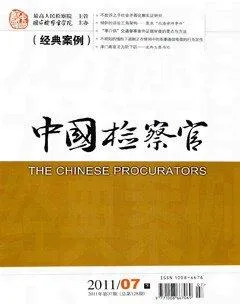李某凯强奸案的争议与分析
本文案例启示:威胁下的帮助行为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但也可能是避险过当。避险过当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虽然刑法并不因为一个人性格懦弱而免除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情况在对其适用刑罚处罚的时候也必须予以考虑。
[基本案情]2011年5月20日新华网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暴温州‘冷漠的哥’被判强奸罪获刑”为题报道了一起强奸案件。报称,2009年12月31日凌晨。李某凯驾驶已承载同村人李某臣的出租车,在温州火车站附近招揽乘客。从外地到温州的少女小梅(化名)上车后,遭到李某臣的强暴。在此期间,小梅曾向李某凯求救,要求他停车。李某凯见状出言劝阻,但受到李某臣威胁。之后,李某凯告知小梅。她要去的目的地——新城汽车站快到了。李某臣叫其继续往前开。李某凯便按李某臣要求,驾车绕道行驶,本来10分钟的路程,结果开了30分钟,从而使李某臣的犯罪行为得逞。此案经当地检察机关公诉后,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李某凯有期徒刑2年。
一、案件认定
经办本案的检察官指出,“被告人李某凯的行为已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突破道德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李某凯明知李某臣在其驾驶的出租车上欲强行奸淫被害人,仍驾车绕路以让李某臣顺利完成奸淫行为,系对李某臣强奸行为的帮助,因此已构成强奸共犯,鉴于其最初并不认同李某臣的强行奸淫故意,后因受到了李某臣的威胁才驾车绕路,故系胁从犯”。口’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显然认可了这一点,承办本案的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被告人李某凯协助李某臣违背受害人的意志,以暴力手段强奸了她,虽然的哥没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但他的行为依然触犯了《刑法》第236条第1款之规定,应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过,李某凯系被胁迫参加犯罪,属于胁从犯,所以应依法‘减轻’处罚”。
检察院的说法重点在于李某凯的行为是“对李某臣强奸行为的帮助”,法院的说法重点在于李某凯的行为“协助李某臣”完成了犯罪。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李某凯之所以被诉和最终被判强奸罪,原因在于检察官和法官认为,他的行为“客观上”为李某臣的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因此属于刑法规定的从犯(胁从犯)或学理上的帮助犯。与实际的强奸犯罪行为人李某臣构成了共同犯罪,根据通行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应该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案件争议及评析
(一)李某凯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共犯
我们认为,李某凯没有与李某臣共同实行或者完成奸淫受害人行为的主观罪过,所以李某凯的行为并不构成强奸罪的共犯。具体分析如下:
1、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的犯罪,李某凯却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李某臣强奸犯罪行为的故意。李某凯事前没有与李某臣进行通谋,没有意思上的联系,在李某臣要对受害人施以强暴的时候,又予以劝阻,可见李某凯到这一阶段都“不认同李某臣的强行奸淫故意”。那接下来后一阶段呢?李某凯劝阻不成,有没有选择停车或者报警,是不是就发展出了帮助李某臣完成奸淫行为的故意呢?我们认为不然。
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但无论是希望或者放任,都应该是行为人主动追求的一种意思表示(我们不妨称之为“犯罪故意的主观方面”)。如果行为人是在他人的强制之下,失去意思选择的自由,只能按照威胁者的意思行动,那么他的行为就不能理解为他自己的行为,那又何来故意可言呢?李某凯正是在李某臣的威胁之下才继续驾车绕路的。虽然如何威胁我们不知道,也很可能只是一般的言语威胁。但被威胁人感受到多大程度上的强制和危险从来都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法律不必也不能要求被威胁人激烈反抗直至达到明显难以抗拒的地步,才认为他的确不是故意要去做某事的,才能免除他行为主观上的罪过。况且就本案而言,从案件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李某凯明显是一个很胆小怕事甚至于懦弱的人,“在警察询问案情时,他总是怯生生地答上一句,甚至都不敢抬头看一眼”,“审判过程中头也不敢抬”,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不上什么的言语威胁,对李某凯来说就可能是极大的恐吓了。并且我们不应忽略,李某凯和李某臣是同族兄弟,居住同村。而不是陌不相识凑巧做成一宗生意的过路人。李某凯不仅知道李某臣是“会乱来的”所以才没报警,而且一旦李某凯见义勇为了,等李某臣接受刑罚处罚完毕后,我们的法律和司法机关又有为李某凯提供哪怕一丝一毫“事前”的保护吗?我们虽然能鼓吹“明知不可为而努力为之”的信念,但却不能阻止李某凯为此而担忧!
李某臣继续驾车绕路的行为,是基于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保护自身利益为重的意愿,虽然折射出了自身甚至整个社会对他人受害置若罔顾的一种冷漠,但毕竟不同于那种遇到强奸案件主动递绳捆绑被害人的帮助犯。区别在于,后者在共同完成对受害人利益的侵害问题上,态度与实行奸淫行为的实行犯是一致的。
2、刑法在共同犯罪一章规定了胁从犯的情形。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刑法也认同共同犯罪存在着共同犯罪人不必要总是存在着共同的犯罪故意。但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不但会破坏共同犯罪体系的严谨性,造成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相抵牾,也是对“严惩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刑事政策的分政策“胁从不问”的一种违背。事实上,胁从犯只有在有可能向主犯(亲自参与到实行行为中去)或者“自从犯”(相对于胁从犯而言,主动实行了帮助行为等)转化,又或者出现以下两种情形:(1)避险过当;(2)不纯正不作为犯(后面将做具体讲述)的时候,才有存在和追究责任的意义,否则以之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则既不能让其心服口服,也无形巾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
(二)李某凯的行为应该如何评价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并不否认李某凯在本案发生的时候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如弃车逃跑(相对后来的刑罚处罚来说,于他为更好)、停车向路人呼救、趁李某臣施暴的时候将车驶向公安局等,使李某臣的犯罪行为能够得到及时阻止,而受害人的利益避免遭到进一步的损害,社会上见义勇为、不惮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风气也可以得到扬清。正因为如此,我们认同李某凯的行为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
另一方面,李某凯在李某臣的威胁下不再劝阻和继续驾车绕路的行为,有紧急避险的含义,因此应遵循紧急避险的一般规则:在两种利益不能同时受到保护的时候,允许牺牲价值较小的利益,保护价值较大的利益:但如果被威胁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人较大的利益时,该行为就超过了刑法可以容许的范围。《刑法》第21条第2款就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我们称之为“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在一般人看来,本案中受害人性自主和不可侵犯的利益显然较之于李某凯仅受到言语威胁的生命、财产安全利益为大,因此李某凯的行为也未始不具有法律上的可非难性。
问题在于,如果从李某凯的行为属于避险过当的角度来看,法律虽然规定了其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但是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中,刑事责任又总是与刑法典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对于违背刑法一般规定的行为并没有规定其刑事责任的多寡和实现形式。实践中,对于避险过当行为的处理,多认定为具体犯罪的过失犯。如遇到某司机驾车避让路上突然蹿出来的一条小狗,却冲上人行道撞死了一名路过行人的情况时,对该司机一般作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理。但过失犯都由法律明确规定。李某凯的行为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受害人性自主和不可侵犯的利益遭到完整侵犯,法律却并没有规定强奸罪的过失犯形态。因此司法机关如何对李某凯这一避险过当的行为进行认定,也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一种合理的评价是,李某凯的行为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刑法典分则条文没有明确将不作为表述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即通常预想由作为予以实现的构成要件,而由不作为来实现的犯罪,或者说行为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通常为作为形式的犯罪。我国刑事立法活动中并没有专门提到不纯正不作为犯。但是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某些条文却体现了把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特殊作为犯的理念,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因此,在面对可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行为时,检察官和法官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惮于运用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
本案中。李某凯对自己的行为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而没有作为。李某凯与受害人事实上存在着运输合同的关系,根据《合同法》第290、301条的规定,李某凯有“在约定期间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达约定地点”,“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遇险旅客”的作为义务,而最终受害人没有“安全”到达目的地,李某凯也难说已经尽到“尽力救助”受害人的义务;其不作为的行为更导致受害人需要直面性自主和不可侵犯的利益遭到侵犯的危险,对此,李某凯应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从行为导致结果的严重性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李某凯的不作为一定程度上可以等价于作为形态的强奸罪。
关键在于“尽力”一词。李某凯在李某臣要对受害人施以强暴的时候有加以劝阻,但是否已经达到了“尽力”的标准呢?李某凯在李某臣的威胁下行为才继续驾车绕路,是否算是尽其所能了呢?就李某凯还有其他办法可供选择的时候,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并不要求个人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去阻止犯罪,他也可以去借助别人的力量。李某凯没有这样做,因此李某凯的行为就可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可以被以强奸罪的名义起诉和判处刑罚(当然。这里我们还要考虑一个人在极端情况下作出理性思考和选择的可能性)。
(三)李某凯的行为应该如何量刑
刑法并不因为一个人性格懦弱而免除他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情况在对其适用刑罚处罚的时候也必须予以考虑。这不仅是辩证看待犯罪构成四要件之间的关系、正确适用法律的要求,也因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行为人,而在于对行为人再次犯罪的特殊预防和对社会其他人犯同类犯罪的一般预防。同时,刑罚还具有严厉性。对于行为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仅会产生拘束行为人行动自由、使行为人财产减损的效果。也可能可以对行为人其他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规定,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根据《劳动法》的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等。刑罚还属于对行为人的一种极为强烈的否定性评价。如本案中,“犯强奸罪被判刑”这样一种评价可能让李某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即便接受刑罚处罚完毕。不明就里群众的非议也能让他难以承受。直接影响他再次融入社会,实现社会转化的效果。因此检察院在建议和法院最后决定对行为人适用何种刑罚处罚和多重的刑罚处罚时,必须慎重。
本案中,考虑到李某凯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悔罪态度、认罪表现以及其行为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特别是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已经因另一起案子的判决(李某臣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得到一定的抚慰等因素,我们认为可以对李某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可以适用缓刑。
三、结语
综上,我们认为李某凯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的共犯,但从避险过当的角度来看,应该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并且李某凯可以因为其行为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缘故,被以强奸罪的名义向法院提起公诉。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建议量刑应轻。虽然法院已经审结本案:李某凯也已认罪服判,但本案仍存在讨论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