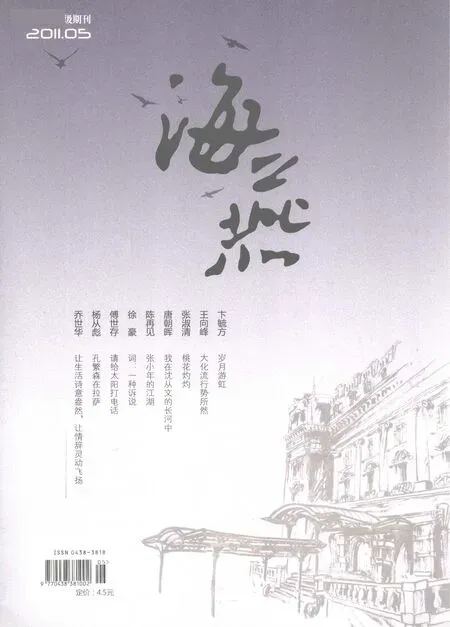我在沈从文的长河中
唐朝晖
我在沈从文的长河中
唐朝晖

唐朝晖
1971年出生,湖南湘乡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心灵物语》、《一个人的工厂》、《勾引与抗拒》等书。散文作品上榜“ 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曾获冰心散文奖。作品散见于《大家》、《花城》、《美文》、《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等报刊。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感觉到自己没有着落,漂着,浮着,也不是有什么悲伤的事情,更不是那种矫情的忧郁,就是无所事事,而,同时,又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当时只是强烈地感觉到生活:不应该这样!至于该怎样?就没想清楚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渐渐明白——生活肯定不应该是现在这种模样。
像很多人一样,我好像在做一番事业,其实,我们都只是落在一个井里,只是在勤奋地不断把井给掘宽些,至于多宽,终究不过井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力,而力都用在对外的物质上、身体上、肉身上,都用在虚华的其他人的认同上。好像是为了证明给某个人,或者某小群人看,证明自己可以做好某件事情,可以把某些事情做得风生水起。风有多大?水有多深?与井底之蛙无异。
风——生,经过树林,吹动那些细碎的枝叶,摇曳着,要不了多久,所有的动作就停止了,树林还是树林,还站在那里。到了我退休的那天,生活还是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更多的年轻人用其他武器和工具走在我们认为那是一条奋斗之路上,重复着我和上辈的生活之路。
一切,似乎与自己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没有太大关系,有限的时间烟灰堙没于生命遥远的地方,无声无息,明知为一种浪费,而无能为力,而冠以风生水起之名。
如果能够破碎成花也好。
最奢望的是:长枪出击、战旗绕长风,这些,真就只是一种奢望。
对于太多事情我无法给予良好的判断,做出让自己彻底欣慰的事情。
只有一点:阅读。阅读是纯净和全能的,可以给至清的水增加无限的深度,可以让浑浊的水静下来。可以让彻底满溢的事物,空出一个回旋的空洞,深入或扩延,植物在空出来的地方蓬勃生长,绿色开始绽放,水在空出来的地方流动。
在绵绵的时空里,阅读帮助我脱离无力的抗争。
在每一个一百年里,都有数百种不同地域的文明,留下几位大师的作品,舒展成阔远的大地,供我自由行走,并享用。
我羡慕那些远行于大地上的知行合一者,他们用故乡的血滋养着自己,用生活中的坎坷,用身体来阅读陌生的、熟悉的大地。感谢他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让我得以与他们深切交流,让我倾听和妄想,他们的身体力行和文字成为我的泉水,滋养着我四分五裂的精神和干涸的河流。
沈从文就是其中一位大师。
他朴实至憨,他的文字是泥土随意捏出来的,文字的世界,泥土的世界,土的气味把我从疯癫的奔跑中唤醒,让我止语,让我停止,让我倾听山在水里的声音,水绕山的绵长。
从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开始,我一次次怀揣着沈从文的文字,行走在那山重水复的湘西,那里有繁杂的人群和静谧的丛山。
我出生于湖南,在湖南生活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湘西的那些河流和重重叠叠的群山,那些隐藏于树林和灌木里的小路,我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机会去游历。那个时候的我,整个身体和心理都处于警觉状态,没有放松过,肩膀、胳膊、腰、头、颈、膝盖、脚趾等主要部位都绷紧着,应对着各种人和事,没有轻松随意地面对大自然,也就无法如水般流淌在沈从文的波澜之地,去感受和呼吸他生命的混合之音。
来北京后的数年里,都会经常打开《湘行散记》、《长河》和《边城》,那片我曾经游历过的土地,在文字的召唤下,在我的身体里复苏,蓬勃而有生机。神奇的土地复活我的记忆,让我无数次醉行其间。
虽久居城市,但一幅幅画面固执地停留在我的头脑里:迂回百转的沅水河,两岸丛山之中,三人撑舟而行,沈从文先生在船上,观村看景,更多的是感慨时态,记忆中的灯火,围柴火而坐的闲谈,火光照亮的那些人影和脸……
1934年冬天,因母亲病重,沈从文从北京回到湖南,乘车到达武陵,即现在的湖南常德。在河边码头,他租了一条小船,沿着屈原和陶渊明曾走过的沅水溯流而上,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沈从文全部在这条船上度过,他每天以书信的形式,告诉新婚的妻子张兆和,他在千里沅水及支流上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想起了什么过往之事。他随性地与张兆和叙说着当时的心境,沈从文也知道,信到张兆和手上的时间,最快也在十天之后,所以,文字隐约之中多了一种自语的成分,想念着妻子,喜欢着这些山山水水,与曾经熟悉的人见了面,有的只有惊叹。船上虽有流动的重叠的千山万水,但更多的还是作者的孤独和寂寞。
在写给张兆和这些信件的基础上改写和梳理,1936年结成一部系列散文集《湘行散记》,成为现代散文的名作,共由十一篇作品构成。
湘西是沈从文的故乡,常德亦属于大湘西概念之中,20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离乡出走,十多年后再返故里,旧时的那些人与往事,一一重现于激情的现在。
《湘行散记》头篇是《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沈从文由常德去桃源坐船之前,坐的是一辆公共汽车,由这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陪着,这是位懂人情而有趣味的朋友,也是位风流的主,对画有些了解,他是专程来陪沈从文走一段路程的。
沈从文的作品是立体的,不是单纯的游记和风情,有他自己的影子,有回来数十年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经历,有湘西特有的人文情境,语言也是湘西的味道,不是纯正的普通话。他笔下的那些水是轻灵的,山是重的,生长着枝繁叶茂的古树。
他用文字随意地营造着或空旷或幽暗的时空,荡荡回回,从现在的公车汽车,回到十三年前的那个小镇。
他的每一篇作品中,基本都有一位个性鲜明的与他有过数次交往的朋友。每次都会出现在他触手可及的视野中,或者是可视的虚空之间。
沈从文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桃源河街附近的船码头上,与人讲好价格,船总写好了保单,一切就绪,第二天就出发,开始他的船上生活。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规矩行市和路数。
常德、桃源于我太熟悉不过,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妻子就是常德临澧人,我孩子的童年时光就是在常德度过的。1931年沈从文与丁玲营救胡也频没有成功之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的就是湖南临澧县,现在每次回湖南临澧,总会经过丁玲公园,也会在丁玲广场上转转。
因为我太执迷于沈从文的语言和他所写的作品,无数次梦想着跟随从文先生文字去他曾经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用文字回应他,告诉他,三五十年后的湘西的模样。《湘行散记》的魅力,船,成为我用行动跟随沈从文的一种方式之一。船,随他的文字走一遭。从河流到城镇,沈从文在湖南的飘荡、游历所经之地,我都绘成了地图,随时准备租船而重游。回去了几次,探听到河道上建了几个水坝,修建了几个光荣的水电站之后,沈从文亲历过的几个小镇、山水码头和风景,如青浪滩、寡妇滩等诸多村镇、风景都已经沉没于水库深处。
遗憾沉痛,但我依旧深爱这条河流,这是一条诗歌的河流,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屈原曾生活于这河边,也曾乘舟于这沅水之上,河声也回响在《楚辞》里。沈从文在《湘行散记》的《桃源与沅州》篇中写道:
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估想他当年或许就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花香草的沅州。
沈从文以写流浪军人,湘西底层劳动人,以及求生存的性情妓女为主,写花草不多,而在这里有一小段对香草香花细致入微灵动的描写, “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文字一改那种“土”和至朴,而以细微、雅致亮相。
包括陶渊明的退隐,也在这条河流上。
在那些土得掉渣的文字里,文化的厚重与轻灵浑然一体,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作家的思考和反省不动声色地融于其中,农民抗争的鲜血,杂草的湮没,四十多位牺牲者被抛入屈原所称道的河流中,这一切,被流动的水永远存封。沈从文说,本地人大致把这件事也慢慢地忘掉了。
作家不玩文字的,作家的灵魂的眼睛是应当明亮的,暗而复明,黑而复亮,是循环着的,不应当只是沉迷于山水的险奇峻峭,沈从文的深度和激情深含于文字中,不外露。
船到沅州,水手们上岸买些烟丝,对话和场景,都真实可摸。
从文先生喜欢这些底层活生生的水手和生意人,远胜那些寻幽访胜的知识分子,底层生活的丰富性,远胜那些编造的戏剧效果。
在《鸭窠围的夜》,沈从文的船在河上行了五天。下雪了,南方的冬天寒冷彻骨,何况是在河上航行,冷的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是我走这条水路,万不会是冬天去的。夏天再热,因为有水上的凉风,倒是另有种享受的。
在冬天的河流上行进,做生意的、运货物的、接送客人的船,冷的夜,让水手更加孤独。大大小小三四只船,拥挤着停泊,到这样一个有人情味的小镇码头,水手们纷纷上岸寻找些特殊的女人,吃“荤烟”,更多的只是去烤烤火。那些屋子里的主人,大有背景和历史,有退伍的军人,有运气不好的老水手,有寡妇等等。
那时烤火的方式,是典型的南方乡里烤火的方式。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是这样烤火的。在屋子中间浅浅地刨一个小坑,在上面架些树根树块,柴火的温度远胜过所有的取暖方式,乡里人常说,柴火温度上身快,可以驱除湿气。
沈从文的过人之处在于:突然之间,在虚虚实实的场景中,把一个人、一群人,更多的是一代人、一类人的不可思议的生死和生存环境细细地梳理成章。这些烤火屋里的主人不会有名字,河两边码头镇里的人们也没有名字,但成百个不同人物的命运都会浮现出来。
文章中写到一些美丽的有想法的女孩,因怀上外乡人的孩子,被沉潭。这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审判的族长、围观的乡人、推她下潭的人,都是主角,让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看和沉重的份。

我们再回到这烤火的屋子,里面有些小细节,屋子的木板墙壁上,会有大大小小、红红白白的军人、团总、催租吏、木排商人等头衔的名片,我想到现在一些有小情调的酒吧,也是名片和随意的签名留言,制造些文化的氛围。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这是唯一一篇以时间为标题的作品。因为这天,船将到达沈从文充满了浓郁感情的辰州。
他在离辰州约有三十里水路的船上醒来,他是被一个极熟悉的声音喊醒的,人醒了,那声音还在耳边,原来是辰州的河水,足见辰州在沈从文心中的重量,非一般文字可说的。
他写到另一条搁浅的船上的水手,跳进水中,试图用肩之力让船离开沙滩,但浪咆哮着卷走了水手,其他人在岸上追几步,人便不见了,一个生命在水中消失,于水手而已,这是常事。因为太平常,而震撼人。这样的险滩与长长的激流,较多。
船过了滩和激流,进到平静之处,沈从文坐在日光里,他离开辰州十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故乡。
沈从文离开家乡之后,就停顿在这码头上,他熟悉辰州的每一条街和每一个店铺。
他温暖地爱着这条河里的船和船里的人,那些日夜流着的水,和沉于水中的小石子,还是那样细碎,他的开悟和智慧,都源于这里。
沈从文写的就是他的生活,生活中就有那么巧的事情。在多篇文章里,他都会笔墨较多地写到一个人。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文如其名。第二天清早,沈从文的船准备出发了,他的目光和心思落在一个叫牛保的水手上。这些水手待船一靠岸,就有一部分人上吊脚楼与相好的妇人去睡一个晚上。他们感情复杂,说是露水恩情也可以,说柔情万种也对,从这些妇人身上,可以依稀从今天的湘西女人身上找到。沈从文眼中的这些妇人,没有半点脏的感觉,有的,只是分别和快乐。牛保的阳刚之气和腼腆之情,留于纸上。沈从文给了牛保四个苹果,他又再次跑回阁楼给那妇人,其间感情和分享的爱意跃于联想中。
这一天,沈从文的船全部在上滩,他欣赏着船舷边奔涌的白浪。船,下午在一个叫杨家岨的地方停靠,这里不像其他地方停靠的船多,好像就他们一条船,沈从文有些担心船上的水手下黑手把自己给黑了。不久,后面来了一邮船,与一小伙相识,在岸上一人家里烤火,突然进来一位让沈从文惊艳的妇人,名为夭夭,夭夭打听着牛保的消息,也对沈从文这位京城里的人有些羡慕。
沈从文在不经意间,把生活中的杂质在文字的河中洗涤掉,留些相关联的事件,用文字串起来,就有那么巧的事,而远比那些发生在影视里的喜剧效果来得有趣。
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只是被太多的琐事所遮蔽。
沈从文几百字描写夭夭妇人,一个水灵灵的夭夭就落在纸上,尤其夭夭在文章结尾唱的那首《十想郎》,是给谁听的?牛保?沈从文?或者是天性的爱唱和打闹而已,都可以想象。
十天了,沈从文一直坐船而上,他也比较集中地写了这些将与他共同度过二十多天的水手们。他知道那年龄较大的掌舵者是八分钱一天,拦头的水手是一角三分,那个学徒小伙计一分二厘一天。这条河上有十多万人这样过日子,可见那时的河流,以及两岸是何等的繁华。
沈从文的丰富在于他进入了身边人的世界,从水手大伙计的过去,到现在的憨实,读来生动。
在船舱里,我与沈从文一起等着黄昏的到来,触及伤感的向晚,看阳光幽淡。没有辰河上的奇异光彩,没有人生的沉浮颠覆,就不会有《九歌》的惊魂。同样,没有至朴的水手和吊脚楼里的乡亲和妇人,也就无从有沈从文那波澜不惊的《湘西散行》。
十二月七号,沈从文来到他十五年以前来过的箱子岩。那些曾经的记忆,依旧萦绕于树林和丛山之中。看着那些刚下水的船,他要水手们把船停泊在十五年前待过的地方,在一家小饭铺里,他与一群正直的乡下人一起烤火,谈他们的生活,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回来了。说这里是“小饭铺”,用这样的名词表述,应该只有湖南南方才有。那些可以吃点饭的地方,只卖点小小的生活用品,如小酒、小烟、盐和味精的小店子,就叫小饭铺。有些也指可以住宿的地方,共同点是,来往的人多为附近乡邻,经过这里喝喝茶,聊聊天,烤烤火,说说闲话,顺便买点家里需要的小东西。这样的小饭铺,遍布湘西的各个小小的交通点。基本是不会有外地人。人们坐在一起,每次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某一件事,或以一个人为主要话题,所有的褒和贬,都不是恶意的,最多的是在调侃中带些羡慕和批判。乡村的很多道德也是这里的一些强势人说出来的。
沈从文那次看到了跛脚什长,出现在小饭铺里,这是一个乡村居民的灵魂性人物,战争、残疾、生意、倒卖、烟、玩花姑娘,都是他的关键词。沈从文就在这些亲历中,用湘西的口语写活一个个湘西大山里的人。似小说,而不是。似传奇,也不是,都是生活中的大活人,真真实实。沈从文深切的感情浓浓郁郁地怀抱着湘西的绿色。
政治、军阀、反抗、民风,沈从文一一写到。
在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的“题记”中,沈从文的船一入辰河,他就感觉到一切变了,一切在变化中堕落,山里人正直朴素的人情味几近消逝,人们的敬畏之心随着破鬼神的动作而消亡,现代的文明肤浅地在这里如码头的垃圾,漂浮水面。也有一些公子哥们花着祖宗的钱,在外面游乐,享受现实的腐朽部分。深刻的思想和学习,是没有的。
批判中更多的是痛惜。
责任编辑张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