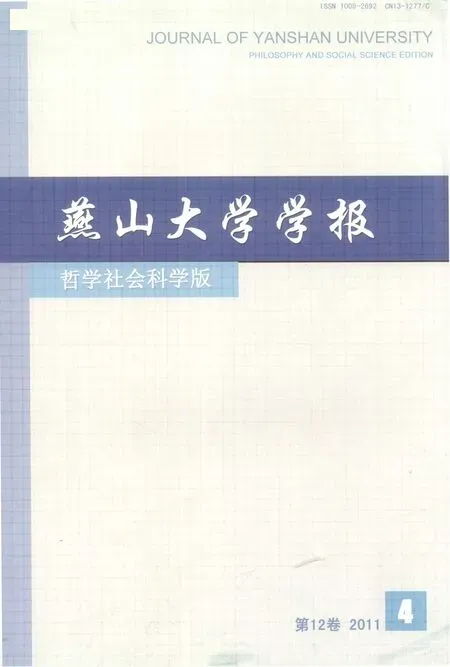普特南的意义理论探析
张高荣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意义理论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普特南提出劳动的语言分工、因果指称理论、科学本质主义等一系列主张,在英美哲学界激起强烈反响,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该理论也不断地遭到质疑与批评,迄今仍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国内学界对这些批评也有所附和。笔者认为,进一步全面理解和系统把握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对于回答这些质疑与批评,深入把握普特南意义理论的重要价值,仍是非常必要的。
一、意义不在头脑之中
普特南的意义理论的形成缘自他的语义学研究。普特南认为,传统的语义学所处的境地非常糟糕,原因是语义学所依赖的“意义”这个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给语言哲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以至于像奎因(W.V.Quine)那样的怀疑主义者在同“内涵论”论战的过程中宁愿放弃“意义”这个概念。但在普特南看来,对“意义”采取怀疑主义态度丝毫无助于对该概念的澄清,并且指出意义概念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而内涵论只不过是一条通往这种概念的完全错误的途径。与戴维森(D.Davidson)等人所持的立场不同,普特南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词的意义而非语句的意义方面。他认为,传统的意义理论关于语词的意义的观念所显现的问题更为严重:“我的讨论将几乎完全针对语词的意义而不是语句的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关于语词意义的观念,要比我们关于语句意义的观念更有问题。”[1]216
通过对以往学界有关研究的反思和批判,普特南认识到,传统的意义理论主要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1)知道一个词项的意义,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 (2)词项的意义(‘内涵’)决定它的外延(相同的内涵意味着相同的外延)。”[1]219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任何词项都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假定。因此他断言,传统的“意义”概念是建立在错误理论之上的。
弗雷格(G.Frege)和卡尔纳普(R.Carnap)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认为,意义是某种公共的属性,同样的意义可以被不止一个人掌握,而且可以被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掌握,因而,他们把意义(内涵层面上的)等同于某种抽象实体,而不是心理实体,并以这种思想来反对传统的“心理主义”。但是,普特南指出,以弗雷格、卡尔纳普为代表的所谓“反心理主义”并不彻底,因为“‘抓住’这些抽象实体活动本身,仍然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行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人质疑如下事实:理解一个语词(知道它的内涵)就是处于一定的心理状态之中。”[1]218
根据传统的意义理论,心理状态的“公共性”意味着,如果张三与李四对词项A的理解不同,那么他们就一定处于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他们知道I是A的内涵这种心理状态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张三与李四的心理状态相同,那么他们对词项A的理解也一定相同。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决定着A的内涵。因此,根据上述假定(2)可得,心理状态也决定着词项A的外延。
普特南指出,假定(1)与(2)合起来就肯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两个人所处的心理状态完全相同,但他们所说的 A的外延却不相同。故而心理状态不能决定词项的外延。对此,普特南借助三个思想实验做了论证。
第一个思想实验就是享誉学界的“孪生地球”说。设想在1750年前近代化学尚未问世之时,除地球外,还有一个与地球几乎完全相同的孪生地球。孪生地球上的液体和地球上的水看上去一模一样,用起来也一模一样,但其分子结构却不是H2O而是 XYZ。但是,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在孪生地球上,人们当时都不知晓这一点。因此,很难说地球人与孪生地球人对于这两种液体的心理状态有什么差异。但是,他们所说的“水”,一种是指H2O,而另一种却是指XYZ;它们的外延显然是不同的。这表明决定语词外延的不是个人的心理状态而是客观环境。
第二个思想实验是关于“钼”和“铝”这两个词项的。除了专家,一般人区分不出钼制锅罐与铝制锅罐。普特南设想,钼在孪生地球上就像铝在地球上一样常见,而铝在孪生地球上却像钼在地球上一样罕见;在孪生地球上,“铝”锅罐是由钼做成的,而“钼”和“铝”这两个词刚好调换了位置:“铝”实际上是钼的名字,而“钼”实际上是铝的名字。假如张三与李四分别是地球与孪生地球上的说共同语言者,他们在化学或冶金学上都是门外汉,那么当他们用“铝”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在心理状态方面可能没有任何差别。然而,我们必须说,他们说出的“铝”或“钼”分别指的是不同的外延。因此,普特南认为,他再次证明了说话者的心理状态不决定语词的外延。
第三个思想实验是关于“榆树“与“山毛榉”这两个词的使用。普特南指出,除了专家以外,普通人都分不清榆树与山毛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我所说的“榆树”与其他任何人所说的“榆树”具有相同外延,即所有榆树的集合;同样,所有山毛榉的集合也是人们所说的“山毛榉”的外延。这种外延差别不可能是由我们在观念上的某种差别而造成的。因而,在确定什么是榆树什么是山毛榉时,人们的心理状态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普特南断言:“无论如何,‘意义’不在头脑之中!”[1]227
二、语义外在论
如前所述,在确定什么是榆树什么是山毛榉时,不能凭据我们的心理状态。普特南指出,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助于专家,求助于社会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这表明,不是个人的心理状态,而是社会的分工合作以及客观环境等决定了语词的意义。因此,普特南把自己的语义理论称作“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
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的核心思想在不同文献中有不同的描述。从否定的维度看,语义外在论的核心思想是:词项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不是模棱两可的;个体的心理状态不能决定外延;原则上,孤立的个体不能掌握任何概念;某个个体所掌握的概念不能完全决定其他所有个体掌握的语词的外延;关于意义的知识不是私有财产;“我们最好不要把意义想象为实体,或者根本就不要把它想象成像对象那样的东西。”[2]18从肯定维度看,语义外在论的核心思想有三个关键点。其一,在意义主要是由指称所决定的角度说,“意义”概念是涉及对象或者现实的;其二,意义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社会特性;第三,“我们对于意义、概念和信念的个体化,以及它们对于什么是真的,都是由并且应当由一定范围内的涉及文化和环境的因素来确定的。”[2]18
语义外在论将人们探究语词意义的思路由内在心理状态转向了外在环境和社会,将指称在确定语词意义过程中的地位凸显出来。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环境和社会是如何确定指称从而决定了语词的意义的呢?对此,独立于克里普克,普特南提出了著名的因果指称理论,以及语言分工(divisionoflinguisticlabor)和科学本质主义主张。按照传统的观点,任何非空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知道意义”就是拥有关于内涵的知识,理解词项是一件获得知识的事情。与一个词项有关的充分的语言能力和理解一样,都是关于知识的事情。但是,根据普特南的因果理论,这些观点都是根本错误的。“语言能力和理解不仅仅是知识。拥有完整的通常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一般并不足以获得与一个名词有关的语言能力,人们必须与某些典型的情况(即该名词的指称通常在其中出现的那些情况,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有某种恰当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种理论才被叫做意义的‘因果理论’。”[3]341
在谈及物理量名词“电”时,普特南指出,许多使用“电”这个词的人知道电是某种量值。但电曾一度被认为可能是一种物质,热也是如此。现在谈论电和热的说话者假定“电”和“热”是可测定的物理量。普特南认为,即便如此,使用“电”这个词的多数人除了知道电的少许性质外,未必了解“电”的本质属性。这样一来,对于“电”的充分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该领域的某些权威专家。富兰克林知道“电”是以电花和闪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他人也许对电流和电磁铁有所了解,还有的人也许知道原子由带正负电荷的粒子组成。他们都可以使用“电”这个词项,而不必有一种他们共同指认的“内涵”。“他们每人都通过某种因果链条与电的描述情况相联系,这种描述通常是一种因果描述,即把电挑选出来作为以某种方式而造成的某种效应的那种物理量值的描述。”[3]342人们可以由不同途径学会使用“电”这个词项,这里的因果传递链条可以是复杂而漫长的,个人有时根本无法追究它的来龙去脉,但这并不重要,社会、历史帮助人们与这一链条联系起来。比如,一旦“电”这个词被引进一个人的词汇中,那么“电”的指称在这个人的个人语言中也就固定了,即使他并不知道自己已固定了指称。而一旦固定了指称,人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词来构述任何数量的关于该指称的理论,而不使这个词在不同理论不同层面上成为一个不同的词。
与克里普克一样,普特南也注意到自然种类的名称与专名起作用的方式比较相近。他反对名称具有传统的意义理论所认为的那种意义的观点。按传统的意义理论,名称的意义可以通过还原为其所指称事物的一系列性质的合取来给出,例如把“柠檬”分析为“色黄”、“味酸”、“皮厚”等等。普特南认为,人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把分析“单身汉”这类“单一标准概念”的模式机械地照搬到自然种类名称上的缘故。“单身汉”有一个显在定义,即“没有妻子的男人”,但“柠檬”却没有这样的显在定义。在反对把自然种类的性质当作其名称的意义的观点时,普特南谈及“正常成员”和“非正常成员”。发白的柠檬还是柠檬,三条腿的老虎仍然是老虎。普特南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自然种类所指事物的外延不是由一组“语义规则”来确定的。这些规则仅仅可以确定一种事物的范型(stereotype),但不能确定它的外延。人们不能描述老虎或柠檬的一切状态,但可以对一只典型的老虎或柠檬进行描述。与其他本质主义者一样,普特南也承认一个自然种类具有本质属性。不过,对于自然种类的本质属性,普特南认为,“那不属于语言哲学家要回答的问题,那是一个科学理论构造的问题。”[4]592如何决定不同事物的本质属性,要看那个事物属于哪个领域,即其本质属性由那个领域的特定研究来决定。这就需要诉诸于语言分工。
自然种类的本质属性或者内部结构不是经验外显的,语言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不具备识别这种本质属性的能力,因此,普通成员不能借助于本质来确定自然种类语词的指称。但是,语言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究竟是如何成功地确定这些自然种类的指称呢?普特南指出,这是由于语言具有社会性。社会生活中存在不同的劳动分工,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从事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研究,因而,不同的人对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的熟悉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他认为,普通的劳动分工导致语言分工:“任何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只要黄金对他很重要,他就必须掌握‘黄金’这个词;但是,他没有必要掌握辨别真假黄金的方法。他可以依赖一些特定的说话者。一般认为与通名有关的那些特征都有存在于被当成了集合体的语言共同体之中;不过,这个集合体将知道与使用‘金子’这个词的意义的不同部分的工作进行了分工。”[5]465也就是说,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金属专家精确地掌握了“黄金”外延的理论和技术。语言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之所以能自如地使用像“黄金”这样的语词,正是依赖于这些专家。为此,普特南提出了他的“语言分工假说”:“每个语言共同体都表现出上面所说的那种语言分工,也就是说,至少拥有一些词汇,与之相关的‘标准’只有少数掌握它的人知道,而其他人对它的使用则依赖于他们与上述少数人的有条理的分工合作。”[5]466传统意义理论不能解释的情况,按照这种语言分工假说,却可以对之做出合理解释。在普特南的这个主张里,有没有专家不是主要的事情,关键是分工和集体性;指称不是由个人理解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共同体的能力决定的。普特南还间接地批评了维特根斯坦在列举工具来比喻语言的时候,只列举了个人使用的工具,他认为应该用轮船之类需要分工协作才能使用的工具来作比喻。
三、语词意义的确定
基于上述探讨,普特南提出了自己关于如何确定语词意义的理论。他认为不可能找到一个与意义等同的东西去定义“意义”这个概念,而只能对意义做出一般形式描述。在普特南看来,对一个词的意义的一般形式的描述,应该是一个有限的序列,其成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适用于这个词的句法标志,比如“名词”;(2)适用于这个词的语义标志,比如“动物”、“时间段”;(3)对范型的额外描述;(4)对外延的描述。语词范型在确定语词意义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范型”是一个惯例性的观念,它告诉人们 X长什么样或者行为方式如何。比如,如果一个人要成功地掌握“老虎”这个词,就必须知道典型的老虎是有花纹的。更准确地说,他必须知道关于典型老虎花纹的范型,并且还必须知道这个条件是强制性的。
在语言共同体内部,若要成功交流,知道“范型”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可以说,知道“范型”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但是,普特南同时强调,对于语言共同体来说,关于事物基本特征的描述,范型描述并不是分析真理,它是一种从经验中概括出来且可以修正的:“一种特点(比如花纹)被包含在关于语词 X的范型中,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些命题是分析真理 三条腿的老虎和患了白化病的老虎,并不是逻辑矛盾的实体。”[5]495普特南指出,范型所规定的正常成员的标准是可变动的。这是普特南的意义理论与弗雷格型传统观点的一个基本区别。按传统的观点,自然种类语词的意义等同于关于自然种类语词的定义,而自然种类语词的定义则是一组性质的合取,比如“柠檬”的意义可以通过详细说明一些性质的合取而给出,如色黄、味酸、皮皱等;这些性质对于柠檬的分析为真,是不可改变的,它规定了柠檬和非柠檬的严格界限。普特南认为,如果按照这种传统观点,绿色的柠檬(在黄色为“正常描述”的情况下)就不再是柠檬,患了白化病的老虎就不再是老虎。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总之,“对于范型的认识可以概括为,这是一种基于当下经验概括的对于理想化状况的描述,它只有约定方便的性质,不可把它看作是对‘范型’的‘理论说明’即分析的说明。”[6]
显然,在确定一个语词意义的四个要素中,“句法标志”和“语义标志”是人们使用语言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知识。因此,普特南对它们没有过多的讨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做出系统总结。(1)关于语词意义的本身的分析,普特南颠覆了传统的意义理论,指出知道一个语词的意义不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意义应该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把握。(2)关于日常生活中如何确定语词的意义从而使用语词,普特南指出了确定语词意义的四个基本要素:“句法标志”、“语义标志”、“范型”和“外延”。这要求人们必须对语词的范型、语义标志和句法标志具有最起码的基本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要素并非并列、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是前三个要素(“句法标志”、“语义标志”、“范型”)合起来与最后一个要素(“外延”)处于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之中,而在这两方面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外延起着决定的作用。(3)普特南反对把语词的意义当作使用者个人事务的倾向,以及忽视世界的倾向。因为忽视语言分工就是忽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了来自环境的贡献。普特南认为,传统语言哲学家之所以出错,就是把社会共同体和世界抛在一边了。因此,对于一种正确的意义理论来说,必须考虑语言使用者与社会共同体及世界的相互作用。
[1]H.Putnam.Mind,LanguageandReality[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2]YemimaBen-Menahem.HilaryPutnam[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3]普特南.说明与指称 [M]//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 英美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88.
[4]普特南.语义学是可能的吗? [M]//马蒂尼奇.语言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普特南.“意义”的意义[M]//陈波,韩合林.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6]陈亚军.意义何以可能——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解读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