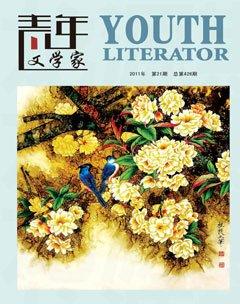师陀小说中的乡土空间书写
摘要:乡土意象是师陀空间书写中最突出的意象。田园空间和小城镇世界是其乡土空间书写不可或缺的两方面。师陀向我们展示了空间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意义,而其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展示了空间文化圈如何决定了人以及社会群体的心理结构,揭示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恋乡”和追寻本源的情结。
关键词:师陀乡土空间
作者简介:温泉(1979-),女,汉族,湖北荆州人,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教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029-02
“文学空间”和“文学景观”的说法是近年来空间理论的产物。1998年,麦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中曾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他的主张如下文学景观最好是看作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文学景观也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客观的地理空间,提供一种情感的呼应。相反,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了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文化的景观。师陀的文学空间正好是这样的一个范本。师陀的作品里充斥了大量的空间意象,有代表性的如中原故土的“浮世绘”、诗意盎然的“果园城”以及喧嚣的都市上海等。
乡土意象是师陀空间书写中最突出的意象。田园空间和小城镇世界是师陀乡土空间书写不可或缺的两方面。
1、纯粹田园空间
首先,充溢在田园空间中的是无限美好且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观,这里充满了各种光亮、色彩、芳香,还有天籁的声响。不管春夏秋冬,四时节气,作者展现给我们的都是一幅活色生香、丰沛盎然的景象。试欣赏以下小说片段:
“抖的一闪,是火一般的桃,烟雾似的棠梨,鹅黄的菜田……滑行着。一个颠摆,娇滴滴的阴影下来……”(《乡路》)
“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特有的香气,天空是蓝的,高的,耀眼的。阳光温暖地照着阅无一人的院落,一点声音都没有。”(《同窗》)
“阳光好像细粉,薄薄的敷满了果园,透过树木的枝叶,斑斑点点地洒到地上。春意融融的拂过人的眉梢,草的尖梢。”(《春梦》)
色彩、光亮、香气、大地,师陀笔下的自然生命是多么令人欣喜。
我们再来看动态的自然。在师陀的作品中,动物的身影如同植物一样随处可见,而且情态不一、可爱至极。比如青虫是“荡着秋千”,鸡或鸽子是“娴雅的叫”,狗白天打一着奸吹,晚上则“徉吠儿声”,好像对人说“我在这里”。并且狗还会笑出声。驴子更有个性,如果他决定撂挑子不干,则一定是副打骂不怕,死乞白赖的“痞相”。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师陀对自然界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描绘。白杨翠柳,枣子红了,桃花是火一般的,稻田是鹅黄的,郊野是茵绿的,村庄是苍蓝的,天空是翠色的,日出日落各有其彩银红,晕红,金黄,橘红……
另外,师陀作品的暖色调还表现在对大量绿色生命的描写。没有一部小说中有如此之多的芳草芝兰,瓜果菜蔬。麦门冬,龙舌兰,蜀葵,番柿,凤仙花,桃李,棠梨,鲜枣,沙果,花红,还有最平常亲切的红薯,毛豆,葛芭,菠菜,韭蒜,黄瓜……这些美丽的生物,像植物博览一样在我们眼前动,展现了生命的蓬勃葱茏,展现了大地给予人的恩惠和启示。师陀是用最纯净的怀念笔调来写他这段乡土记忆和自然体验的,好像那是个在现实中失落、在心理空间中永存的家园一样。
其次,与自然交织在一起的还有美好的人伦和人事。天伦之乐不外乎夫妻、父子母子、兄妹、祖孙这几对关系。《病》是师陀少有的回忆童年的作品。在这里师陀用一种电影的技法,营造了一幅温暖芬芳的天伦之乐图。如《落日光·序》中,祖母用林黍梗替孩子们编了模筐,每天早上往里面装了蒸熟的红薯、毛豆、鲜枣,足够孩子们冶游一天……
2、小城镇空间
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中,除了特质显著不同的现代都市和内陆乡村以外,二者之间还夹杂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空间,那就是“小城镇”。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作家皆生长于小城镇,如鲁迅、沈从文、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废名、萧红、路翎、师陀、施蛰存等等。生于斯、长于斯的特殊因缘关系使得“小城镇意识”无形地渗透在作家的血液当中。不论是出于批判、欣赏、留恋还是其他原因,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在文学叙事中以小城镇为背景,甚至为文学角色。
师陀笔下的小城镇有一种惰性。作家在小说中故意淡化了作品的时代性和时间性,突出了稳定文化内涵下导致的一幅幅静态的生活图景。比如果园城从清末到民国25年,虽然遍经沧桑,却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一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蔚”。果园城“成为一个封闭、落后、悲伤的生存空间”。它们的世界自成一体,外面的工业文明、挣扎与竞争丝毫影响不了这里的依然故我。在师陀笔下,果园城是真正的主角。
师陀小城镇居民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多余人,包括果园城子民葛天民、孟季卿、素姑、徐大娘,还有周易安《恶梦》、快乐的人快乐的人等。他们有的是乡村知识分子,有的是老处女,有的是孤独的老人,有的是曾经的革命积极分子。虽然身份不一,但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失去希望,生命变成了一个空壳。
这里的人似乎衰老的格外快。葛天民,一个有才一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他已經自以为老了,说话总喜欢用“我们那时候”开始。这里的人也特别容易胖。“安乐公”孟季卿,“时常有人看见他在街上走过,穿着又宽又大的袍子,满身油垢,挺着肚子很费力的摇曳过去”;周易安,“他的全身散发出一种平凡的肉感气息,他挺出的肚子仿佛说一切都恰恰满意。”这里的人的标准姿势是“凝望”。素姑“惆怅的望着永远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孟季卿,“他的眼睛老茫然望着空中”徐大娘的目光也“转到别处,望着空中”。同样的表情,同样的悲哀。果园城人心中的天空飘着的是他们永无可能到来的幸福和对逝去生命的悠远的回忆,映衬着今天生命的衰败和亮不起来的生命的灯。那是果园城人的痛苦,也是师陀的痛苦。
二类是恶势力。这些小城有它安宁和平的美,如果园城的秋天和秋天般的寂静。但小城也有它的丑恶和败落。师陀笔下,丑恶的代表就有果园城主“魁爷”朱魁武(《果园城记·鬼爷》)、百顺街上的人称“阎王”的缉私队长(《百顺街》)。
魁爷在家里是封建君主,他的深宅大院仿佛皇宫一样幽禁着他娶来或抢来的四位老婆,仆役们必须把心提到嗓子眼做事一一稍有不慎,他就把她们剥得赤条条的,吊起来,然后用专门给她们准备的鞭子抽打。在外面,他掌管了果园城人一切的诉讼、权益、生死,是果园城货真价实的土皇帝。“阎王”的确姓王,他有着巨大的胃口,他的马鞭就是他的名片。他还豢养着一班壮丁,一队肥壮如龙的马匹。壮汉们全是劫盗、流氓、恶棍、土匪出身。而王爷的龙驹即使在集市上亦能野奔,“以致踩死了棺材铺主的老爹。一幕幕恶行令人心寒。”
这些先辈的权势者,不到他们二世、三世的子孙把家业败光是不会彻底淡出人们的记忆的。由此,诞生了小城镇第三类居民形象—败家子。师陀笔下的败家子、浪荡子实在太多了,光《果园城记》中就有刘卓然(《刘爷列传》)、胡凤梧(《三个小人物》),另外就是《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等。
画册式结构、独特的情调与意境、浓烈的抒情性构成了师陀独特的空间型叙事文体。通过这样的空间书写,师陀向我们展示了空间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意义,而其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展示了空间文化圈如何决定了人以及社会群体的心理结构,揭示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恋乡”和追寻本源的情结。
在现代文学史上空间的书写其实早已有之。乡土空间书写有老舍的北京城、废名的“竹林”、沈从文的“湘西”等,都市空间的书写上,茅盾、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但师陀的“乡土空间书写”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意义。
1、空间书写的生态意义
所谓生态伦理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伦理自觉它表达的是人对理想匕存的渴盼。20世纪中叶之后,“回归自然”成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并且这种回归不是中国老庄思想的重复,不是18世纪法国“卢梭式”的浪漫怀旧,它所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状况和生存意识的新的转折。“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的家园”成为我们一致的认识。我们看师陀的乡土作品,总是能很强烈地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和谐与美好。在师陀的生态叙事中,有三种生态画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类是人与动物、人与神和谐共处的画面。我们看《老抓传》里师陀向我们展示的人畜共居的感人至深的一幕:
“一到晚上,老抓将食物弄进来,畜生们欢迎了他。牲口在槽上慢慢地嚼,他在槽下慢慢地嚼,狗这边嚼,猫那边嚼,情形象一个小家庭。他的猫狗也和平相处,从不相打。”
这里,人畜各就其位,各安其分,但又如家庭成员般完美和谐地组织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通过这种想象和摹写,师陀是在表达他对生命伦理的理想吧。
第二类感人的生态画面是山民道家般淳朴的生活。如《老抓传》中的老抓,《行脚人》中的老店家,《果园城记》中的葛天民,无不透射出这样一种气息或理想。
第三類生态画面充满了酒神般的欢乐和力量感。它青春明亮、小有破坏和创造,是人和自然原始生命力的爆发。《果园城记·阿嚏》中的水鬼阿嚏就是典型的酒神角色。首先,阿嚏是打着呼噜出场的。被老渔夫一脚瑞下水后,他打了两个好响亮的喷嚏,然后光身子爬上岸,水淋淋的置于月光和我们的视野下。其次,阿嚏的戏弄劲头十足。他报复了瑞他的老渔夫,使他处于不成器儿子即将中举的臆想和癫狂之中。他还戏弄了一位贪心的老财主,还有一位好色的秀才。原来阿嚏戏弄的只是卑微的人的不切实际的欲望啊。最后,阿嚏居然还能娶妻生子并且继续逍遥自在。快乐、机智、反叛着沉闷秩序,还能维持大体上公平公正的阿嚏,不正象征着我们对快乐生存的渴望吗?
2、空间书写的文化意义
陆扬在《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中说,20世纪后半叶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两种向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 [1]。
师陀的《果园城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小城镇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经济模式被迫转型的迷茫与挣扎,但出于对自身极端低下的政治地位的习以为常,当面对强加于身的悲惨命运时,未曾想过任何改变,而只是以惊人的强韧力,抑或可称为惰性来承受。当这种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已坠入无法前进的禁锢中。师陀把他这方面的敏锐感受凝聚在果园城的场景中展现。在小说中,他淡化了作品的时代性和时间性,突出了稳定文化笼罩下的一幅幅静态的生活图景。
在这个文化圈子里,不再是人去影响空间。事实上,果园城的三类人都不想,也更加不能改变果园城的历史与生活,果园城的恶势力,不管他们曾怎样的喧嚣或煊赫,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就是败家子们都在不可避免地没落下去。而果园城的多余人,生命本就是一个空壳,枯萎和死亡是他们的宿命。显而易见,在强大的小城镇文化空间里,人是渺小无力的。人必须生活在城的文化规范和影响里。不是人改造城,而是空间的文化性格影响以致决定人的精神和生活。
师陀的空间书写的第二个文化意义在于体现人类永恒的恋乡情结。恋乡,寻根,追寻本源和原初意象,不管在古典文学还是在现代文学里都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有人说过,乡土情感址一种比普通情感更加恒久、普遍、具有原始性和根源性特质的情感。其实,更进一步地说,乡情感址所有情感里最顽固、执著的情感。师陀有关乡土空间的书写给我们提供了最充足的范例。在师陀的旅行故事中,典型的结构就是设定一个家园,不论是失落的家园还是回归的家园。他的其他文本的空间故事,也都在呼应这个行旅的主题,主人公先是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最后又回到家乡。
总而言之,“空间书写”师陀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必将因自己所创作的丰富的景观和同样丰富的意蕴而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文艺理论》,2004年第12期,第24页。)
——师陀小说《争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