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之死”与“巨星陨了”
——路易士两首诗作的辨析及史料新发现
/[江苏]吴心海
“巨人之死”与“巨星陨了”
——路易士两首诗作的辨析及史料新发现
/[江苏]吴心海
“巨人之死”:纪念被暗杀的托洛斯基
关于诗人路易士(纪弦)抗战期间的历史问题,古远清先生从2002年起迄今,反复说过不少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26页)一书。且引其中一段:
目前,人们获得路易士参与汉奸文化活动的最重要依据是:沈子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披露的纪弦写过适应日伪“大东亚文学”要求的汉奸作品。中国大陆出版的如陈青生所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乃翔和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这样叙述的:路易士《巨人之死》诗,系为悼念一名被抗日敌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作。特别是1944年秋冬,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轰炸上海日军,路易士写了“政治抒情朗诵诗”《炸吧,炸吧》,谴责美军的正义行为,嘲讽中国政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虚妄,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按:这些作品发表的出处,还须进一步查实)。纪弦对这些事实一律不认账,他在前后写的两种回忆录中辩解道:“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是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1942年,我从香港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几年之内,我从未写过一首‘赞美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诗,我也从未写过对于我们先总统蒋公有所大不敬的一字一句。”他认为1944年自己倒是写过一首抗议“陈纳德飞虎队误炸上海市中心区,毁屋伤人”的诗,但说原诗遗失,另又说不出发表刊物的名称和时间,因而这种辩解是无力的。

耐人寻味的是,古远清先生一方面说纪弦的辩解是无力的,另一方面又表示“这些作品发表的出处,还须进一步查实”,竟以道听途说、自己还没有查实的东西作为证据给一个人贴上“政治标签”,似乎不是史家(诗史、文学史皆然)应有的严肃态度,其实倒和“莫须有”没有什么两样。更何况是古先生质疑纪弦历史问题的文字,从第一次出现在2001年第12期《武汉文史资料》(题为“台湾诗人纪弦的诗路历程”)后,同样的内容和观点九年来陆续又在《书屋》(2002年第7期,题为“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兼评《纪弦回忆录》”)、《文艺理论批评》(2002年第4期,题为“纪弦抗战前后的‘历史问题’”)等杂志及《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台湾当代新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中,不断重复出现,延续至今呢?此种“锲而不舍”精神固然令人敬佩, 遗憾的是只止于人云亦云。为什么不能花点工夫,把自己八九年前就说过的那些“还需要进一步查实”出处的纪弦作品,查个一清二楚呢?
在这点上,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刘正忠先生的《艺术自由与民族大义:“纪弦为文化汉奸说”新探》(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11期,2009年6月,下称《新探》)一文,并未人云亦云,而是“对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搜寻、扒梳及引用皆有新的发现”(该文审查人语),以“白纸黑字”的事实,把路易士两首被笼统指为“汉奸作品”的诗作《巨人之死》和《炸吧!炸吧!》加以厘清,还历史本来面目。
下面重点说说《巨人之死》。
刘正忠先生不但从路易士诗集《三十前集》中找到了《巨人之死》(1942年),还把它与同一诗集中的另一首《失眠的世纪》(1941年)加以比较,认为此诗中受害的“巨人”并非人云亦云的被“抗日特工”处死的“汉奸”,而是遭遇苏联特工暗杀的“托洛斯基”(现通译为“托洛茨基”——编者注)。
1940年托洛斯基的遇害,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震撼。仅以笔者所见杂志为例,从1940年到 1942 年就先后有《中央导报》、《艺风》、《杂志》(半月刊)、《天下事》、《青年知识画报》、《国际间》、《国际两周报》等发表有《托洛斯基之生平》、《托洛斯基之死》、《托洛斯基之死与第四国际》、《托洛斯基论史太林(特稿)》(史太林即斯大林——编者注)、《托洛斯基与史太林》、《斯氏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托洛斯基与斯大林的斗争》等多篇揭露秘辛的文章。其中《托洛斯基与史太林》称:“史太林与托洛斯基之争是一场巨人的大战。”而《托洛斯基之死与第四国际》一文中则有“他的一党和儿子遭杀害不算外,他自己还不得不在外而过着迫害流亡的生活”的内容。
且不论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观点有什么分歧,但托氏及其支持者遭遇残酷清洗,流亡海外之后种种打击迫害仍然接踵而至,直至自由和生命最终被一起剥夺,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自称从“一个左倾幼稚病患者”成为“‘第三种人集团’之一英勇的斗士”的路易士来说,闻此种种,拍案而起的可能性是相当之大的。请看他在《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下称《回忆录第一部》)中的宣言:“为了保卫‘文艺自由’,我的笔也武装起来……鲁迅、胡风、周扬等迫害‘文艺自由’,杜衡、路易士等则坚决地反抗之、批判之。”
1940年第7期《艺风》(该刊1940年5月创刊于上海,香港设立总经售处,其时路易士正蛰居香港——笔者注)上刊载的《托洛斯基之死》一文,最后有“列宁撒手西归之时,托洛斯基曾匆促口传十三字云:‘列宁死矣。消息之来如巨石坠海。’托洛斯基临终之时,无人为志一首,未免可惜”的字样。或许就是这样一段话,引发了路易士1941年的《失眠的世纪》也未可知呢!

通过路易士《巨人之死》中的诗句“你是至善的光”、“你是全人类的太阳”、“继你的英勇的儿子后”、“你竟死于那凿冰斧的一击下”及“二十世纪的沙皇恐怖地狞笑着”和《失眠的世纪》中的诗句“我听见一个自称来自加拿大的游客”、“用凿冰斧/凿一个人的脑袋”、“然后是克列姆林的/二十九个字的/尖锐的狞笑”,的确不难找出如下线索:巨人是思想的巨人,否则谈何“至善的光”、“全人类的太阳”,从这一点上,当时中国沦陷区“沐猴而冠”的“大人物”里似乎找不到可与其比拟之人!死于“英勇的儿子”之后,死因是遭遇冰斧的袭击,行凶者“自称来自加拿大”,又正符合托洛斯基遇害的史实:他留在苏联的长子谢尔盖1937年被枪决,出走巴黎的次子列夫1938年在接受阑尾手术时神秘死亡,他本人于1940年8月20日遭遇一名持加拿大护照的西班牙男子以冰斧袭击致死!至于“二十世纪的沙皇”和“克列姆林”所指引的方向,则更为明确,与苏联丝丝相扣,而和当时沦陷的中国则风马牛不相及。
因而,以“路易士《巨人之死》诗”,古先生以及一些论者便认定“系为悼念一名被抗日敌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作”,显然属无稽之谈。
至于路诗中为什么没有直接点出托洛斯基的名字,应该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中国的“托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冠以叛徒、汉奸、国民党内奸等罪名,此为后话,实际上当时的“托派”,正遭遇了共产党的“肃托”、国民党和汪伪政府的“反共”的三重围剿。因此,路即便是以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对以暗杀手段迫害自由的行径的愤懑,也不会贸然指名道姓,而去趟政治的浑水,引火上身的。其实,在《失眠的世纪》中也写得很明白,“巨人”被暗杀后,除了“克列姆林”狞笑,还有“色盲们,/投机分子们,/没有文化的猪猡们的/一致的喝彩”,这一指向,也是不言而喻的。
“巨星陨了”:即席悼念汪精卫
对于抗战期间的历史问题,纪弦在《回忆录第一部》(第152—153页)中曾如此表示:
是的,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我也不是什么“文化汉奸”,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我没有“认贼作父”,我没有“卖国求荣”,我手上没有血,我心里也没有阴影。我是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是诗人,而且又是名家,当然不能不发表作品。我的诗和散文以及诗论、艺术论散见各报刊的,大受读者欢迎。但我从未写过“赞美敌机轰炸重庆”的诗。我也从未写过对于蒋公有所大不敬的一字一句。那些文丑文渣,如果他们所造假的“诗句”,真的曾在沦陷区的报刊上发表过,那就请他们拿出白纸上印的黑字作证据吧!可是他们有吗?屁都没有。既然无凭无据,怎可随意给我戴上一顶大帽子呢?
文中所提“赞美敌机轰炸重庆”的诗,其实就是上文所涉及到的《炸吧!炸吧!》一诗,和“敌机轰炸重庆”确无关系。刘正忠先生找到了原始出处(《文友》第4卷第4期,1945年1月1日),并在《新探》一文中进行了精当的分析,还原了历史真相,本文不赘。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期上,看到一则论者从来没有提及过的史料《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文,涉及路易士的诗歌创作。该文在叙述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代表11月12日下午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用中文和日文为刚刚死去(11月10日)的伪政府头领汪精卫致吊词后,接着写道:
继之,上海诗人路易士亦自告奋勇,谓即席成诗一首,题为《巨星陨了》,请求登台朗诵。经议长转达后,闻者鼓掌。于是路诗人昂然登台,高声朗诵,其词如后:
扬子江在呜咽。
紫金山在叹息。
十一月的噩耗传来,
亚细亚的巨星陨了。
……
听那太平洋的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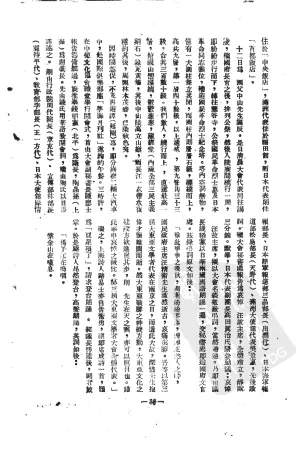
鼎沸,狂啸;
……
滴滴是
先生的辛酸泪。
……
啊啊,谁来收拾
这山河的破碎!
(《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月号,第36—37页)
从文中的省略号看,诗应该没有全引,也不知道此诗后来是否正式发表过。不过,据周越然追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字《自大会归来》(《文友》第4卷第3期,1944年12月15日,第20页)记载,汪精卫死亡的消息“正式在会场上公告,是十三日的下午。我们听到之后,即全体起立,并且静默三分钟。半小时后,人人都臂缠黑纱,带了孝了”。因此,路易士登台朗诵《巨星陨了》一诗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论及《巨星陨了》之残篇,有必要一提路易士1938年9月6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的《诗人们,到前线去!》。在这篇几乎无人注意过的散文中,他充满诗人的激情和爱国之心呐喊道:
诗人们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搁下他们的笔,荷起枪来,走上前线去。
他们应该觉得能以参加这个为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的神圣、庄严的战争何等的光荣!
一种新的,有力的,有生气的,充满了正义感的诗篇,将要蓬勃地,茁壮地生长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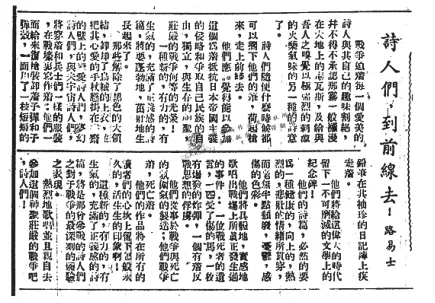
……
这种新的,有力的,有生气的,充满了正义感的诗篇,将是那曾参战的诗人们之对于战争的最深刻的体验之表现。
只是不知道,此后六年,路易士在即席朗诵《巨星陨了》时,有无想到它和自己所说过的“一种新的,有力的,有生气的,充满了正义感的诗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呢?
高龄九十八岁的路易士是先父、诗人吴奔星上个世纪30年代的老朋友,自前几年在美国家中中风后,一直不良于行,由女儿照顾。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似应“为尊者讳”,但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笔者还是把掌握的材料写成此文,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不以一眚掩大德”,不论路易士抗战期间如何,他20世纪后半叶对台湾诗坛乃至中国诗坛的巨大贡献,足以彪炳史册。
作 者:吴心海,学者,现居南京。
编 辑:孙明亮 mzsulu@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