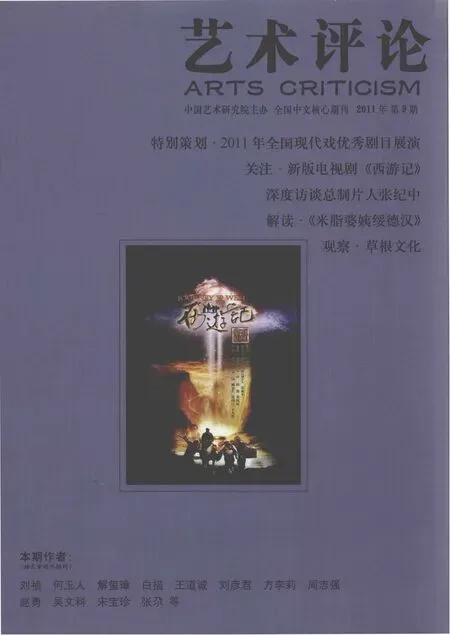物象·他者·原乡:台湾电影的“后海角”怀旧
马聪敏
马聪敏: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翻看“后海角”以后的台湾电影,“台湾之夜”上同台亮相代表新浪潮、新新浪潮、超时代浪潮的侯孝贤、蔡明亮,李安,陈国富、钮承泽,共同堆积汹涌出了台湾电影“后海角时代”的热闹、缤纷和丰满。但定睛一看,文艺化的青春、耽美化的爱情、浪漫化的成长、流行化的怀旧,是琐碎而乏力,丰富又沉寂。不管是单纯的台湾历史记忆里的怀旧,还是当下生活中若隐若现的怀旧,怀旧,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唤起和伤怀。怀旧,深深地牵涉到对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去哪里的认识,是一种我们在永无止境地建构、维护、重构身份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电影的怀旧有了比安慰和疗救更深刻的意义。
怀旧的物象——表达“在地”特殊性的文化恋物
“在地”的概念虽然有点拗口,但比“本土”一词更有说服力。一方面它是有着殖民历史的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面前的自我文化更新与重建,另一方面是指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与本土融合(glocalization)的现象和越来越系统的交互联系。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
台湾有什么好 玉兰花的清香 蓬莱米的饭香 牛奶芭乐的果香
……
你问我台湾有什么好,我犹豫了
台湾有什么好 百合花的芳香 地瓜叶的菜香 春天冻顶的茶香
……
——苏来《我要如何对你说》
台湾的伟大过去的形成确实经过了太多风雨,而对于台湾的体认,也经历了太多困惑和犹豫。“我们是谁?”“台湾是什么?”是萦绕在台湾人心中的永恒追问。当人想要依靠记忆的魔手,拼命拉回一段段早已失去的岁月和日渐遥远的故乡,通过回望过去解决自我身份认同的疑惑时,大抵总是觉得无力,免不了要通过玉兰花、蓬莱米、牛奶芭乐、百合花、地瓜叶、春天冻顶等这些具体的物象来完成。在电影中,如同《阿甘正传》里的白羽毛,《锡皮鼓》中的纸牌游戏。物象,哪怕是一朵花、一张钞票、或者一块马蹄铁,都承载了台湾的特质,台湾的生命和记忆。
本省人导演魏德圣的《海角七号》(2008)用日籍教师写给台湾女孩的七封情书,江文也的音乐,还有舒伯特的《野玫瑰》、小米酒以及原住民项链等具体的物象,将汉人、原住民、包括以日本为代表的殖民海盗一起整合为台湾的伟大过去。《渺渺》(2008,程孝泽导演)中日本交换生渺渺要寻找的是奶奶初恋时常去的一家名叫永记的糕饼店,不过岁月轮转,这家糕饼店被置换成了一家二手CD店,店主人是一个不能从过去的故事中走出来的忧郁的男子,一遍又一遍地放着《长春花》,这也是渺渺小时候奶奶教过的日本歌谣。永记糕饼店和《长春花》这样的怀旧物象及其中所包含的关于记忆与遗忘的纠结,说尽了台湾的本土抗争与外族统治之间的甜蜜与哀愁。
在《泪王子》(2009,杨凡导演)所试图回到的国民党据守的50年代,一本破旧的童话故事《泪王子》成为唯一贯穿整个叙事的怀旧物象。《泪王子》不仅纠结了宛平与千君在老上海时的革命的青春和莫名其妙的同性感情,更催生了刘霞军和小立为代表的眷村外省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新传统。不过,在矫情做作的节奏和叙事中,《泪王子》成了装腔作势的摆设,没有为影片的失魂落魄带来任何一些扭转。同样,《新鲁冰花·孩子的天空》(2008,陈坤厚导演)的70年代的遥远茶乡和传统乡土台湾已经无法再现,其物象化的表现就是老师郭云天的那副画作,而古阿明对其进行创造性地涂鸦,甚至用彩绘的方式将其漫画化,这似乎预示着台湾社会人文图景的传神描述在流行元素的包装之外已找不到其他方法。
怀旧的当代用意是将过去理想化和浪漫化,于是,怀旧的物象在朴素的形制外就有了美、愉悦、快乐、满足、善良、爱等等意义。怀旧物象通过影片的包装,不仅用来表达“在地”的特殊性,同时将“在地”特殊性作为时尚的文化恋物和流行商品加以包装,台湾的过去成为卖点,也是在地特殊性作为文化意义再生产的题中之义。
怀旧的他者——建设“在地”身份的彼岸想象
“在地”自我身份的确立一方面要从内部以怀旧物象的文化意义来加以填充和建设,一方面还要在与他者的遭遇中,得以想象并加以完成。有趣的是,怀旧电影中“在地”的他者想象,不管是殖民主的日本文化,“亲美反共”意识形态下的美国文化、大陆文化,还是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他者:欧洲、美国、日本、大陆等等,对于在阶序逻辑上高于自己的他者[1],台湾电影呈现出将他者魂灵化的统一特点。他者被想象为历史的幽灵,表现出难忘但却飘渺的无生命的存在形式。
《海角七号》里死去的只留下书简的日本情人,其表现形式仅仅是几个简单的蜷缩的背影,我们几乎很难看到他的脸颊。后来被证明是收信人友子的外孙女的酒店清洁工,则一直用抽烟、心绪不宁、莫名的烦躁和愁绪表达对日本人的又恨又爱,离开又难以忘怀的态度。伤了她的心的日本人,从未出现,就像殖民历史中的日本文化一样抽象无形。《渺渺》中,在台湾留下初恋回忆的渺渺奶奶作为殖民历史中殖民文化的象征,始终是以电话里的声音的形象出现,同样呈现出无形化的特点。
具有有形生命的他者的被杀,同样能表现出将他者魂灵化的特点。《蝴蝶》(2008,张作骥导演)里,主人公一哲的父亲是个移民台湾南方澳渔港的日本人。20年前,正是父亲造成了母亲的自杀,抛弃了一哲兄弟并去日本“混黑道”。积郁着20年愤怒的一哲终于开枪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弑父后的一哲,用自身的毁灭呼唤着历史的灵魂。《墙之魇》(2008,林志儒导演)中来到台湾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日本“先生”,一度被阿义夫妇当做权威和导师,但最终被阿义所杀,表示了对精神之父的抛弃。
《泪王子》中孤独的风琴手汉生被以通匪的罪名枪决,影片的最后,安排他在想象中死而复生,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满心欢喜准备过新生活的宛平身边。电影中对魂灵的这段表现,虽然在实际效果上混淆视听,是让本来就不清楚的叙事更加扑朔迷离的败笔,但在另一方面却佐证了影片试图将大陆文化这一他者无形化的效果。
《新鲁冰花》中的偏远茶香小镇,从城市里来的美术老师郭云天带来了全新的美术与教育观点,具有绘画天分的古阿明的才华却不为沉溺传统的师长乡绅所认同,郭云天离开小镇,古阿明高烧不退,信神信风水的阿求神问卜,贻误了治疗的时机,古阿明患病离世。70年代的台湾,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在地文化正在向城市文化转变,与更具现代性的外来者认同的古阿明的被扼杀也许就是文化换代和转变的代价。
电影《阳阳》(2009,郑有杰导演)里的中法混血儿阳阳的从未见过面的法籍生父,可能最能代表全球化时代“在地”的他者形象了。阳阳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她不会讲一句法文,却长着法国人的脸庞。全球化时代,法国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处在台湾对他者想象的最上层。这样的情节安排,延续了台湾人认为日据时期日本文化处在台湾他者想象的最上层,国民党据守时期美国文化处在台湾他者想象的最上层的对他者位置的想象。
与余光中等一辈作家及侯孝贤、杨德昌等将台湾作为“亚细亚孤儿”来描述其遭遇变革时代的无奈不同,“后海角”的“超时代”们正在用更为开放和超越的态度靠拢他者,用更为开放的态度面对“多元他者”。在真正置身于多元文化的他者中时,在地文化身份必然要遭遇不断的重新选择和定位。承认他者的启蒙意义,但告别,或者随时准备告别,却是更为开放的在地文化的新姿态。他者作为魂灵,或者被杀死的魂灵,其表现出的沉默和隐晦,无名化甚至无形化,被悬置,去现实化等等特点,是现时台湾在地文化“反客为主”的有效做法。于是,在台湾电影中,我们习见了这样的场景:码头上,夕阳余晖里,少男少女奋力地挥舞着双臂,大声地喊着“再见”,感谢外来者带来的启蒙和梦想,从此后便将对方放上记忆的祭坛。
怀旧的原乡——回归“在地”的空间意象
从“怀旧”的希腊文的词源nostos(回家)和algia(一种痛苦的状况)来看,怀旧是一种对重返家园的痛苦渴念,最终指向是“家”、“家园”这样的空间场所。经由怀旧所建构的这一空间场所,是精神的冀望所在,是扎根于人的内心深处,让人生有所依附和归宿的空间所在。“在地”观念的认同一旦借助于怀旧的历史元素作为媒介,其所呼唤的那个召唤心灵中共同的经验,共同的记忆的空间场所,就是原乡。原乡,是一种完整的在地想象空间。同时,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当现实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的时候,怀旧就呈现了现实的所有意义。[2]“怀旧的时刻是一种准备脱离过去、脱离一切结局和回响的文化标志,为将来的尽善尽美做准备。”[3]可见,“怀旧”一词一方面指向过去的永远失落或远离的家园,一方面又指向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中自我认识的努力和对未来的重写。可以预料,台湾电影中的怀旧虽然在指向上会到达“原乡”,但却是一个重写后的“原乡”,一个指向未来的“原乡”。
《海角七号》里的民意代表也许并不知道,塑造恒春的在地乐队,已经实现了“在地”一词的实践性:在兼顾族群地区性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包容性极强、丰富多元的在地生活文化,才是面对并修复殖民历史记忆,同时与强大的全球文化并存的有效策略。于是,《海角七号》成功地将1945年遣返日俘的引场码头和恒春旧地“海角七号”置换为垦丁海滩BOT,将带着历史创伤的集体失意转换为个体的小小失意,将疗伤的七封怀旧情书置换为信义乡的小米酒、垦丁观光饭店和原住民工艺项链。这次成功的尝试,让台湾电影开始着力塑造一种走出困境正在享受幸福的完美宝岛形象。海角以后,幸福温暖的台湾在地形象蔚然成风,甚至在政令上也有意延续其意义。在政策方面,政府调整过去主要基于血缘、族群、历史、地域的身份认同,开始从文化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切入,重建一个属于文化和审美的共同体社会。在以怀旧为主题讲述台湾过去故事的电影中,“原乡”便是未来重建文化和审美的共同体社会的切入角度。电影不约而同地对“原乡”形象进行了模拟化的表现,其模拟的效果,便是一个天堂般的伪装的原乡。
以模拟的方式对原乡的再现,在怀旧作品中浪漫化地处理“原乡”形象,用天堂的原乡来建构历史中“审美与文化的共同体”,鼓励自己更爱它,是解决在地文化自处问题的积极手段。如果说,在《海角七号》《泪王子》等影片为代表的试图将台湾的历史记忆与台湾恒春、原住民聚集区、高雄的地方特点结合起来的作品里,原乡被模拟化为天堂;那么在《霓虹心》(2009,刘汉威导演)、《星月无尽》(2009,唐振瑜导演)、《夏日协奏曲》(2008,黄潮亮导演)、《一页台北》(2010,陈俊霖导演)等直接呈现当下“在地”的风土人情与“在地”人的生存观念的作品中,带有历史感的原乡却不再是天堂,而是文物化的沉默的荒凉景致了。《霓虹心》透过一对瑞典母子的眼光看当下的台北。但故事的一个重要空间便是台北县三芝乡海边矗立了数十年的飞碟屋,导演用飞碟屋对应自己十七岁以前在屏东乡下时运甘蔗的小火车站,用荒凉的废墟般的景致为逝去的岁月致意。《星月无尽》和《夏日协奏曲》中的金门则是文物化的原乡,宗地、祠庙、衙署、陵墓、炮台、登陆桩、备战时遗留的炮弹等,它们冷冰冰地沉默着,静观“在地”的变化。
总之,台湾电影中对“怀旧”的再利用,是建构“在地”身份的重要途径。不管是其内部用怀旧的物象填充在地的文化再生产意义,还是在与他者的遭遇中,将他者魂灵化,来行使在地文化的自主权,抑或是模拟化地处理“原乡”这一在地空间形象,都是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并体现其价值的有效尝试。当然,当怀旧一途进入自我迷失的复制,随着新鲜感的消失,新的沉闷和自溺将随之而来,其实,在侯孝贤赞颂《艋》开创了台湾电影未来十年的荣景的同时,新的沉闷和自溺已经出现,不过那已经是需要另文论述的内容了。
注释:
[1]陈光兴:《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688319/。
[2]蒂莫里·W·卢克:《美学生产与文化政治学:波德里亚与当代艺术》,见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页。
[3]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