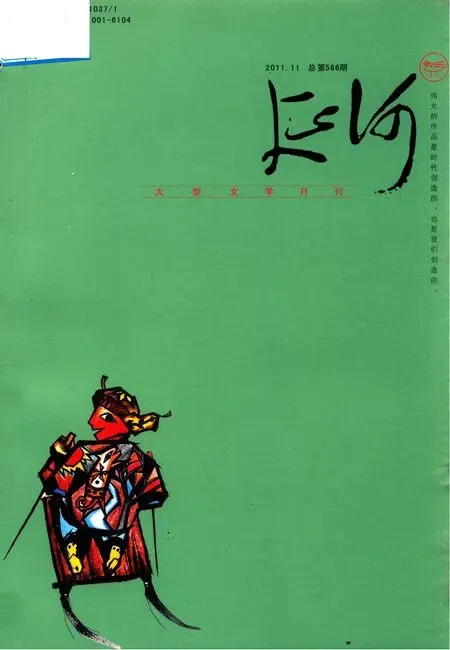寄洛杉矶
西风野渡
10 号台风
10号台风
先是雨
深深浅浅的水洼
坐飞机而来的女鬼,高一脚低一脚
在灯火中绕道而行
10号台风
从遥远的太平洋,从
大海的深处带来秋天
秋天,我渴望已久
全神贯注的秋天
你选择台风夜归来
更加凄冷更加孤绝,更加充满
妖艳般的恐惧
现在台风已过
台风将一万名清洁工扔向早晨的街道
我不关注街道,我只关注鹰
一只鹰在早晨的滚滚天空中盘旋
昨天晚上它还象一个贪杯的酒鬼
把远方岩石上的血
舔得一滴不剩
我们一万次地
我们总是一万次地
从午夜归来
穿越城市的街心花园,一万次地
迷途知返
我们总是一万次地
在外省陌生的客栈醒来
天使的哭泣早已在长途电话里哑掉
在一万次的灾难中我紧紧地
将你护在胸口
而黎明总在消防车的背面
张大它恐惧般的黑眼睛
我们总是一万次地
在雨雾中走出去
走向郊外那古老的教堂
清晨湿漉漉的大理石小路
我们总是一万次地滑倒
然后忏悔,不安地追忆
在大海深沉的喘息中我们一万次地
舔舐她那永恒的伤口和比伤口更疼痛的
忧郁的花朵
忘川之上我们总是一万次地
仰望星空,静卧在碧波中
寄洛杉矶
1
雨后的洛杉矶,霓虹漂染着夜
色彩恣意地流淌
像南加州那些漂亮的鸡尾酒
斟满月光的杯盏
不要怀疑眼睛所看到的
真实的梦境,和
闪闪的忧伤
当最后一名旅客,拎着伞
消失在湿漉漉的森斯特大街尽头
我们依旧坚持
不把自己迷失
并把最后一杯月光带回家
2
这样的场景我至少在三首诗中描述过
诗人西风野渡,你还记得吗
生命中的每一场淋漓之雨他都凑巧赶来
他孤立且坚仞的下巴闪烁
如同美利坚上空那颗暗红色的星
而另一场被气象台漏报的大雨
使羁旅异国深夜的窗口
深深哽咽。这是全世界华人孩子
都闭上眼睛数星星的一夜,这是
万里之外的祖国渐次展开最荒凉的田野
3
如果是早晨,成群的鸽子在威斯理广场上飞舞
天空在太平洋上的鱼眼睛里
缓缓张开。天使总比魔鬼
早一步抵达丰盛的早餐桌
让光明收拾残局吧让隔夜的乡愁
冲刷绵长的海岸线
在洛杉矶,没有一个男人不会饮酒
没有一个女人不懂亲嘴
逢场作戏,让欢愉装满或者被痛苦
迎头痛击,丧失母语和记忆
哦,都快八年了
蓝眼睛的洛杉矶,你还记得什么
4
当好莱坞泛着甜腻的气泡醒来
教堂的尖顶缓缓升上地平线
洛杉矶从不缺少疲倦的女士
卷毛的狗,晨祷以及隔岸祝福的人群
岸的这边已是深夜
天空迸发出宁静和死亡的气息
大地倾听着磨房与水的歌谣
月光,一堆又一堆的水银
擦拭着故乡信阳的屋顶
并差点把长满毛尖茶树的村镇
妆扮成一个异国女子
5
有一个秘密我一直不敢问你
季节被玫瑰深藏
有一个地方我一直不敢梦见
流水镇的铁匠将一把大锁反复锻打
一段旧情,宛如一张新出土的老唱片
从深圳到洛杉矶
走一千零一次夜路,能赶到你身边吗
写一千零一首夜歌,能让你听见吗
诗人只能黯然伫立在这个陌生国度的地图前
要么选择分手
要么继续单恋
故乡的油灯
1
一灯如豆
昏暗
孱弱
代代不灭
窑洞的泥巴墙上
夜夜上演
生活的皮影戏
我挨个抚摩
奶奶的
母亲的
父亲的
瘦俏影子
可折腾半天
就是抓不住
我自各的
2
奶奶搓麻绳
母亲纳鞋底
父亲教我字
妹妹说梦话
70年代的乡村夜晚
没有你想象得
那么清贫
重点说说父亲
一个威震三十里的
乡村教书匠
用沾满红墨水的食指
随便戳在书本某页
这些七十年代的夜晚
都会令我深深敬畏
3
我有过短暂的牧童生涯
翻山越岭,寻找草场
我目击过那些废弃的村落
整村整村,迁徙或死绝
那些卸掉窗户的窑洞
如敲掉牙齿的嘴巴
朝远方的岁月
乌黑地敞开
每个收工的傍晚我都要登上
白季峁对面高高的山梁
俯瞰那些半月形的窑洞窗户
在孩子们的的哭声中一扇扇点亮
噢,白季峁村依然活着
我这才放心地,赶羊归栏
紧紧攫着心灵,来自惊恐
让我三十年后依旧对命运葆有警觉
4
乡村夜晚的剧情
平铺直叙,缺乏悬念
仅有的高潮
都在煤油灯的影子里
孤单上演
婶娘上吊死了
大灰狼叼走了二毛子
羊倌二爷丢了一只山羊
找寻的队伍
将马灯高高举过头顶
记忆最深的是
一棵流星砸向村口的老槐
我看见了擦出的火花
扑过去
但并未找到传说中的陨石
5
初中时期
从家到学校步行六十华里
沿途散落着五六个村庄
积雪没膝的深夜
我,赖子,晓军
数次穿越陕北高原的沟沟坎坎
坟地里的野蒿草摇曳过后
不知名的野兽又将深不见底的沟壑
叫得一片狰狞
我们加快步伐
希望赶紧看到一窗灯光
让我们发麻的头皮松弛下来
三十年后我才想
如果随便叩开一扇
我的命运也许就将改变
6
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
白季峁村依旧噤若寒蝉
仿佛人人都是告密者
一不小心就被办进
公社学习班
直到1979年的春天
有一首歌和白季村无关
我亲自目睹了
生产队最后一次会议
唯一的主题就是
——分家
大伯分得一只犁铧
二叔分得两张草席
一村之长的四爷
最后一次仗势欺人
将一头落泪的老黄牛
公然牵走
轮到我家
只剩两盏灯
一盏是常见的铁柱式煤油灯
另一盏是可以拎着
半夜喂牲口的马灯
7
这盏人民公社的煤油灯
一直照到1984年
我从故乡
举家迁走
煤油灯夜夜点亮,照进
我的童年,多少年后
只要打开
依旧还是橘黄色的质地
我想燃烧着的,除了煤油
还有别的
但我不想比喻也不想
抒情
直到2002年我回老家
想找出那盏煤油灯
带回深圳
将它点亮在异乡,繁华落尽处
可隔壁的二伯
早将它卖了废品
至于价格,我想了想
终没好意思问
凌晨三点四十分的城市广场
我想除了我,不会再有人
这么晚打这里经过
道路空空荡荡,宛如四肢伸展
把中心广场,那美丽的胸腹部
裸露出来
我简直惊呆了
仿佛一生只此一次,仿佛
知道我要来或者是我
如期而至。是应该熄火
停留一会儿,感受
自身的渺小与世界的无声
电台女播音员,语塞时多么温柔
她一说月亮,我就抬头看见
那孤独的环形山
一点点风,舔舐着落叶
一点点秋凉,溜进车窗
我真想说让爱情回来
可白露已结满长天
不用多久气象台将挂出
黄色的降温警报
我知道是该撤离的时候了
我知道我撤离后这里将有
最黑暗的半小时
再次变成一个死寂的场子
但捱过这短暂的空旷
清洁工和洒水车
都将来到这里
人们再度涌向晨光中的街道
仿佛昨夜的一切
都不曾发生
蒙太奇
起先是男人
呼哧呼哧
女人如死鱼
后来是女人
呼哧呼哧
男人比女人
更加死鱼
后来,两条死鱼
河床上晾着
一片乌云过来
刚好盖住他们
后来乌云飘走
客厅的门敞着
半掩卧室里一张揉皱的床单
比河床还要空旷
画框里响起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