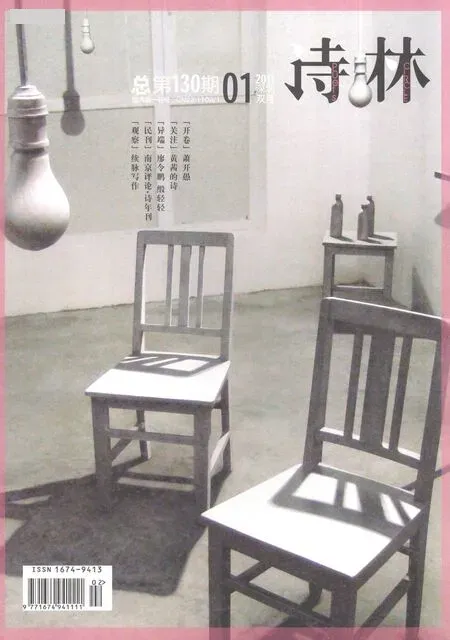胡桑:打开和再度打开的世界
胡桑:打开和再度打开的世界
徐 钺
一
八月,我在傍晚有些踟蹰的黑色到来前读诗,某个人的诗。几分钟后,我伸开弯折的手臂,把诗稿举得远了一点,并且高一点,略带倾斜的角度——这有些奇怪。在阅读大多数诗和它们的作者时(虽然更多的人总是先读到前者,或者只读到前者),我习惯于将他们放在灯里,靠得近一些,在灯罩下那放大镜般的光晕中寻找某些东西。
我忍不住掠过那诗稿之下的名字:胡桑。
熟悉的名字,有些危险。毕竟,熟悉会造成另一种阅读的偏移——以对“整体作者”(thewholeauther)的印象来先验地判断他的某个作品。我迅速把目光移回文本,刚刚翻开的一页,一首题为《惶然书》的诗:
我迫不及待地完成。从地平线返回,
背负着夜的寂静,那令人渴望的形式,学习如何再一次进入生活。白昼永不消失,
就这样存在着,像自己一样盲目。……
对一首好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判断或许有多种方式,但有一点几乎是必须的:它要让人看到它的作者。因此,尽管我试图像新批评那些固执的理论家一样,拒绝让自己想起胡桑的性格、诗学诉求、语言习惯,以及他长期西方哲学研究的背景,效果却总是微乎其微——这首诗只可能是他写的。
然而,出于篇幅的考虑,也出于此刻对一个诗人作出概括判断的必要,我还并不打算轻率地去谈论《惶然书》(或《褶皱书》)这样的作品:它们需要更长的专论。
约一年前,王东东曾写过一篇具有某种导引性质的文章——《下沉与飞翔: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写作》。其中在谈到胡桑时,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我们这一代诗人会不断迫近新诗的基本问题,即世界观的问题;在我们这一代诗人身上,写诗和搞哲学研究完全是可以并行的……”对于作者自称的这一段“题外话”,我赞同其绝大部分。只不过,出于论述的需要,这段话的主体实际仍是一个大的“我们”,而非胡桑,一个具体的诗人。世界观的问题或新诗的基本问题的确被新世纪的诗人们不断迫近,但每个诗人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这种“迫近”源于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与对个人经验陈滓的筛选摒弃,源于我们共同分享的历时资源和历史背景。但在评论胡桑的时候,这种概括性的表述就会略有危险。
说到底,我们对于某人或某物的兴趣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距离更远,而与他者(熟悉或不很熟悉的更多他者)对某人或某物的兴趣距离更近——这是心理学对于当代信息接收意识的一种描述,它对大多数的公众有效,同样,也对大多数的诗人和评论者有效。然而胡桑似乎并非这“大多数”中的一个,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他的阅读兴趣与对现实的观察兴趣更多地来源于对自身不断生发的可能性的选择,一种貌似随意却又颇为“理性”(并非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和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选择。在写作中,胡桑则似乎是在发明某种从理性和自身已拥有的诗歌技艺中冲脱的方法;他对自己的知识和技巧所带有的警觉毫不亚于他对生活本身的警觉,并且,不断检视正被他握住或握住他的语言。这就像一只飞鸟偶然意识到自己正悬于空中时的警觉,它会通过自身而非他者的飞翔姿态来重新判断方向,小心,却拒绝变成更“安全”的爬行动物——对于“世界观”或“语言自身的基础”,胡桑的迫近形式与大多数诗人不那么相类:他处在现实与语言那巨大空间的某一点上,完成自身,又将完成之处打开,带着冷静与怀疑,不断进入另一个不为人知(或也同样不为己知)的世界。
伴随于此的,是这样一个表象:我们发现,他——胡桑——并不很热衷于发表自己的作品。如果不能简单地说,他对发表无甚兴趣。
总有一些对当代诗歌的属性了解略少的批评者(偶尔以“普通读者”的姿态出场),他们会用某种老生常谈的、教诲式的调子质询诗人:你们的作品是给公众读的,给一小部分人读的,抑或仅只是给自己读的?——当然,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质询面向了当代诗歌确然存在的问题,面向了那些我们迫不及待想扔掉的杂质(不管这些杂质被冠以了怎样的名目与怎样的个体光环)。而另一种(也是更常见的)情况则是:他们或许并不清楚当代诗歌近二十年最大的成就便是删减了那些在八十年代以非诗面目出现的群体性话语,他们只是期望(我相信这种期望的真诚)一些可被理解的“优秀”诗作出现在自己的阅读视阈中。
但对胡桑而言(就像对大多数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而言),作为“公众”的读者想象并不在他的写作图景之中现身——这与是否选择
大声言说自己,是否如某些杂技演员那样积极地兜售自己毫无关系。个体之外,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外部世界,是所有事物的镜像或个别事物的在场:“但是,窗口的阳光并不平静,挣扎着/像一种古老的疯狂,舔着桌子上一只梦幻的水果”(《褶皱书》);而面对自身与自身的写作时,他则会将存在于体内的世界如坚果般剥开:“我返身,一种坚固的修辞/迎面而来。它扶着一个敏感的/灵魂。”(《久雨夜读》)
这种似乎不露声色、却锋利异常的显影与他的书写姿态直接相关。
极端一点说,胡桑的所有写作都是有节制地从“世界”返回“事物”(我会再次提及这两个在他文本中异常重要的概念)、从外在返回自身,并且,再以相反的方向重新出发。胡桑首先拥有的是对世界/事物的智性,而并非他精湛的语言技巧;而在智性之中,他又始终试图超越固有的、稳定的自我,从阿波罗向一个略显清醒的狄奥尼索斯趋近。他很显然地意识到,诗歌写作借由哲学思辨而获得的平衡与匠人般的手艺都不能让自己满足,不能让语言满足。对发表作品的不甚在意实际印证了他对诗歌、事物与自身内部已有存在的绝对在意:对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与多变的必然性的在意。与我们时代的许多诗人相比,他从不急于在自己名后写下过长的注释,那些用以装饰身份的金属片。这是一种于喧嚣中濒临灭绝的气质——在较熟悉并且出众的同代人中,我仅在胡桑和另一位青年诗人金勇那里见得明显。
事实上,对于上文所述的那个质询,我们只需略微改用一下奥登在《丰产者与饕餮者》中的话:如果对公众的吸引力和对读者的诱惑才是艺术唯一的标准,那么,电视广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承认,有些写“诗”的人对这假设关系理解得颇为精当,他们把自己和不属于自己的声音卖得很好。
二
我们谈到一些诗人。
这是我们的疾病和善良。
有些诗人毁于政治,
有些像一枚硬币被经济磨旧,或者,从诗歌的小仓库走向
散文的山林。还有一部分
是隐秘的灌木,散居各地,
守护语言的气候,渴望
碰见黄昏与寂静,多么
不在乎现实,那任性的季节。
——载自胡桑《与藏马对饮衡山路至晨》
2010年5月的一个不很寂静的黄昏,我和胡桑、金勇、王东东在北京某家因蟑螂而著名的小酒馆中喝酒。几小时后,我们换到另一家小店,露天,风很温顺。当另外几个朋友加入的时候,已是深夜,我们揣着自印的诗集,沿街寻找通宵卖酒的地方。
这个5月,是我第一次见到胡桑。
那一夜总是被记忆精确地找到,似乎它隐藏着什么秘密:几个灵魂在黑暗中飘向有光亮和酒杯的所在,对某些东西心照不宣。那没有路灯的街道像是一段隐喻,在比黑夜更长久的时间中跟随我们,进入我们,低声说:你们谁会首先离开?
没有人。当“有些诗人毁于政治,/有些像一枚硬币被经济磨旧,/或者,从诗歌的小仓库走向//散文的山林”时,我们彼此确认,没有询问也没有丝毫怀疑。我们很清楚:在这条路上离开的人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多,他们消失于近旁,消失于可见的、每一秒都被我们掠过的近旁。然而无论胡桑、金勇、王东东或是我自己,皆没有谈及这些;如同分享着某个相同的回答,我们走向时间更重的地方。尽管身体很轻,像可能被随时取走的行李。尽管那个夜晚之前我对胡桑的了解还不算很多,甚至,还没有读过《与藏马对饮衡山路至晨》这首诗——那探入并洞悉世事的语言,“疾病和善良”。
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空旷的所在,有低语和流汗的酒。催熟星光的夜晚浓稠。空杯被诗斟满,被喝下,使我们更加浓稠。
归根结底,能在当代诗歌的荒扩空间中显现或曾经显现的,只有两种灵魂:如海螺壳般的,如秋日果实般的。后者以轻柔之词隐藏心脏,隐藏未知的内部;他们熟悉季候的规则,把成熟的梦幻详尽描绘,年复一年。前者则以相反的姿态,用坚硬的心脏握持着一个柔软而危险的肉体;在风暴到来的浓稠时刻,他们打开自己,用号角般的呼吸吹动海洋。
我并非要于此褒贬这两种诗歌中的主体存在形态,它们并不拥有天然的敌意;在一个诗人——甚至一首诗中,我们都可能读到两者的并存。但毫无疑问的是:胡桑更偏向于前者。如同许多我此刻无法一一列举的名字,他选择(也许“选择”这个主动性的词并不完全恰当)那穿行于顽固阻隔的言辞,那打开和关闭之间令人激动的危险。事实上,写作的长久性和可能性也更多地源自这种“不安”,这种同时自外部和深底涌来的震颤;而不是如大多数人所想,依赖于后者“安全”的年复一年(尽管它在我们“年龄的雾”中也很重要)。
胡桑的主体表象似乎过于坚实,以至于读到他《夜读黄仲则》这样的诗篇时,那种过于尊重的致敬和减轻自己声音的姿态甚至让我不易接受。“我希望像你一样取悦于汉语”和“一本短诗集放在台灯下,我不忍心望见窗外密集的小区”这样的诗句充满敬意,却也将客体变得过“重”;自我则在这重量下退回螺壳内部,构成了主客间不对等的紧张与平静——而不是像他那些更具力量的作品,闪电般生发并进入内部,再重返那掀动自我的所在。在对话中,时间之镜中可能的言辞实际上被衰减了,那穿透自身与外在空间的强力退回到螺壳内部,缩紧,变成仅属于自己的回声(与之相比,《孟溪三章——致何羲和》等就更加关注内在的生长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没有太过谦逊地跟随他者的声音)。因此,尽管《夜读黄仲则》这首诗在其语言和结构方式上都显得让人满意,我却始终不认为:它是胡桑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
在我看来,《惶然书》、《褶皱书》和《十一月五日午后,狂风大作》这样的诗作才真正代表了胡桑诗歌独异的品质——广阔而精确,平衡,带质疑的理性,节制中释放的力量。许多人会在较浅显的阅读后得出判断,认为胡桑的写作是内敛并自我抑制的;但恰恰相反,他并没有简单地从外部回到自己、回到发出声音的螺壳内部藏匿起来,而是将自身作为天平的支点,同时穿透“世界”和“事物”那随刻变动的、对偶的意义砝码。简单点说,他从未被已有的存在抑制,不管那存在来自诗或哲学。
此刻,也许回到这篇文章开端的那个场景是合适的,甚至是必须的;我们必须伸开弯折的手臂,把胡桑的诗稿举得远一点,将他言说自己的声音从世界的喧嚣阴影中辨别出来,从事物的沉默重量里抽取出来;而不是钻进语词的巢,像在过度拥挤的惊惧之中钻进自己,将一个诗人正在点亮的空间与时间熄灭。
在那首诗——《惶然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突然。”
还要惶惑。它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变得短暂而迟缓,破碎在人群中,
使我更加惶惑。但我看见无数个未来。
XY
2010.8.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