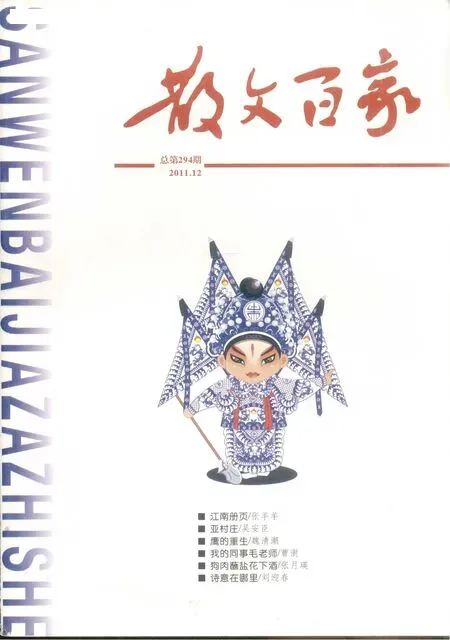拥山入梦
●周 建
安静的车厢里顿时骚动起来,心情豁然开朗,啧啧的赞叹声不绝于耳,一个个欢快的声音在车厢内回荡:联通,没信号;电信,没信号;移动,没信号!都没有信号了啊。我们来到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与外界隔断了联系。心头的欢乐就像边侧的山溪一样,在汩汩地流淌。所有的尘俗和喧闹与我们无关,所有的烦恼和纠结与我们无关。
我们到达长寿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好像从一个世事浮杂的尘世漂移进了纯净透明的净土,疲惫的心灵栖息在一方安静的天空下。人忽然轻松起来,话也多了起来,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霞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映照出些许鱼白来。我有点疲劳,躺在床上不想动,懒洋洋的,有着奇怪又有着好笑,眼下真是闷热的夏天,可床上却铺着厚厚的棉被,盖着厚厚的棉被,一点儿也不觉得暖或者热,没有一只蚊子,也没有一只苍蝇。一股股清冽而新鲜空气,从窗户从门缝挤进来,拥进来,凉爽而宜人,宜人而亲切,从未有过的舒畅。鸟儿唧唧喳喳地叫,一阵又一阵地叫,不紧不慢,不疾不徐,晨练一般。可是久居小城的我对这鸟鸣也有着麻木,竟然分辨不出来是什么鸟了,一种也分辨不出来。于是调动所有的积极因素猜:是麻雀?是乌鸦?是画眉?是白头翁?是啄木鸟?想着想着,就自个儿默默地笑。笑着笑着就起床了,开了门,推了窗,一看:是喜鹊,大群大群的喜鹊间或飞间或落下,呼朋引伴地,在舞蹈,在飞翔,在欢唱。
看到喜鹊。我格外地兴奋,巧遇老朋友的兴奋,自己仿佛也成了一只快乐的喜鹊。倒不是有着讨吉祥的原因,而是这么多的喜鹊在我居住的小城也已经少见了,就连层林尽染的老家,也不是很多,只是偶尔地在林间会冒出个喜鹊窝来。还记得只是在儿时见过一群又一群地喜鹊,站在枝头,落在院间,踯躅在田野,和农人争抢着粮食果实,多得让农人反感,赶也赶不走。可是这样的人鸟和谐的景观却渐渐地越来越少了。阅读一些资料了解到,喜鹊对空气质量的反应十分敏感,是灵敏的空气监测器。空气质量的逐步下降,逼得喜鹊渐渐地远走他乡,不再回来。而这里喜鹊声声,空谷回声,山风幽幽,气息清纯,飞鸟盘旋。
在登山的途中,我们走走停停,满山的生物陌生而亲切,不时有飞鸟掠过头顶,打破着大山的寂寞。转到山顶,凉风习习,云飘雾漫,芳草凄凄,虫飞蜂舞,山花烂漫。歇下来,坐下来,躺下来。山拥我入怀,我拥山入梦。
处在山头上,享受着凉爽的山风,放飞尘俗的心灵,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感觉那些群山就是一个个小山包,或是一只只轮船,或是一幢幢房子,融入了我的呼吸融入了我的生活。远远近近的群山相依相伴,层峦叠嶂,脉脉相连,耸入云端,如果用“雄伟、壮观、瑰丽、险峻、豪迈、阳刚”等词语来形容叙说他们,是不是有点太庸俗太渺小了?!我的心头滋长着不可名状的亲切和喜悦,痴痴呆呆,呆呆傻傻,真的不想走了,只想留下来,细细地看一看,数一数,瞧一瞧,想一想,给每一座山取个好听的名字,大声地呼唤着把对每座山的情感都抒发给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