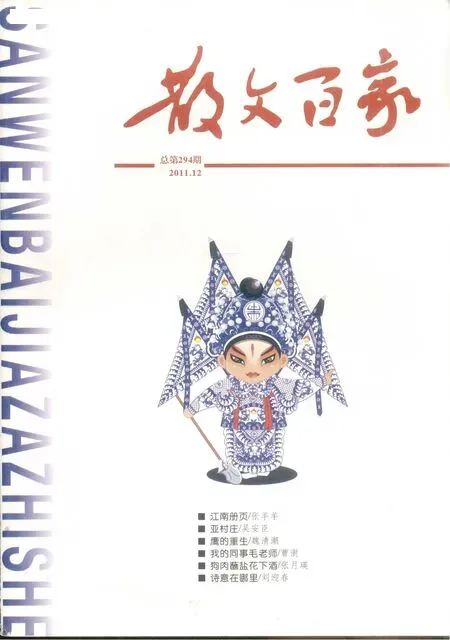江南册页
● 张羊羊
稻子
几乎相同的方言口音,几乎相近的童年背景,我同属南方的兄弟黑陶满怀恩情地写下南方精神的物质基础——“粥,依然是南方百姓最为信赖的食物,淘洗过的白米,从水缸里舀起的清凉河水淹盖它们,耐心的火焰使水米交融。渐渐地,米香溢起,锅内变得滚烫、粘稠——这,就是我们的粥”。熬粥用的是白扑扑的大米,弥散着健康的体香,照耀着南方少年在天地之间果断地拔节;熬粥最好是乡村普通百姓人家的土灶,稻草跳跃的火苗舔舐着漆黑锅底,在看似熄灭的灶膛,水稻的另一组成部分柴却依然用余温成全着米的个性的完美体现。
中国自古便有开门七件事之说,柴、米居油、盐、酱、醋、茶之先。那么我的身后应该要有这么一片田野:比如我最信任的画面出现在沉甸甸的五月或十月,勤劳业已成为生理反应的祖母淹没于厚重、浓密的穗子中央,风吹过,在浪之间她露出尚未埋葬的部分。这片田野里有二十四个守约的老客人年年光顾一次,我会感觉到一份踏实的信赖——像个即将踏上遥遥之途的少年,心里想着走不下去时可以回过头来,身后还有父母的肩膀,如同我们的转身还有生命与希望的依托和存在。
然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对这片土地的认识是如此的浅薄,仅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书写着一生潦草的命运。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日晒雨淋、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迈进,因为无法自控的慌乱节奏,它正丧失着与笔、墨、纸为伍时的严谨、节制以及它“减肥”后的体重。我的家乡有一条俗语“秀才不识字读半边”,当我用智能拼音怎么也打不出“粳”和“籼”时,只能借助《汉语规范字典》掩饰我的沮丧。而它们分别住在我手头这本1996年8月第1版、1998年6月第2次印刷的南方出版社的《汉语规范字典》的第246页和546页上,我和我的祖辈们至今还在用方言读着字典里[正音]部分说明的“粳不能读作geng、籼不能读作shan”。科学的程序化操作对于汉字的识别是不接受方言的,不接受它们的鲜明个性。
粳稻,水稻的一种,米粒短而粗,黏性小;籼稻,水稻的另一种,米粒黏性小,但出饭多,我居然不能正确地读出喂养我长大的粮食的名字(1979年6月—7月,40天雨量很少,部分河道干涸,造成杂交稻分蘖受影响。我列下这条记录是因为发生时间与我的密切:我的出生至满月期间世界给我的礼物)。然而我依然有部分的少年时光深深地记录下以下的农作经历;笨拙地插秧、杂乱地收割、颠晃地挑担、枯燥地晒谷收谷,期间因脱粒对于年龄的隐匿危险向来被大人阻止。
苏南太湖平原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在历经数代人对于耕作经验的积攒与修正,已然熟谙了泥土、季节、气候的性格,并与它们达成了完美的默契。于是这片土地除部分种植油菜、棉花、豆类农作物外,一贯遵守着稻麦两熟制的丰收规律,但稻子在南方百姓心中有着恒远的血缘之亲。
稻花香里说丰年,“丰年”这个产自农耕国度的词语在近二十年数典忘祖的挤兑中慢慢被人遗忘,像那些积淀着深厚农业智慧的农谚一样逐渐消失。我不知道一个城市要怎样克制贪婪和愚昧,才能停止大面积复制对于神造之物的摧枯拉朽之势,当我羞于把出生地与那个丰富饱满的词语“鱼米之乡”连在一起时,昔日田园牧歌式的江南把所有诗意沉淀在1980年代以前。倒是北方,一所叫沈阳建筑大学的新校址的景观设计项目使用了“稻田校园”的设计理念令人感到惊讶与欣慰:五千年中国土地和土地上的表情,平民的田地、庄稼和耕作,造田、灌田、种田、田的收获、田的欢乐和田的纪念,它们所承载的民族的个性和文化意义,较之虚伪的、空洞的、王家贵族的大屋顶和琉璃瓦的非常语言、特殊语言有更深层的意义。
是的,我将是一个远离土地、乡村、农业的中国青年公民中的一员,我如何延续对下一代来自土地恩惠的教育?我的亲人在慢慢别离世代居住的乡村家园和世代照看的土地的一刻终于热泪盈眶,农业文明的耕作乐趣在少数几代人之后将无法追忆。我知道,我有生之年一定会到故乡的残容面前回望一眼我的童年,我要在故乡的河流边深深磕几个响头,最后嗅一嗅晚风里稻浪铺展的惊人之美和孕育之息。
麦子
麦子是海子采摘的不倦诗意:“在青麦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收割季节/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放弃沉思和智慧/如果不能带来麦粒/请对诚实的大地/保持缄默”……这位已故的南方兄弟,无限热爱着村庄、镰刀、收割……一个个充实饱满的沉甸甸词语反复翻滚,它们永恒而庄重。当麦苗或麦芒适时铺满南方乡村的间隙,砌就了我们繁衍生息的碧绿或金黄婚床。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历史,由稻子和麦子这两位植物姐妹随季节交替轮流书写。
麦子本为北方主要食粮,南方人的粮食以稻子为主:一日三餐由粥和米饭组成。我的乡村生活麦子参与了极为重要的部分,我必须记录下几种帮助我健康发育的食物。
摊饼,关键词“摊”。面粉和水搅拌成糨糊状,起火热锅,抹灶布抹一遍铁锅。因为油贵,加入数滴润遍锅。舀一铜勺面糊沿锅浇一圈,已具雏形;用菜刀(指炒菜的长柄铲刀,切菜的短柄刀称薄刀)把积聚到锅底的面糊摊匀,直至摊饼熟,起锅如锅状。和面粉时如果没加盐,在摊饼快熟时洒半调羹红糖,红糖熔化渗入饼内称美味(那个年代我们对于糖或者直接点说甜的欲求远远大于咸);如果把摊饼切碎,放入油、盐、酱油、味精,加入韭菜,叫炒摊饼,这一种更是美上加美;还有“千层摊饼”,千层是夸张了点,正因为夸张愈加说明对于年月来说的奢侈。摊这种摊饼耗油,每一层都摊得细薄,贴锅的那面翻过来再浇上油,摊一层面糊,如此反复,应该有五六层吧。千层摊饼因芝麻的参与就更香了,一锅千层摊饼吃之前还认真地切成好看的菱形。
团子。关键词“包”。面粉加温水揉成均匀的面团。馅是水焯熟的蔬菜剁碎,多为青菜和霞菜,加佐料拦匀,也常用红糖作馅。包团子时熟练地用双手手指拿捏,至半碗状,塞入馅,左手托住,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相互配合,慢慢收口,直至馅完全包在里面。双手再搓圆。水沸后下锅,团子先沉后浮,即可食。
烂块。关键词“夹(读ga,平声)”。烂块这两个字是我自己想出来表达方言的,可能其他地方叫面疙瘩。烂块并不烂,实际上蛮有嚼头。夹烂块比较简单,也是面粉加温水调匀成面团,用铜勺舀时在钵头口刮一下(可能铜勺刮体头之间的动作也有夹的意思),烂块形状没有规则,大小也不一。夹烂块一般是隔夜有剩饭,煮泡饭又怕吃不饱,于是在煮开的泡饭里夹几个烂块既不浪费粮食又是一天早餐,烂块里如加有乌豇豆我就更喜欢了。
面条。关键词“擀”。擀:用棍棒碾轧,所以家家户户有一根圆、长的擀面杖。将面粉与水调成面团,用手揉匀,然后平放于桌子上,用擀面杖向四周用力擀开。面块擀到一定大小时,将擀面杖卷入其中,面块紧紧包裹住它,并用手不断向外推卷。反复几次后,将面块展开,撇上一些的扑面,换一个方向把擀面杖卷入其中,进行推卷,反复推、展开,撒扑面,直至将面团擀成薄片为止。将擀好的面片折叠如围巾,切成细条,煮面时配以时令蔬菜即可,儿时手擀面里拌两调羹肉汤那更美哉。
馒头。关键词“蒸”。南方的馒头与北方馒头不同。腊月二十过后,每户人家有蒸馒头的习惯,并用硬币拨刷蘸上红颜色液体的牙刷或用一截麦秆“点红”,那是新年即临的气氛之一。包馒头会塞入肉、菜、芝麻、豆沙等馅,就是北方人说的包子。也蒸少量不放馅的馒头。半球形,主要用来祭祖宗用。加糖制成长条形的叫“大腿”,切成片,晒干,平时充当点心。时常是做早饭时放粥锅上蒸一下,或油煎。
以上种种食物制作所包含的一系列动作和过程由奶奶或母亲熟练呈现。说实在的它们谈不上美味,只是充饥用的,那时候一天的劳动消耗太多的体力,即便我之类很少涉及农事,也总是感觉到饿。随着居住地的变换,人的胃好像缩小了很多。厨房间从以前灶膛上的大铁锅到现在煤气灶上的小不锈钢锅,似乎进行着同样的三餐,可真是胃小了吗?我们对于山珍海味倒是来者不拒了。
我在不断地书写故土平原上的植物,却差点错过了它,这让我感到羞愧。多年后,我满身疲惫穿越城市的重重围困终于来到一片麦地,那里涌动着股股浓郁的热息,绿色波浪里我还能看见已故的母亲在躬身劳作,仿佛在弥补她余生未能尽守的劳作方式的那段时光,顷刻间我会幸福得满怀热泪。母亲抬起头,她的汗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光辉里还包含了先民最初对麦子的朴素欲望和神圣的生命蕴藏。
鱼
我对汉字的审美,大概符合唐时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腴。一但减肥了,就感觉上吐下泻吃错西药般病恹恹的。我喜欢看繁体字,像极了一张农业中国内容丰富的田野的脸,有亲近感,也会觉得自己更有来处些。汉字的唯一性有其神秘而不可昭揭的地方。其他不说,我用草书填籍贯江苏的“苏”字,就有草草办事的感觉,以前的“蘇”,写起来眼前就浮现出青草繁茂的乡野,水里的鱼和稻田里的禾相邻,密密麻麻的景象似乎才配得上“鱼米之乡”这个称号。
在江南水乡生于斯长于斯,对于鱼的感情是不含糊的,鱼水情鱼水情,水滋养鱼也滋养人,人爱鱼也像水爱鱼一样,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生的宰割,后者则是对生的承载。一个“鲜”字由鱼和羊这两位低一级食物链的代表来概括是有它的道理的,常州有著名的“全羊宴”,但我这人不吃羊,于是把对“鲜”的全部认识寄托在其一半的鱼身上了……即便是冬天,把小鳑鮍、小鲦与腌咸菜放一起做碗菜,早晨就着鱼冻下粥,也堪称一道美味。
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对各地风靡的泉水鱼、酸菜鱼之类几乎不屑一顾,看那菜的品相已经破坏了我的食欲,我估计这些菜的出处大多来自不产淡水鱼和少产淡水鱼的地方,由于运输的问题鱼无法保鲜,就想办法用辅料、佐料来提味,我觉得这些地方的人们从一开始就缺少了对鱼之鲜的基本认识,所以他们的期待指数远远停留在出租车的起步价上,记得有年去西安,好客的朋友热情地说,今天得来条鱼了。上来一看,红烧鲫鱼,在我家乡,鲫鱼与鳊鱼、草鱼、鲢鱼之类均属于最普通的家常菜,常州北依长江,南枕太湖,所辖的武进有滆湖,金坛有洮湖,溧阳有天目湖,另有数以千计的大小湖泊、河流、池塘镶嵌交织于在乡野村落间,产的水乡鱼品种就近百余种。
许多年前,苏东坡大饱了江南水中珍品鲥鱼的口福后感叹“芽姜紫醋炙鲥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南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读这诗就挺馋的;许多年后,若想品尝野生刀鱼、鲥鱼、河豚此长江三鲜已经近乎奢望,诸如鳞白如银的外形和骨软如绵的内质皆变成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至于原因,无非是泛滥捕捉以装胃这只无底的口袋所致,即便濒危禁捕,仍有渔民经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甘作食客的帮凶。于是成了如今现状:我国从2002年起,从美国引进了鲥鱼,当时引进的鱼卵,一粒鱼卵卖到1万元人民币,再加上其他成本,“到岸价”高达2万元人民币。
然虽此三鲜与长江渐失亲缘,孕育吴越的太湖依然恩赐着滨水而居的子民另三鲜:白鱼,白虾,银鱼。银光闪烁的白鱼细骨细鳞,肉质细嫩,鳞下脂肪多,酷似鲥鱼,是太湖名贵鱼类;无鳞、无刺的银鱼更无腥味,营养丰富,二寸余长,圆润透明,像极一根根悦目的洁白玉簪,亦为太湖名贵特产;白虾通体透明,也称水晶虾,壳薄、肉嫩,鲜美无比,若作本地传统名菜“醉虾”,上桌时还鲜活蹦跳,鲜嫩异常,此是即便晒干后去皮,也还是名贵的“湖开”。
“太湖三白”与“长江三鲜”都属性娇之物,大都离水即死,因此虽然这座城市里以“鱼舫”、“渔庄”、“渔村”为缀名的饭馆一个挨着一个,你还是得往江、湖边的小渔村就近享用才能得其“鲜”的真谛。正因为其鲜,也就无须多放佐料、多琢磨制作方法,清蒸白灼略微几粒葱花即可,色、香、味的话我说的都不能算数,只得由食者亲临体验视觉、嗅觉、味觉的三者交融。
也正因为“长江三鲜”和“太湖三白”的名贵。它们还是走不进寻常百姓家的,但老百姓依靠着先民智慧的积累,在普通鱼类中下工夫,竟也能悟出“青鱼尾巴鲢子头”的家常菜,并逐步做成了本地的名菜。典型的就有“溧阳天目湖鱼头”和“戴溪青鱼”。
天目湖鱼头早已闻名遐迩,品尝过的食客更会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天目湖鱼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天目湖周围山体的绿色植被过滤了湖水,湖底又为沙质而非淤泥,这造就了清澈甘甜、纤尘不染的天目湖水质,其中生长的鱼类也没了土腥味。天目湖砂锅鱼始创于江苏常州的天目湖宾馆,据说以前水库职工把鳙鱼捕上来,给客人作下酒菜,由于胖花鲢太大,烧时主人常将肉不多的鱼头斩下扔掉。水库有一老书记觉得可惜,就将鱼头捡了回来,放在锅里煮汤喝。经过几年的摸索,煨出的鱼头,味儿越来越鲜美,汤浓如乳,香气扑鼻。再经过从部队转业来到水库食堂当炊事员的朱顺才近三十年的精心烹制后,现在已经成为了江苏最佳传统名菜之一。做天目湖砂锅鱼头选用的是天目湖水体中天然生养的大花鲢鱼头作原料,纯天然天目湖水为汤基,辅以葱结、生姜、料酒、香醋、香菜、胡椒等,撇除浮油,在火上煨煮数小时,一道汤色如乳、鱼肉白里透红、细嫩无比的砂锅煨鱼头就可以上桌了。
戴溪青鱼似乎更平民化,在资源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凡武进洛阳人家有红白喜事,餐桌上最后的压轴大菜必是“氽青鱼”。但随着青鱼饲养户使用颗粒饲料来缩短鱼的生长周期从而降低鱼的生产成本起,这种青鱼变得体形肥胖,肉质松软,一下锅就缩水,鱼肉酥散,难以夹筷,无论是外形还是口感,较之喂养天然饲料的青鱼逊色多了,青鱼的身份就此一落千丈,渐渐淡出餐桌、酒席。现在的戴溪青鱼又“游”回来了;在每天以螺蛳、蚬子等贝壳类为食物的环境下长大的青鱼,体形“结练”不虚肥,肉质硬实。春秋淹城的农家菜美食街有家“戴溪青鱼馆”,以8—10斤的新鲜青鱼加工而成,宰杀洗净后切成2—3厘米条状,加盐腌制一定时间,配以适当比例的佐料加工而成。红烧时,鱼皮被烤得酥脆,香气袭人;氽青鱼汤时,汁浓味鲜;做成鱼丸时,鱼肉滑嫩。但无论哪种烧法,只要是正宗的戴溪青鱼,随便用筷子夹一块鱼肉,决不会松散,味道鲜美而不肥腻。尤其以青鱼尾巴做的一道“红烧划水”,色泽红亮,鱼尾油润,肉滑鲜嫩,堪与鲜鱼翅媲美。
海边的人说海鲜有多好吃,我尝了感觉粗糙,就像海水咸湿没有淡水那样清爽。当然,我并没有强迫海边的人承认湖鲜、江鲜比海鲜好吃,这问题就像北方人说玉米窝窝比南方的米饭香,我却难以下咽,那是粗粮。只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是苏南秀水中“太湖三白”与“水八仙”的荤素搭配下滋养长大的,于是长成了“细粮”的体格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