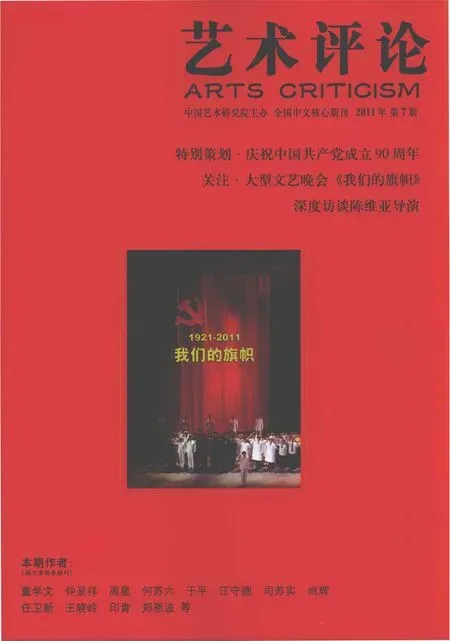新中国红色舞旅追思
于 平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新中国的文艺创作在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之时,必然从多情境、多视角、多义涵出发去塑造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新中国的舞蹈创作在这方面也有着精心的创编和精彩的呈现。在对这一创编足迹的追思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条令人感动、令人振奋、令人向往的“红色舞旅”。
一、红色舞旅的历史节点
追思新中国舞蹈创作的红色舞旅,我们会看到一些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历史节点。捕捉并分析这些“历史节点”,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特征:其一,“历史节点”往往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应,体现出社会发展“关键点”与“时段性”的统一;其二,“历史节点”往往体现出特定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时代精神对历史义涵的选择;其三,“历史节点”的更替与延续,构成了红色舞旅的丰富性与深邃性,使我们的追思有了一个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的观照。
“战士舞蹈”开启红色舞旅
新中国建国前,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舞蹈活动中,也会有共产党员的形象塑造,那一时期共产党员形象塑造的特点有三:其一基本是以群体形象的形态呈现,其二主要是在“扩红救亡”的军事斗争中呈现,其三大多是以“歌舞活报”的综艺式样呈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舞蹈活动,与其说是塑造共产党员的形象,不如说是宣传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和表现共产党员人的革命实践,比如说中央苏区时期的《当兵就要当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进军舞》等。当然,在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以“秧歌剧”来歌颂战斗英雄或生产英模的作品,《刘顺清》作为当时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体现出运用包括舞蹈在内的综艺手段塑造共产党员形象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建国前夕,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表现,成为舞蹈创演的主要视点。吴晓邦创作的《进军舞》和梁伦创作的《乘风破浪解放海南》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舞蹈活动作为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创演了《母亲在召唤》、《最可爱的人》这样的舞剧呼唤正义与和平,一方面也创演了《罗盛教》、《不朽的战士》(黄继光)等“最可爱的人”的舞蹈作品——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是党的战士、就是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聚焦“党的战士”来塑造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体现出红色舞旅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崇尚与弘扬。接踵而来的舞蹈《狼牙山》、《十八勇士》、《刘志丹少年先锋连》、《飞夺泸定桥》等都体现出共产党人身上迸发出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些作品形成了红色舞旅第一段历史节点。
红色舞旅创造“优秀样板”
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舞蹈”构成了红色舞旅的主要脉络,特别是1959年新中国建国10周年之际,“战士舞蹈”的不懈追求使红色舞旅开始有了大型革命现代舞剧,由广州等区战士歌舞团创编的《五朵红云》和由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编的《蝶恋花》,成为大型舞剧成功塑造共产党员形象的“合珠联璧”。《五朵红云》的七场戏分别是归来、劫笼、暴动、初胜、找党、挺进和解放,表现的是黎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蝶恋花》则是着力塑造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革命先烈杨开慧的光辉形象。这两部大型革命现代舞剧不仅提升了“战士舞蹈”的整体创编水准,而且实现了红色舞旅重大历史进程。
5年后,也就是新中国建国15周年庆典的1964年,我们的红色舞旅迎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当然首先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问世,同时还有两部产生广泛影响的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从《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到《复兴之旅》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也可视为红色舞旅的宏大叙事,但我们在此主要是聚焦“舞旅”本身。大型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是红色舞旅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作为革命现代题材的芭蕾舞剧,它成功地塑造了洪常青和琼花两位共产党员形象。由于以洪常青和琼花的形象塑造为舞剧的中心任务,该剧六场戏的场景和行动都围绕“形象塑造”来展开:从序幕的“琼花出逃”、一场的“常青指路”、二场的“琼花诉苦”、三场的“琼花违纪”、四场的“常青授课”、五场的“常青阻敌”和六场的“常青就义”,舞剧堪称思想内涵深,艺术水准高。毛泽东观看该剧后曾高度评价说:“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一时期与《红色娘子军》堪称“双璧”的另一部革命现代舞剧是《白毛女》。《白毛女》的序幕有一个概括性的提示,说明该剧是千千万万受苦人家世的缩影,说明那些“诉不尽的仇恨,汇成波浪滔天的江和海”。此后的八场戏分别是悲风年关、不堪凌辱、满腔仇恨、深山寒暑、减租反霸、狭路相逢、走出山洞和报仇伸冤,揭示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可以说,《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作为革命现代舞剧与《五朵红云》一脉相承,虽然二者分别改变自同名电影和同名歌剧,但主题却如《五朵红云》的主题歌所言:“红旗插在五指山顶,天空落下来五朵红云……共产党是再生父母,共产党是民族救星!五指山前千条路,一心跟党奔前程”。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因其成功的艺术创造,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树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亦成为我们红色舞旅的“优秀样板”。
红色舞旅的艰辛跋涉
革命现代舞剧的一“红”一“白”是对当时召开的音乐、舞蹈“三化”(即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座谈会的积极响应。这两部舞剧在被指称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后,开始了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普及的芭蕾艺术的大进军。事实上,《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普及既是芭蕾艺术的普及也是舞剧艺术的普及。需要指出的是,“文艺样板”普及的年代正是“文艺百花”凋零的时期,“八亿人民八出戏”使得“革命文艺”有些“革文艺命”的味道。因此,当“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动乱被制止,红色舞旅开始了新的历史选择,开始了新的艰辛跋涉。虽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舞剧,也塑造了不少共产党员的舞剧形象(如在芭蕾舞剧《红缨》基础上创作的《沂蒙颂》,根据同名京剧改编的芭蕾舞剧《杜鹃山》、《苗岭风雷》等),但都因其服务于具体的政治任务,在我们步入“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就云消烟散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缅怀杨开慧的舞剧纷至沓来。除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复排《蝶恋花》独领先机外,中央芭蕾舞团(时称“中国舞剧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分别创作了《骄杨》和《骄杨颂》,与此同时,还有湖南省歌舞团创作的《红缨》。最初的《蝶恋花》,重在塑造大革命时期“武装斗争”中的杨开慧形象,舞剧《红缨》的重点关注也在于此。但后来新创的《骄杨》和《骄杨颂》,更强调杨开慧作为毛泽东革命伴侣和战友的身份,强调“骄杨”值得“大骄特骄”的境界和情操,使得这一革命烈士的缅怀在当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批判。
接踵而来的是红色舞旅对张志新的哀悼,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呼应。在当时影响较大的一是双人舞《割不断的琴弦》,一是独舞《无声的歌》。作为共产党员的时代形象,除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罗盛教、黄继光外,具有重大影响的首推张志新,而且在舞蹈表现中着重关注她被行刑之前遭遇“割喉”的惨烈。这也是第一位为维护党的正确路线而遇难的“斗士”。共产党员形象、特别是作为时代先锋的共产党员形象不易用舞蹈表现,后来的舞蹈创作较为成功的还有《天山深处》塑造的郑之桐和《高山下的花环》中塑造的梁双喜。在缅怀杨开慧和哀悼张志新之后,我们的红色舞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开始了沉思与求索……
红色舞旅的一路飘“红”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型舞剧创作形成鼎足三分的局面,一足是从《丝路花雨》起步的中国舞剧的“新古典舞派”,一足是从《召树屯与楠木诺娜》起步的少数民族舞剧之花,还有一足是展示鲁迅、曹禺、巴金作品的中国芭蕾画卷。小型舞蹈创作(如双人舞《小萝卜头》、独舞《囚歌》等)虽使红色舞旅不绝如缕,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在我的印象中,一是出了些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士舞蹈”,如双人舞《再见吧,妈妈》和《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当然还有追忆当年“上甘岭战役”的《一条大河》;二是表现抗日战争的“战士舞蹈”,从60年代的“五壮士”(《狼牙山》)实现着向80年代的“八圣女”(《八女投江》和《八圣女》)的转换,红色舞旅由“壮”而“圣”了;三是钢琴协奏曲《黄河》作为舞蹈音乐被不断阐释,其中当然也可视为红色舞旅的心路历程。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由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根据同名小说创作的大型舞剧《高山下的花环》,它的序及五场戏分别是乳汁哺育、激战前夜、浴血疆场、凯旋思亲、情牵碧水和魂系青山,堪称红色舞旅在这一时期的力作。
1999年迎来了新中国建国50周年大庆,它对于红色舞旅的再度启程有重要推动作用。广东的《星海·黄河》和山西的《傲雪花红》南呼北应,将冼星海、刘胡兰两位革命志士拉上了当代舞台。《星海·黄河》选择了一条具有双重文化视角的“黄河”:一方面是沉积着中华民族数千年苦难史、奋斗史的黄河之“水”;一方面又是作为中华民族苦难史、奋斗史艺术写照的《黄河》之“唱”——这就是由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水”之黄河与“唱”之黄河相激相撞,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中走向永恒……,《傲雪花红》作为讴歌刘胡兰的舞剧,是一部通过奉献“花季人生”来认同崇高的舞剧。因此,“花季”成了舞剧戏剧场景转换的显要表记:一幕《杨花飞》、二幕《山花红》、三幕《菊花黄》、四幕《雪花落》——“是花还是非花”,在这里不是禅宗公案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象征……当刘胡兰迎着漫天飞雪昂然走向铡刀,当一面面血色的红绸自天而降,共产党员的形象在舞剧中升华,舞剧也因为刘胡兰顶天立地的壮举而成就了《傲雪花红》撼天动地的佳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舞剧创作的红色舞旅不断壮大不断奔流不断澎湃,甚至从剧名上就能看到红色舞旅一路飘“红”。《闪闪的红星》、《红梅赞》、《风雨红棉》、《天边的红云》、摩肩接踵,正可谓“红”流滚滚,气壮山河!《闪闪的红星》的剧情依托于70年代广为传扬的同名电影,着力塑造“党的孩子”潘冬子的形象。这是一部在总体结构上没有场、幕之分的“无场次舞剧”,通过多次出现的“红星舞”有机地结构起舞剧的情思和情节,体现出“红星”(党的象征)在全剧中的贯穿性和凝聚力。《红梅赞》也属于“无场次舞剧”,这是一部确立了“整体舞蹈剧场”观念的舞剧,由平台、布景设定的实体空间和灯光、道具设定的可变空间,不仅引导着舞者的空间运动形态,而且构织了舞者的空间运动氛围,由此而成功地塑了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群像(包括华子良、龙光华、小萝卜头等等)。《风雨红棉》表现的是20年代大革命时期血雨腥风中结伴同行的革命志士周文雍和陈铁军,舞剧的三幕戏分别称为《相知》、《相隔》和《相约》,这是紧扣着二人的人生际遇来结构的,而其人生的境界升华在“刑场上的婚礼”中得到了令人无比崇敬的体现。《天边的红云》是一部以“人物”而非以“故事”立剧的“舞蹈诗剧”,塑造的是长征时期八路军女战士的群像,5位女战士分别是某部护士、某部教导员、某部炊事员、某部司号员和某部班长,分别名之曰云、秋、秀、娃和虹。可以说,这部“舞剧诗剧”的成功一是得力于红军群像氛围营造的雄浑磅礴,二是得力于性格人物刻画的缜密机巧。《天山芙蓉》虽不称“红”,但也是一部置身“红”流的重要舞剧,它以系列舞蹈剧的样式表现新中国建国初、8千湘女入伍赴疆为屯垦戍边奉献壮丽人生的往事。需要进一步提及的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红色舞旅的大型舞剧又推出了《铁道游击队》和《三家巷》,这两部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剧在持续延伸着红色舞旅的前行轨迹。
二、红色舞旅的经典表情
新中国红色舞旅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但红色舞旅观照并加以阐释的对象,至今更是有90年的时光跨度。我们知道,历史的阐释者大多是通过阐释历史来敞亮心迹,言说历史的目的大多是借历史言说。因此,不同历史节点的红色舞旅就具有了不同的经典表情。之所以称为“经典表情”,一是因为这表情作为观照对象具有历史的代表性,二是因为这表情作为观照主体具有时代的特征性,三是因为表情在历史烛火的时代朗照中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向往的境界。
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建国的前10年,是“战士舞蹈”及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革命现代舞剧构成了红色舞旅的时代特征。作为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仅面对着残存反动势力的捣乱破坏,而且面对着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包围。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的文化建设,无疑需要坚定一种信念并张扬一种精神,坚定一种能有效应对现实的信念,张扬一种能有机赓续传统的精神。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能有效应对现实的信念只能是我们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传统。从《进军舞》、《乘风破浪解放海南》到《罗盛教》、《不朽的战士》,从《狼牙山》、《十八勇士》到《英雄邱安》、《艰苦岁月》,我们透过不同的观照对象和观照方式,能看到一以贯之的、整体倾注的经典表情,这便是“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这种“革命英雄主义”作为红色舞旅最初的经典表情,当然是一定时代背景的历史选择,同时也与我们舞蹈表现方式的历史认知分不开:比如我们注重从外部动作的“可舞性”去选择题材并着意强化题材的“可舞性”,这就特别容易关注战斗场景并表现“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比如我们在新文化的建设中希求摆脱“柔曼”并创造“阳刚”的舞风,我们也寻求到了“革命英雄主义”这一重要的形象依托……毫无疑问,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既是那一时代精神的呼唤,又是时代精神前行的动力。
翻身解放、改地换天的工农武装割据
其实从革命现代舞剧《五朵红云》起,“翻身解放,改地换天的工农武装割据”就成为红色舞旅的一种经典表情。这种经典表情的内涵与前述“革命英雄主义”一脉相承,但内涵却更为丰富,表述也更为深邃。从《五朵红云》起,到《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也包括《红嫂》和后来的《沂蒙颂》、《杜鹃山》及《苗岭风雷》,似乎都在通过“工农武装割据”来实现受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来实现封建社会的改地换天。“工农武装割据”作为红色舞旅的经典表情,与“革命英雄主义”对一种精神状态的呈现不同,是在呈现一种行动目标,呈现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其当时对应的社会主张便是“阶级斗争”作为第一要务时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时期的红色舞旅通过柯英、琼花、喜儿、红嫂等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通过她们投身“改地换天”的革命,申说劳苦大众必须通过武装革命才能推翻压迫自己的反动政权,申说这一武装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并进一步申说无产阶级必须以“解放天下”为己任……因此,这一时期红色舞旅的经典表情不仅是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更是具有远大革命理想的。
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不屈捍卫
经历“文革”后,人们开始了痛定思痛的历史思索。70年代末、80年初的舞蹈创作,有过表达思想困惑、迷茫、求索、消沉、奋起的独舞《希望》,也有过明媚春光中“小桥流水”的浅酌低唱,但构成红色舞旅的作品,并非单纯地“讴歌”和“颂扬”,对杨开慧的缅怀和张志新的哀悼之所以成为经典表情,是在颂扬“骄杨”时斥责“浊江”,是在讴歌“真理卫士”时鄙视“政治文痞”。但平心而论,在整个80、90年代(新中国建国50周年庆典前),可算做红色舞旅的作品十分有限,我们的舞蹈家不仅在重新思考表现怎样的“革命”,而且在重新思考怎样去表现“革命”。除了通过杨开慧、张志新的形象塑造来表现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不屈捍卫外,此时对正义战争中革命军人的讴歌也在转换着视角——如果将80年代初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再见吧,妈妈》、《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以及大型革命舞剧《高山下的花环》与当年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可爱的人》、《不朽的战士》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在革命英雄主义之中亦有深深的人生之爱,是母子之爱、战友之爱支撑起我们的“英雄主义”——我们的“革命”也是有情有义的革命,也是大爱大善的革命。
对青春的无悔选择、无愧奉献
跨入新世纪的红色舞旅,显然是青年舞者对“革命”的深层认同和重新发现。在此认同和发现中,革命者为革命捐躯的过程似乎比其为之献身的理想有了更重要的意义——青年舞者们发现并认同的,是革命者对青春的无悔选择和无愧奉献。从《红梅赞》中以江姐为代表的“把牢底坐穿”到《风雨红棉》中周文雍、陈铁军的“刑场婚礼”,从《天边的红云》中五位女性在憧憬中献身到《天山芙蓉》中多情湘女在磨砺中扎根,从《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人生选择的果决到《傲雪花红》中刘胡兰慷慨赴义的凛然……似乎都聚焦为“对青春无悔选择、无愧奉献”的经典表情。事实上,这一经典表情对于我们当下行进的“中国道路”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意义的实质在于,青春不能碌碌无为,青春不能庸庸虚度,青春的选择与奉献既是价值的追求,也是一种价值的所在。从红色舞旅经典表情的时代义涵来看,无悔选择、无愧奉献的青春也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也包含“服务人民大众”的意向,当然也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不屈捍卫紧密关联。可以说,红色舞旅的经典表情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各有侧重,但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中浑然一体。这也是我们红色舞旅经典表情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三、红色舞旅的美学风范
追思红色舞旅,虽然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起的动议,但通过“追思”却发现它们在新中国的舞蹈创作中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也就是说,纵览红色舞旅的系列创作,可以看到它们对中国当代舞蹈的美学建构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当代舞蹈美学风范的重要构成和主导方面。由红色舞旅在解决创编问题时所探寻、撷取、拓展、创生的美学方法,涉及语言的提炼、结构的安顿、性格的解剖、情调的罗织、氛围的营造、境界的敞亮诸方面。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红色舞旅的原创和优创,中国舞蹈美学风范的当代性及独立品格都会大打折扣。
贴近现实的“新舞蹈”品格
纵览红色舞旅的各历史节点、各经典表情,可以看到它的节点无论怎样转换、表情无论怎样更替,其一以贯之的是贴近现实的“新舞蹈”品格。所谓“新舞蹈”品格,在理论上受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概论》的影响,也可以说吴晓邦在创编《进军舞》时就贯彻了这一理论主张。吴晓邦的动作理论,强调在人体动的“自然法则”上来发展和创造舞蹈语言,强调必须从实际生活中、从生活的情感和想象中去塑造人物形象和组织动作语言。事实上,红色舞旅的几乎所有舞作,都遵循或者说都体现出这一追求,因而也都共同地具备了“新舞蹈”品格。当代意义上的“新舞蹈”品格,其实并非某一类型化的动作语言风格,因此在舞蹈语言形态的作品分类中,它们无法、也不屑跻身在所谓芭蕾舞、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类型化动作语言风格的旗号下,而是以“非类型化”自成一类,“这一类”时而被人唤作“当代舞”时而又被人唤作“新舞蹈”。实际上,这正反映出红色舞旅不为类型化动作语言风格所累而从贴近现实中去创造“非类型化”的“这一个”。正是因为具备了贴近现实的“新舞蹈”品格,红色舞旅的诸多舞作不仅艺术形象的个性鲜明,而且艺术语言的性格独特,黄继光不会类型于罗盛教,五壮士不会类型于八圣女,刘胡兰不会类型于陈铁军,江姐也不会类型于杨开慧……可以说,红色舞旅的舞作创编是形象第一,形象的性格刻画第一,形象性格刻画的语言表现第一,而这必须走“贴近现实”而非“贴近类型语言”的创编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红色舞旅不仅传扬了中国革命的经典表情以激励后人,而且引领了一种真正具有动作语言“原创性”的时代舞风。红色舞旅的这一美学风范是立足时代标高的风范。
聚焦崇高的悲壮情怀
在动作语言的创编上贴近现实,在形象塑造的内质上则聚焦崇高,红色舞旅的“聚焦崇高”几乎都体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悲壮情怀”,因而“聚焦崇高的悲壮情怀”也成为红色舞旅显著的美学风范。所谓“红色舞旅”,基本上以革命志士为表现对象,基本上表现的是革命志士面对强大邪恶势力时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因为目标的“正义”和行为的“坚毅”而具有了“崇高性”。作为审美形态的一个重要范畴,“崇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美”,也即不同于那类具有完整性、和谐性、典雅性的“优美”;相较而言,“崇高”更倾向于用粗砺、剧烈、剽悍的形态去凸显精神的力量,如康德所说:“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是因为它们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力量……”事实上,我们红色舞旅的创编,主要的创作动机就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精神力量,是为了民族精神的昂起和高扬。为了提升和激扬民族的精神力量,红色舞旅在对革命志士进行表现之时,都必然将“牺牲”作为舞作的高潮来加以表现,而为“牺牲”所做的种种铺垫——磨难、求索、坚贞、信念等等,都成为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有力注脚。这样,红色舞旅在聚焦“崇高”之时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悲壮氛围,寄寓了一种深厚的悲壮情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色舞旅是一种对史迹的缅怀,更是一种对时风的匡正——特别对那种“娱乐至死”、“过把瘾就死”的欲念而言是如此。红色舞旅的“聚焦崇高”会让我们铭记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无数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想,“聚焦崇高的悲壮情怀”是我们当下民族精神建设中最应倡导的美学风范。
在性格成长中结构“戏剧性”
我们的红色舞旅之所以让人们觉得历久弥新并经久难忘,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就在于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丰满性格和鲜明形象。就红色舞旅的创编历程来看,对于革命志士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有一个由单纯而丰富、由简洁而饱满的过程。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张扬中,红色舞旅的性格刻画比较单纯,通常是在一个危难的情境中刻画临危不惧、勇往直前、攻坚克难、献身酬志的英雄形象,从《不朽的战士》到《十八勇士》、从《狼牙山》到《八女投江》等都是如此。到工农武装割据理念的彰显之时,性格刻画明显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舞作的情节构成看,往往是主人公由苦大仇深、报仇伸冤走向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在献身精神中饱含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如《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红梅赞》中的江姐等。作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红色舞旅的舞作编创不是为故事的叙述罗织“符号性”的人物,而是为性格的成长设计“戏剧性”的场景,这种美学追求不仅使戏剧场景的设计具有极强的指向性,而且使其转换体现出极强的必然性。需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强调在性格成长中结构“戏剧性”,不仅使“贴近现实”的语言创生品格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使舞作的戏剧结构形态各呈异彩:比如《红色娘子军》以洪常青、琼花“引导”和“被引导”的性格成长形成舞剧结构的“双重变奏”;比如《星海·黄河》在冼星海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中形成舞剧结构的“一柱擎天”;还比如《红梅赞》以江姐作为多个事件络状组接的“原点”,以人物的多色彩及其同“色质”形成“多彩同质”的舞剧结构。因此,在性格成长中结构“戏剧性”的舞作结构方式,不仅是红色舞旅舞作编创的特质,而且是我们舞作结构形态多样化的保证。
在情感交织中凝聚“主色调”
追思红色舞旅,当然会注意到“红色”是其主色调。这“红色”是作品洋溢的革命精神,是人物凸显的革命品质,是叙述贯穿的革命追求,是情感浸润的革命风采。正如红色舞旅的性格刻画不是一路直奔“高大全”,其情感抒写也不是单色素描“红光亮”。红色舞旅,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的红色舞旅,不仅在性格的成长性中强化了情节的真实性,而且在情感的交织性中强化了细节的生动性,使得在情感交织中凝聚“主色调”亦成为红色舞旅鲜明的美学风范。所谓“情感交织”,首先是基于情感表现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就群体而言体现为差异性,比如《红梅赞》中江姐、华子良、龙光华就是以不同的情感表现来显现共同的革命斗志;就个体而言体现为阶段性,比如《傲雪花红》中刘胡兰与女伴、与母亲、与八路军伤员之间不同的“爱”的呈现,就体现情感多样呈现的阶段升华。其次,“情感交织”必然包含情感冲突的对比性,红色舞旅的许多舞作都表现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都表现出崇高与卑劣的抗争,不同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是“情感交织”的一种基本状态:《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对于南霸天诱降的驳斥,《白毛女》中王大春对黄世仁罪孽的审判,《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对胡汉三奸险的警觉,《红梅赞》中江姐对甫志高丑恶的怒责……都是如此。第三,红色舞旅的“情感交织”恪守情感引领的主调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情感交织中凝聚“主色调”,让我们对革命志士的大爱情怀、大善理想、青春抉择、生命奉献产生信念的追随和心灵的崇仰。通过在情感交织中凝聚“主色调”,我们在红色舞旅真正产生了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守望理想、以情提升境界的作用。
追思新中国红色舞旅,我们从历史节点、经典表情直到美学风范,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红色舞旅”不仅是新中国舞蹈创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推动着新中国舞蹈艺术的创新和境界的提升,“红色舞旅”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而且一定会是我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思想财富和艺术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