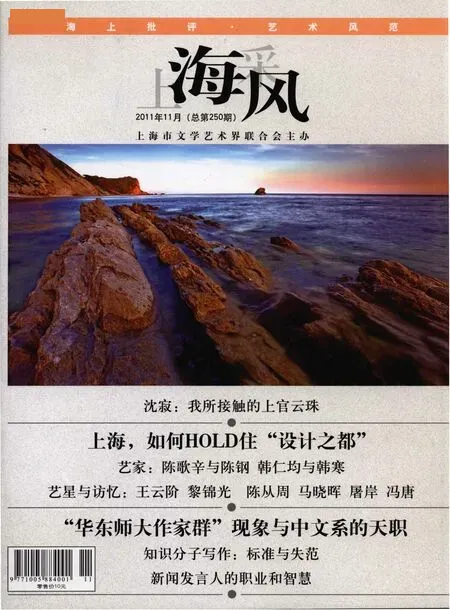仪式语言
文/梁文道
当我第一次实在地接触到中国内地,我发现它首先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刚由台湾回到香港,对彼岸的好奇如饥似渴,所以大量阅读大陆出版的报刊杂志,在收音机中仔细调频以便对准那些说普通话的频道,并且在有机会到大陆旅行的时候盯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让我惊讶乃至于着迷的是,那些文字那些言辞,我竟然怎么看怎么听都看不明白听不懂。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意义太隐晦,也不是因为它们的用字造词太过古僻,而是它们有着一种言不及物的空洞:浅白。但又不知所以:顺畅,却似不求对象的独自。
让我举一个例子。陈为军的《请投我一票》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纪录片。《华盛顿邮报》形容它是“关于一群八岁大孩子的,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所谓“政治戏剧”,指的其实只是武汉某小学有一个班,学生要选班长,于是导演拍下了整个竞选的过程,如此而已。尽管是一群三年级小学生,但他们在选前最后演讲中所说的话,却和当年迷惑我的那些言辞惊人地相似,且看这些八岁小孩如何熟练地操演我记忆中的中国内地。
首先是许晓菲,一个比较单纯的女生,她说:“面对困难,我也曾哭过,我也曾徘徊在放弃的边缘。即使有了困难,也应勇敢面对,不能过分依赖别人。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现,来回报给予我这一切的老师、同学,还有默默支持我的妈妈。选择许晓菲,将给你的校园生活增添更加亮丽的色彩。”
这就是了,即便年幼,这个小女孩也晓得说出这么一段很“正面”很漂亮的好话。但你能听得懂这段话吗?
我常常听不懂“新中国”的言语,是因为它们的每一个段落都这么正面这么向上:但那些编织它们的线索,却又是如此的暧昧,以致我根本搞不清那些字词存在的理由。例如,“即使有了困难,也应勇敢面对,不能过分依赖别人”,这句话当然很对,但一个班长候选人是怎么从这里推出下一句话的呢:“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现,来回报给予我这一切的老师、同学。还有默默支持我的妈妈”?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想当班长的小女生的演说结论:“选择许晓菲,将给你的校园生活增添更加亮丽的色彩”。也许“亮丽”这个词汇太有色彩也太过抽象,可是每一个小学生大概也都希望自己在校园里的日子更好过一些。然而,这位许晓菲到底凭什么去说服大家她可以让同学过得更好呢?她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答案,甚至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是承诺,只是陈述。
在我看来,这类言说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单纯的陈述。我不想对一个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吹毛求疵,而是她这番话真是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许多成人世界的言语特征。比方那些“领导致辞”和“工作报告”,总是有太多动人的陈述,而组织起它们的逻辑却又嫌太少,似乎说话就只不过是一组灿烂陈述的罗列而已。如果说话就是陈述的组合,那么这些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它们的对象又是谁呢?
回到《请投我一票》这部纪录片,回到那群忙着选班长的三年级小学生。依照常理,这些候选人演讲,应该是想说服同学,让他们信任自己,而且给出一套打动他们的理由。不过在这部不到一小时的电影里面,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绝非这些演讲,而是三个候选人和他们的家长施用在这场选战中的种种手段,比方说拉拢和分化对手的朋友,以谎言制造对手之间的矛盾,恐吓不支持自己的同学,甚至凭着父亲工作上的特权公然在老师面前贿赂全班同学。换句话说,比起光鲜明亮的演说,那些鸭子划水般的幕后工作才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也许这就是演说可以空洞可以苍白的理由了:明知不管用的东西,又何苦费心经营?
问题是为什么明明没用的话,我们大家还是要乐此不疲地说下去,而且假装它们有意义?为什么人人都觉得无聊,但仍然一脸正气地“聆听”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呢?数十年来,有无数领导政要严词谴责空话的习尚,他们反复叫人不要再说空话,然而很多时候,就连这些训斥本身听起来也很有空话的味道。
所以我大胆猜想,这些话尽管空洞无物,既不讲逻辑也没有实料,但它们依然是必要的。简单地说,那就是所谓的“场面话”了,是一种为了应付场面需要而存在的表演言语,与场面共同产生了仪式的作用。好比某些宗教的冗长仪典,就算参与者个个无精打采,但典礼还是要继续下去。虽然发言者并不真心以为自己的话很重要,可是昏昏欲睡的听众还是得强打精神地撑下去,然后媒体还要把那番话形容为“重要讲话”,以“响起了热烈掌声”去总结听众的反应。这一切全是为了仪式需要。假如连这些仪式都可以省去,那剩下的东西未免赤裸得过于残酷,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场面话”的功效。
由于是仪式上的“场面话”,我们便能理解何以它们总是依循一套套既存的模式了(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套话”)。那时为了措辞方便,既有现成词章,说话的人就用不着费力地别出心裁。例如介绍一场演讲和论坛,主持人百分百要在会前宣布接下来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至于那场演讲和论坛究竟有没有思想可言,并不是太过重要的事。
又由于是仪式,所以演讲者的表情、声调与动作也都必须尽量跟随一套现有的规范。总体而言,他们的神气应该配得上他们所说的话,因为那些话老是那么的伟大、光明、正确,他们也就得一路高亢激昂。如果到了结尾,那句话的音调就更要由高原走向更高的高峰。假如“思想盛宴”的“宴”字不拔高,观众的热烈掌声岂不就显得毫无来由?毕竟观众也是仪式表演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扮好自己的角色。
久而久之,这些言语还有了自己的修辞美学,比如好用数字。凡是组织论点,往往得把它们套进一组数目字构成的模型,例如,“一×二×三××”、“十大××”、“一种××,三个××”。编撰这些话的人不一定很在意那些论点站不站得住脚,也不在乎论点与论点之间的关系,他最关心的很可能是一套数目能否成形,读来是否易诵,这纯粹是种审美上的考究。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结合数字。于是诸如排比、反复、类比等种种句式也都成了惯见的措辞手段。且看《请投我一票》里另一位候选同学罗雷的演说,“我愿意发挥我的聪明才智,敢于管理、善于管理、乐于管理,为我们三一班增添集体的荣誉”,其中那句“敢于××、善于××、乐于××”就是当今最常出现的排比句式之一。
故此,我们不必担心这些话的言不由衷,也不用为了这些话脱离实际而困惑,更不要计较说话者在台上台下的表现是否判若两人。这一切全是仪式而已,这些话就像一群早已不再信神的叛教者的祷词,上帝已经死了,只是我们必须假装他还存在。
20多年前,我在香港要想尽办法才能摸到这套仪式的边缘,然后由此认识我曾经陌生的中国内地。今天,我总能在香港各种官式场合和文宣稿件里闻到它的熏香。可见香港真的回归了,他们开始举行自己的仪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