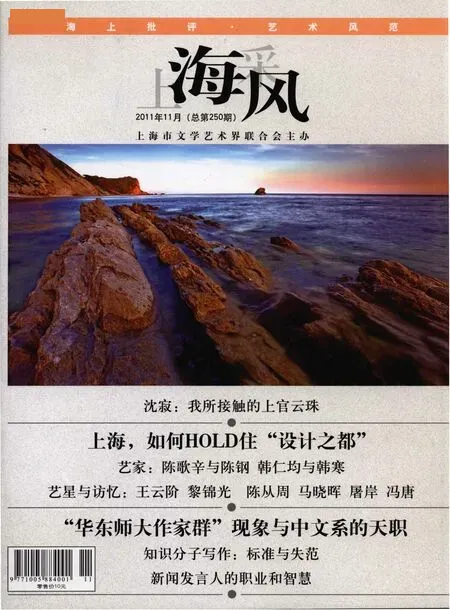话说上海
文/邓 刚
上海是一个名声响亮的城市。全中国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上海,外国人知道上海的也比知道中国其他城市的多几百倍。大连离上海千里之遥,但我刚呀呀学语之时,就知道有个大上海,不夜城,像外国一样繁华。而且在我们家乡的街上,只要是哪个女人长得漂亮白净,就会被冠以“上海大美人”的美名。为此,在我贫穷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幸福呀、美好呀、上海呀是同义词。那时谁要是去了上海,回来后总是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美好之旅,好像是他去了欧洲或美国。后来,我们发了疯地革命,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也就不太敢想上海,但暗暗地更加向往上海了。
后来终于去了上海,那是为了去买肉买糖买烟,因为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才能不靠票证买到副食品。东北人穷得全像眼珠子放着凶光的恶虎,经常蹿到这两个城市抢购,但在北京会遭到冷眼白眼甚至是呵斥,上海人也许和北京人一样瞧不起“东北虎”,但南方语言的柔软和体力的柔弱,让我们北方人永远也感觉不到他们的愤怒。我背着巨大的旅行袋子在上海繁华的市场商店里扫荡,真就像在嫩麦苗地里驰马。我似乎还注意了一下“上海大美人”,细腻白亮的皮肤果然比粗糙的北方女人秀美,她们能吃到这么多副食品,当然应该美成这样了。
上海第一次给我的印象确实是大,不过还有些人山人海的躁乱。
我真正像个人样儿,并堂皇地来到上海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小说《迷人的海》在上海荣获大奖,并第一次住进宾馆,虽然是与邓友梅、冯骥才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那时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大概只能是属于国家领导人级别)。不过使我惊讶的是上海人都很委屈,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用忧郁的表情对我说上海创造财富最多,纳税最多,但得到的回报却最少,也就是上海人只能是像蜜蜂中的工蜂一样在做贡献。我听了也很不平,要是北方人受此委屈,早就愤怒地满街骂娘了,可上海人却只能是小心翼翼地委屈。不过,这种委屈却又让我感到是一种巧妙的骄傲,我开始悟出上海人的精明。上海人确实精明,他们安排会议各种程序,不亚于现在的电脑,从接站到食宿到会议的座位到参观游览到回程机票费用包括下飞机到家之间的出租车费,全都井井有条、天衣无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令我更惊讶的是上海寄来的稿费单,数字往往会精确到角和分,而北方的傻瓜编辑们从来都是给个整数。如果你到上海改稿,随意地用了编辑部两本稿纸,他们就在寄你的稿费单上小心地打上括号,写上扣去稿纸费用(×角×分乘2本)。坦率地说,开始时我感到这是小气,然而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我才认识到这是现代经济头脑。
上海城市的繁华浩大与上海人的精明细腻让我往往不得其解,但这种精明最终令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具体到我身上就是文学艺术的先锋力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可以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面旗帜,而且这面旗帜有着巨大的统领力和感召力。全国很多作家都是先在上海打响后,才能走上全国的。我们辽宁绝大多数的作家都是走先上海后全国的路子。例如金河、达理、孙惠芬、谢有鄞等,当然还有我。我的《迷人的海》在北方遭到冷遇,是上海的编辑点石成金才让我光彩了许多年。所以至今只要想到上海这个字眼,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一片金光灿烂的色彩来。感谢上海的诸多编辑们,是他们辛辛苦苦地帮助和鼓励,使我以后又写出了不少东西,问题是我的懒惰和无能,没有长进,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让他们的心血在我身上白白流淌。惭愧的是,这么多年不写小说,但上海的编辑们见到我却依然是亲切是期望,没有半点冷落的意思,这种轫性的情感能穿透一个人坚硬的皮肉,并令人产生痛不欲生的感动。北方的编辑们热情来得快也走得快,时间一长就去你妈的早就忘得精光。
几年前去上海参加活动,站在黄浦江边遥望浦东,不禁有种现代式的震撼。当然也有人说三道四,我们这个民族由于文化的深远和肤浅,对所有的事物都能品头论足,最现代的也能居高临下地贬斥,最落后的也能发出美妙的赞美。我听到过不少对上海的褒贬议论,然而我从来都是不以为然。反正,上海今天展现出的画面,是我脑海里对现代化前景的一种认同。因此,只要我们大连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吹嘘自己时,我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到上海去看看,然后再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