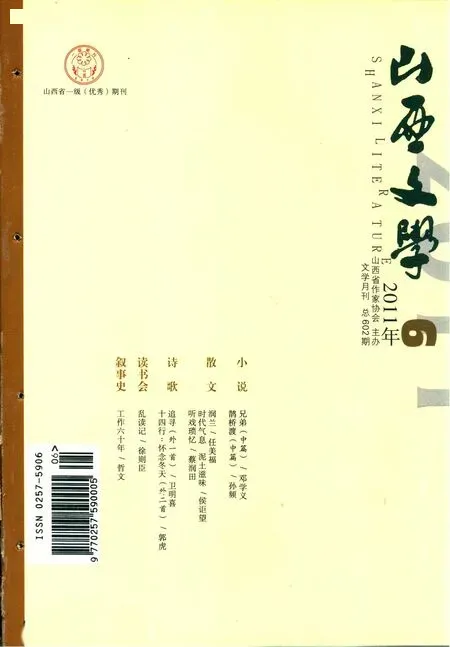乱读记
徐则臣
乱读记
徐则臣
天使与魔鬼
读《长路漫漫》时,我要不断地做两件事:一是反复回头看作者伊斯梅尔·比亚的简介,二是不时回想我自己的中学和大学之初的生活。我要一次次确认伊斯梅尔就生在一九八○年,因为在一九九三年一月他十二岁的时候,他遭遇了战争。而对我来说,一九九三不遥远,战争却极其遥远,我几乎不能相信在九三年竟有人正在饱受战火离乱之苦,开始在一夜之间失去童年、亲人、舞蹈和说唱音乐。这样说你可能会认为我无知且矫情,因为战争从盘古和上帝以来,从仓颉与荷马以来,从未中断过,即便现在,依然有子弹在出膛,依然有人倒下,依然有人流离失所;但是,我仍旧觉得遥远至不可信,因为我的一九九三,我们的一九九三,平安、祥和,百无禁忌,至少在我念书的小县城里,时光如静止了一般。伊斯梅尔比我小两岁,他的童年基本上也是我的童年,他的说唱音乐在我们那里,是荷东音乐和迪斯科和太空霹雳舞。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他离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新的战争又开始,那时候,我正在念大学二年级。我的世界依然平静,生活在生活之中,第二天由我自己选择。正是因为天壤之别的生活现场,让我对炮火连天的伊斯梅尔世界充满陌生和怀疑。
当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绝对真实。有历史为证。有该书封面上那触目惊心的穿橘红色T恤、黑短裤和坏了一只、后跟磨穿的夹角拖鞋的黑皮肤男孩为证。他斜挎带刺刀的枪,我不能像伊斯梅尔一样娴熟地叫出它的型号,肩膀上扛着一枚火箭弹,他低着头走路,表情平静,视枪弹和动荡的世界为日常。还有伊斯梅尔的回忆文字为证,他把战争从头讲起,第一声枪响到逃亡和血流成河,到被迫成为童子军、甘毒品如饴、杀人不眨眼,到获救、挣脱噩梦和深重反思;只有从战火中血淋淋爬出来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简洁、质朴,句句静默却让你动容。
非洲多年动荡,已是常识。我还是忍不住去看世界地图,寻找半天才在大西洋边上看到指甲大的塞拉利昂,被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抱在怀里。伊斯梅尔生在这里,他的所有至亲死在这里。地图上标示的是宁静的淡黄色。但是一九九三年,伊斯梅尔看见硝烟从淡黄色中冒出来。
这很可怕,尤其对一群孩子。它把死亡和扭曲硬生生地强加到了伊斯梅尔们的身上。在此之前,伊斯梅尔们正过着他们应该过的童年生活,念书,踢足球,听故事,狂热地学习说唱音乐。然后,“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人们四散奔逃”。“漫漫长路”开始了。
自传里写了幸福生活丧失的全过程,流离失所、忍受孤独恐惧和死亡的威胁,见识一个个生命在瞬间被剥夺。这是所有战争和贫困生活回忆的常规主题,伊斯梅尔没有规避,但他选择的路径与众不同。他只说“我”,只说亲身经历。不渲染,不高谈阔论,甚至不关心修辞,躬逢战乱者深知战争的奢侈,更懂得节俭才是真正的美德,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干货。和伊斯梅尔一起逃亡的伙伴赛义杜说:“每次有人要来杀我们,我都闭上眼睛等死。虽然我还活着,但觉着每次接受死亡,我就会死去一部分。不久我就会彻底死亡,只剩下躯体空壳与你们同行。它比我还要沉默。”在书中,伊斯梅尔更多使用的也是这种“沉默”,所以他只用了十万字多一点。但是我们已经清晰地看见家园是如何一点点离开苦难的塞拉利昂平民,看见战争是如何残酷地劫掠生命、信任和良知。每一个细节都如平地惊雷。
与其他更多的战争回忆录区别的是,《长路漫漫》深入地呈现了童子军的状态,至少在我,从未读过如此精彩的天使和魔鬼之间的辩证法。而这个精彩,源于刻骨冰冷的真实。回忆录中的塞拉利昂,随着战争的深入,不管正义与否,双方的人性深处的恶都在超常规地膨胀,连一群十来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热衷童谣、故事和玩具的年龄,还是一群孩子啊,天使就摇身成为魔鬼,想来着实令人发指。
但这也是《长路漫漫》的主要价值所在。伊斯梅尔在控诉战争的同时,没有放弃对自身的审视和反思。
他细致地记录了他和一群伙伴如何一步步成为嗜血成性的杀戮者。报仇、自保以及一厢情愿地将自己当成平民保护神的虚拟的正义感,成为他们把天然纯真强行扭转为残暴、冷酷的借口。开始是被迫,接着是自觉,伊斯梅尔们逐渐排斥乃至忘掉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迅速地把自己催熟。“枪是我的供养者和保护人,我的准则是,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我的思想深度到此为止。战斗进行了两年多,杀人成了家常便饭。我对谁都没有同情。童年在不知不觉中离我而去,我的心似乎已经结成冰。看到日月交替,我知道何时是白天,何时是黑夜。但至于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五,我浑然不知”。他们在被催熟的同时变得简单、狭隘,离“人”越来越远。为了取乐可以变着法子肆意杀人,需要吸食大麻和火药粉来提神。像成年人中的“恶人”一样活着,物化为战争机器。他们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孩子。伊斯梅尔对很多个交火和杀戮场面进行了逼真的回忆,读起来阴风怒号,寒气飕飕。
——正因为此,我也愿意把它看成一部温暖的书、劝慰的书。如上所说,因为伊斯梅尔一直没有放弃对自身的反思。他一直在警惕,即便在看着滴血的刺刀微笑的时候也没有彻底放弃。他的噩梦和偏头痛时时在提醒他。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往人性深处的大地方阐发,但我宁愿降几个调,只从人性最基本的本能来看:珍视生命和向往安宁与美好并非什么深刻的大道理,而是人最初的也是最终的需要。伊斯梅尔在被战争异化的过程里依然残存了这个向往,所以,他可以最终成功地得到救赎和解脱,并从事目前的与儿童权益相关的工作。
大约也因为此,我在阅读这本书时要不停地回顾伊斯梅尔和我自己,我们都有自己的警惕和怀疑,也有自己的向往和相信。
看麦克尤恩的《赎罪》
出差,早上回京。下午看完《赎罪》。好。到了第一部的第八章时,我的胃口才被吊起来。之前觉得细腻的铺排漫无目的,一身的痒痒肉漫漶又挠不到重点,现在效果出来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分析颇有莫里亚克之风。在很多我以为无话可说之处,往往又能生发出不少精妙的情节和精辟的见解。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大段大段的闲笔,随着情节和进展,意义便会弥散和发挥出来,麦克尤恩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实在沉得住气。在阅读之初,大概受制于他的《阿姆斯特丹》和早期的《水泥花园》两部长篇的简洁精炼之印象,对突然丰满乃至冗赘的文风有点别扭,看进去了才发现其中的妙处。在现实主义的基本功上,麦克尤恩极为扎实,对历史情境的还原能力让我惊叹。显然小说在准备时下了相当大的笨功夫,这从返回历史场景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具体的时间、地名、历史事件的相关信息,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经得起推敲的。有文史学家的敬业。小说的结构也比较巧妙,四个时间段,叙述视角也各不相同,故事、细节和思考始终聚焦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即布里奥妮诬陷罗比,在整个宏大的人类史中微小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麦克尤恩把它阐发成为三个主人公,布里奥妮、罗比和塞西莉娅一生都不能释怀和回避的大问题,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最具力量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开始了三个人各自人生的新起点,而且是唯一个起点。对于宏大的世界而言,它微不足道,但对一个人来说,它是全部,是经过、意义和结果,是逃不掉的宿命和承担。这里有一个“大”和“小”的奇妙的辩证法。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理由是:个人日常经验和宏大叙事的对接。麦克尤恩在处理“大”和“小”时,游刃有余地把个体的命运嵌入了二战前后的战争背景里。把个人命运和历史连接起来相互考察,已经成为现代小说中宏大叙事一路的惯常招数。也许尽人皆知,但真正能够将“大”和“小”水乳交融地处理好的,其实并不多。这其中“大”要足够“小”,“小”也得能足够“大”,境界、视野、细节储备以及相互转化的技术难度,少有作家能够完美地实现。你不能让“大”架空了“小”,也不能让“小”泛滥至于拖了“大”的后腿,降低了“大”的高度。在“大”的背景下,“小”既能自足,又须具备可供升华至“大”的品质。麦克尤恩解决得挺好,对战争反思的深度和力度虽难称对过去的探讨有多大的超越,但也足以意味深长。他对战争细节的想象细腻精到。
小说共四个时段。麦克尤恩分阶段地关注一颗“偶然”的种子如何播种、发芽、成长和结出果子。相隔的两个阶段之间的空白时期用乔伊斯和莫里亚克的方式勾连和回旋,你能看到那颗“偶然”的种子如何持续不断地汲到水分和营养,没有情节和文气上的断裂,它的成长一脉相承。
赎罪不该单单要布里奥妮来承担,麦克尤恩显然意识到了,他有意无意将罪责分派给了马歇尔、罗拉、杰克和艾米莉,正如小说中所说,没有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麦克尤恩还是没有将“赎罪”意识很好地波及到每一个人物身上,尤其是在黑夜中实施强暴的马歇尔,他的“赎罪”只是简单地交代他最终娶了施暴对象罗拉并在余生里大行慈善,而这些善行在小说中看起来更像是富人的做秀,缺少真诚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若是通过某种方式展示马歇尔等在面对最大的“罪”的躲闪、挣扎和煎熬,小说应该会更好看。没有哪一个人是无罪的。原罪。那么,如何将原罪意识贯穿到整个小说世界,让谁来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赎罪”,对麦克尤恩来说,大约是他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了。
小说家可以是上帝
在通常的印象里,好小说对作家来说是非法的,它要跳出你的预设,要溢出,因为人物和故事有自己的逻辑。就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结尾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安娜肯定比老托动笔之前的那个安娜要动人,要自然和符合人性,她水到渠成地成为了自己。鉴于此,很多批评家和老作家都语重心长地告诫新作者:别想得太清楚,主观意志不能太强大,要贴着人物写。
说得非常对。但是马尔克斯不这么干,他要准确,乃至精确,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他手执罗盘,精确地操控着小说的航向。他自己说:“……我所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地达到了。”这话要不是出自大师之口,肯定会招致一片骂声。文学不是科学,卷尺、量杯和数字对它是无效的。但是马尔克斯坚持用此类工具写出了《凶杀案》,你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小说,而且是最牛的小说。马尔克斯在这个小说里证明了,作家可以是上帝。
掌控力之强首先在结构。这个小说里充满了环形,大环套着小环。从整个小说来看,是大环。开头就写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死。他在被杀死的早上五点半起床,然后出门,最后从外面回来时,在家门口被杀死。显然是一个封闭的环形结构。而小说的细部,依然采用环形的小结构,从某一处开始讲,且走且退,倒叙中又有前进,绕了一圈情节又回到出发点。如此一个个环形往下推,最后成就了一个大的环形。对作家来说,故事往往并不难讲,难的是处理好讲故事的结构。一个匠心独运的环形结构已经是不容易了,马尔克斯还整出了比奥运五环还多的环,实在是让人惊叹。
此外是巧合的运用。巧合在现代小说里其实已经是个忌讳了,它往往意味着匠气和作家的偷懒,好的小说要依赖情节和逻辑的必然性展开,而不是命悬一线在巧合上。马尔克斯不管,拼命地在小说里使用巧合。他就是要证明巧合是如何导致一桩大家事先都知道的凶杀的发生,证明巧合在这里就是不可避免,如同宿命和规律。他做到了,依仗对每一个巧合的掌控,以及对通篇无数的巧合的精确谋划。
此小说说明,小说的可能性之一也会源于精确。只要你足够精确,力量足够大,上帝将与我们同在。
在战争和史诗面前转一个身
花两天时间看《灰色的灵魂》,值。
不记得之前是否看过克洛岱尔的小说,印象里他好像是年轻一代小说家中,新小说的代表,1962年生。从这本小说来看,这个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路子。当然也不是完全和新小说没关系,相反在结构上还是玩了一点花哨。新小说的幽灵一定在其中出现。这可能就是我在阅读中,看了后面忘了前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我这两天头脑不好使,老记不住东西,一想前面的情节就像在做梦,飘着把握不定的迷雾。但基本可以断定的是,这小说绝非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会是新小说的样板。故事其实不复杂,但就是绕,简单得让你觉得绕。其中必有诡异的幽灵出没。
《灰色的灵魂》中写二战,但又避开了正面的战争。克洛岱尔不打算“正面强攻”硝烟、子弹和血肉模糊的场面,而是拐回头扎进人群里。对他来说,人的身体、信仰、情感、灵魂才是前线,而真正的战场是小说的后方。所以小说中不时出现的隆隆炮声只是背景和画外音,拉开幕布,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
克洛岱尔没经历过战争,是否因为他缺少此类经验,才讨巧地绕开战场?如此猜测多少有点小人之心。可能有这个原因。要是我我就坦然承认。但我想说不是这个,不是指责他讨了巧,恰恰是想羡慕和夸赞一下:他找到了一条上好的道路,而这也是小说家真正该干的事。
描写战争从来就不应该成为作家的任务,他们的对象是人,或者说,是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对这个关系中已存的揭示、未知的勘探、可能的生发。切口可以不大,但进入之后必要幽深、辽远,把微妙处摊开,将激烈处呈现。
克洛岱尔的目的大约也在这里。他精致、纯粹和幽深,但不是特别粗粝和开阔,如果说史诗必须是庞大、粗犷、浩浩荡荡的寓言和神话,那么可以说,他在史诗面前也转了个身。
她让尘埃都落定
在看到戈鲁的文字之前,我已经看了很久她的画。十幅,在我的新书《天上人间》中,作为插图,这十幅画给我的小说增色不少。看到这些画时,我问臧长风兄是谁画的?他只说,一个画家,叫戈鲁。男女都没说,我也没继续问。
欣赏画没必要提前知道画家的性别,我可以从画里看人。那些画稚拙、朴实,有种宁和简单的美,适合安静的时候慢慢看,但画家戈鲁却上了浓墨重彩,颜色泼辣,所以稚拙的人物大红大绿,一点都不忌讳。照理说线条和色彩有些犯冲,但在戈鲁的画里天然地调和,像北方乡村走过来的姑娘,穿花红柳绿的大棉袄让你有说不出的可爱和舒服,而且一点不显土。姑娘们娴静、单纯又活泼,又有点传说中的印象派。我就想,戈鲁是个天真年轻的女孩子,热爱生活,底子是沉静的。
看完了戈鲁的散文集《快乐老家》,我发现我猜对了一大半,这的确是个女画家,比我们都热爱生活,在沉静的生活底色上暗暗地涌动着让我羡慕不已的激情,对文学,对艺术,对时光和爱,“一头扎进艺术家的泥坑再也不想出来”,“像猪在泥潭中打滚”,“其乐无穷”,“常人无法理解”。引号中的文字出自书的前勒口的作者简介,我想这是戈鲁的自我解嘲。只这段文字足可以看见这个女画家有着一股怎样的劲儿。
剩下的一小半我猜错了。从前勒口简介上方的照片看,戈鲁正在画画,她没我想象的那么年轻。这就对了,读完这本集子,我确信正在创作的女画家不可能如我想象的那般年轻——有多少人能在年纪轻轻时写下如此质朴沉静的文字?这一篇篇长短不一的散文如同一片片悠远的旧时光。且不说她修辞的技巧,单就那面对回忆和世界时的目光和心境,即非不惑之下所能够修炼出来的。从容淡定嵌在文字的骨头里,写下第一行就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者,她慢悠悠地向我们讲述“那过去的故事”,疯妈,地主,瞎了眼的杨爷爷,老师,妹妹,亲妈和后妈,父亲,讲科尔沁草原和红光向阳院,讲“吃人”的厕所和蒙古包——作为写作者的戈鲁是素朴的、节制的,哀而不伤,欢欣但绝不亢奋。她的矜持与平和不是熟知艺术套路者打扮出来的,而是清水出芙蓉。
因为她忠直地说出了自己的回忆,因为修辞立其诚,所以胆敢素面朝天。而这素面朝天的本色,乃是为人和为文的大境界。
戈鲁回忆的速度几乎等同于时光的速度,如同她讲述的故事里一切尘埃都已落定,她的讲述本身也尘埃落定。所有的矫饰皆已排除,干净、纯粹地现出旧人和旧事物,她决意带我们回到被“今天”过滤之后的历史现场——琐碎的、一个人的“快乐老家”。
如此,我也明白了作为画家的戈鲁为什么能画出我小说中的那些贴合人物内心的画了,因为文如其人,因为画如其人。
责任编辑/鲁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