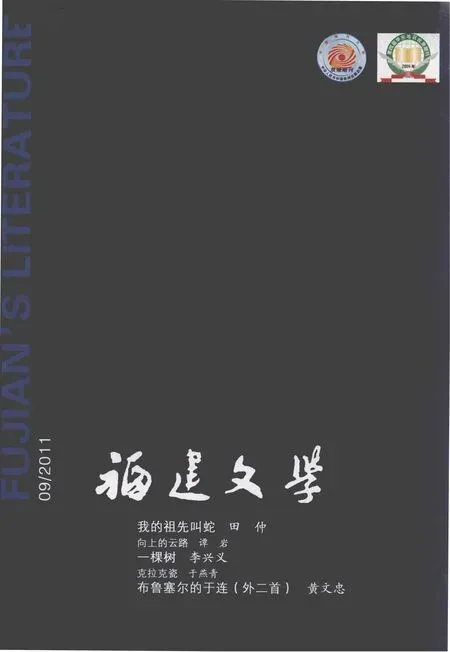闻小泾微型小说二题
闻小泾
闻小泾微型小说二题
闻小泾
时 光
2025年3月19日。上午,阳光依旧明媚。
他蹒跚着迟重的步履,来到门前的草坪上,找了块石凳坐了下来。微微的沁凉从屁股下面向身上蔓延,这种蔓延在气温已经升高的天气里,倒是给人以灵性的感觉。
他从前曾关注过的一棵草,此刻伏在脚底下,卑微地贴紧地面,仿佛害怕被剥离而去;倒是不怕被践踏,也许被践踏都是生物的命运。好在石凳的遮蔽,给了它生长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它失去了许多被阳光照拂的机会。
退了休以后,他的时间多了起来。每天除了上上网,有时电话里和朋友聊聊天,便是到这草地来走走,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活动活动机体。他的身体已经不够好了,血压经常动不动就往上爬,心脏有时也会隐隐作痛,医生说,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散散步就好。他很听话,医生的话不能不听啊!上午九点多吃完早饭,等大家上班后,独自儿到这草地走走,已经是他的必修课了。
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所有的辉煌或不辉煌就这样过去了,所有的动情或不动情就这样过去了,仿佛一切都是注定。也许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命运给他选择了这一条道路,给他选择了这一个城市,给他选择了这一个小区,给他选择了这一片草地,给他选择了这一棵小草,他无可奈何。
假如他当初不是听从了语文老师的话,而坚定地去考文科而不是理科,那么他的命运会怎样呢?假如当初他不是服从组织的安排下去乡镇任职,而坚定地去考研究生,那么他的命运又会怎样呢?假如当初他被派到省里挂职,能够通过关系留下来,那么他的命运又会怎样呢?假如他能改变万事不求人的个性,躬下身来,多到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那里走走,甚至舍得花点银子,那么他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轻轻的一声招呼从旁边传来,如果不细听,还感觉不出有人向他打招呼,他转过头去,看见旁边的石凳上也坐着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有点怕寒似的手在颤抖,花白的头发中依稀的有几丛黑发表示生命活力的存在。“这不是温敬明吗?他什么时候回来了!”惊讶中,他忙挪过步子,挨到另一张石凳上,握着温敬明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知道,这十几年来,自己过得不容易,温敬明过得更不容易,在那暗无天日的封闭的世界里,除了劳动,过上十几年是容易的事吗!尽管是所谓的罪有应得,这样的惩罚对温敬明也是太重了。
他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一切的问候皆显得做作。温敬明的手还是很冰凉,眼睛看着他,嘴唇翕动着,也一样的没有说出话来。但那一双溷浊的甚至有点呆滞的眼睛,仍像针一样的刺痛他的心灵。
他与温敬明几乎是同一天进的市委办公室,他被分在综合科,温敬明分在秘书科。他跟了市委书记一段时间后,因为有人插了一脚,又被调整到市委机关刊物去主持工作。而温敬明就在秘书科呆了下来,而且越呆越如鱼得水。温敬明没有什么像样的出身,他的家在一个小岛的小渔村,本身也没什么像样的学历,最高的学历是电大大专毕业,也许温敬明的最大资本是有着当过乡镇通讯员的经历。因此在秘书科里,他会懂得给领导送文件,不是叫文件管理员把文件放到领导的办公桌上一走了之,而是自己拿着文件等在领导办公室的门外,等领导的客人走净后,才到领导的办公室里,低着眉向领导请示这些文件应该怎么处理特别是那些急件;随领导下乡,晚上其他人都各忙各的事去了,有时秘书也被支配去自由活动了,他仍然是形影不离领导左右,领导喜欢打乒乓球,他就担任起捡球的角色,活动完了下面的同志叫吃点心,一杯一杯的向领导敬酒,领导总是不胜酒力啊,这时他就站出来一杯一杯地替领导分忧,尽管自己的酒量也有限;上面来了重要领导,安排接待方案是件最头疼的事,温敬明会一个接待点一个接待点地进行事先踏勘,有些地方路不好的赶紧叫人整修,几点几分在哪里迎接,迎接时几套班子领导怎么站位,准备好什么样的鲜花,由哪位漂亮的小姐送上鲜花,然后几套班子要不要一起鼓掌,午餐晚餐安排什么样的菜,上什么样的酒,主桌和副桌都由谁陪同,陪同时都由谁上来敬酒,领导房间放什么花篮,上什么水果,晚上怎么活动,活动后在哪里安排点心,都一一标明。所以领导觉得温敬明特别会来事,对他的信任也就日益增厚,除了公事,个人的私事也交给他去办。经常下乡回来,如遇温敬明不在,领导就交代秘书,“挂个电话,晚上叫温敬明到我宿舍来一下。”
温敬明仕途上也就由此一帆风顺,由秘书科副科长而科长而办公室副主任而副秘书长,然后到一个沿海县任县长,正当他志得意满满面春风的时候,想不到对他倍加赏识已升任省委常委的领导因为经济问题而倒台,案件牵连到温敬明,先是被双规,继而被批捕,据说查到的金额就有上百万元,其中向这位领导行贿30万元,因此被判了十七年的徒刑。
十几年不见,自己仍然是平平淡淡,而温敬明则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再从地狱到人间的过程,所谓的大喜大悲,不过如此吧!而类似这种经历的,在这个市在这个以机关干部为主的小区,又不仅止一人。其他回来的,他没有见到,所以他看见温敬明时,就有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
“很惭愧,浑身都是病啊!”温敬明终于开了口,声音低低的,“你看来还没什么变化啊!”“哪里,我身体也不行了,我不过乐观罢了。”“哦,乐观,你看我还乐观得起来吗?”“把过去的一切忘记吧,就当是一场噩梦。”温敬明点点头,脸上尴尬地笑了一笑,原来饱满的脸庞如今已布满纵横交错的皱纹,因为这一笑,使他的脸看去更像一只苦瓜了。
“回去吃药吧。”温敬明的妻子走了过来,附在他的耳朵边小声地说,同时看见他们坐在一起,向他点了点头表示招呼。温敬明的妻子这些年来也十分不容易,家里的两个病弱老人和一个女儿就靠她侍候着,每次迢迢几百里到狱里去看温敬明,只能隔着玻璃窗和他说话,探狱回来,妻子都要大病一场,人也年年显得憔悴,如今看去跟村妇也没什么区别了。
看着他们俩搀扶着慢慢走远,他仰头向后呼出了一口气。这时候,真想掏出一支烟自顾自地吸起来,他的手在衣袋里摸了摸,才想起来自己已戒烟多年了。他闭上眼睛,眯成一条缝,从睫毛处望出去,看见白云在蓝天中显得十分破碎,凌乱地飘浮着,小鸟的调情声从不远的小树上传来。有些风,细细的,如果没有细心感觉,还觉察不到。
想起来好笑,过去他看见一两个老人在这里蹒跚着散步的时候,他心里对他们是充满了怜惜,想想他们有的从解放初期就开始当县长的历史,真的应该叹服光荣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但就是这一代人的筚路褴缕,有多少被后人理解,有的人还以谩骂和糟蹋他们为能事,在这些人看来,天堂是不需要基础的,在空中就可以搭成。当下一辈人以谩骂死无还口之力的上辈人为能耐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道德还不会沦丧吗?
可是,这些老人活着的时候,也不为自己以及自己为之奋斗过的历史争辩,因为他们知道历史不是某些人爱怎么写就可以写得成,特别在资讯十分发达的今天。如此的作为是让某些人成为历史的笑柄,如此而已。
当这些老人一个个在时光里消失,草坪上只留下空空的石凳在晨曦和晚霞中由气流恣意轻拂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也踱进了这一片草坪,在这散淡的阳光中,将开始他最后的沉思。
忽然,一个短信声响起:“小泾君,你在家吗?我在你省城开研讨会,下午过来看你。——羽洁。”哦,哪个羽洁?是那个在网上交流十几年,至今仍未见过面的羽洁吗?当初认识她时她还在上海某大学念研究生,如今听说她已成为国内著名的专家,像当年于丹一样有名了。她真的来看我吗?他心里充满了期待。
远远看去,草坪的石凳上似乎凝立着一座雕像。
叔 公
妈妈躺在门口的一块泥土上,在歇斯底里地大哭,周围围满了人,人们越劝,她哭得越厉害:“你们放了我,让我去死吧……呜…….呜……呜……”四面是漆黑的夜,寒气有点袭人,而门内仍有一个声音在叫,如霹雳一般:“让她去死,你们不要劝她,装什么样子……”这是叔公的声音。那时家里的厢房刚刚落成,客人还在吃酒,不知因为什么,叔公就没来由地把妈妈骂上了,于是就有了上面的一幕。
那时,我才四五岁吧,伏到妈妈的身上,和她一起哭,越哭越伤心。
爸爸则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叔公是老虎,爸爸是猫,看见老虎脚都会发抖,于是叔公的威风就抖得更厉害了。
当然不光对我妈妈,除了对曾祖母,叔公对其他人都是动不动就咆哮的。甚至拿着刀子追杀人,只要想爱惜身体,爱惜性命的,谁不害怕?
这天晚上,我睡在隔壁房间,到了下半夜,忽然被一阵咆哮声吵醒,听到的是这样的对话:“你管我那么多干什么!你这个臭婊子,你还敢来管我!”“我臭婊,你什么时候看见了……”叔婆压低着声音,“我没看见,你以为我没看见你胆子就大了?你这个臭婊子,还敢来管我!”接着,就是动手的声音,摔东西的声音。曾祖母赶紧爬起来,走过去,敲着门,叫着叔公的乳名,“你还不放开手,像什么话。都这么下半夜了,还吵什么!”听到了曾祖母的声音,两个人便放开了手,叔婆仍在呜呜地哭,好久了才归于平静。
第二天,看见叔婆的脸色,仍是没事的样子,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可是,过几个晚上,同样的事情就来一回。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叔公贪赌,常常是下半夜归来,甚或整夜的不归,于是争吵就常常发生。
叔公的赌艺是有名的,常常凯旋而归。赢了钱,总是自己跑到肉铺去,砍几斤肉回来,然后拎一点酒,炒几盘菜,自己慢慢地消遣,当然他家里人也跟着他享福了。别人的孩子要上山砍柴,他家就只要到街上叫几捆柴挑到家里就好了。
村里人说,要是叔公不恋赌,说不定还可以当上大官呢。那是解放初期,叔公和一个同伴背着褡裢上了省城,他们去找一个地下革命时在我家隐蔽过,叫曾祖母为革命老妈妈,现已成为兵团司令的大人物。大人物听说他们来自革命老根据地,某某村某某家的,即对他们非常客气,写了个条子叫他们回来找当地政府,他就这样参加了工作。当时百废待兴,人才缺乏,叔公也念过几年书,因此机会多得是。但叔公因为恋赌,也许还因为恋家,出去工作了没几年就跑回家来了。那时刚好村里设了一个茶叶站,叔公就在茶叶站工作了,其实也就在家里领工资了。
文化大革命风风火火的时候,叔公也没受到什么冲击,因为他不是走资派,虽然某些造反派的标语贴到了家门前的岩石上:“打倒某某(兵团司令)!”跟叔公似乎也没太大的关系。他仍然昼伏夜出,像当年曾祖父和祖父闹革命一般。然后回家还是吵,尤其是大年三十,总要来一场大吵特吵,然后安安静静地过年。
局里调了他几次,把他安排到另一个公社茶叶站去,他就是不去上班,只赖在家里,人家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资格老,又是烈士家庭的,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最令叔公伤心的,恐怕是其女儿的得病了。叔公只有一个女儿,平常爱惜得如掌上明珠。这天,他女儿高兴,背着一个柴篓上山去扒柴火,扒到一户人家的梧桐树下,只见树叶纷纷地落满地,他女儿兴奋得一个劲地往里扒,不想那户男人已经走到边上,大喊一声:“你干什么!把我的梧桐叶给扒走了!”并把她的篮子抓过去往烂里踩。他女儿给吓了一下当场就傻了,回家后当天晚上就发病,开始疯疯癫癫的,可怜叔公平常都是恐吓别人的,而当自己的女儿被别人吓疯时,却束手无策了。
于是,叔公更一心一意留在家里照顾女儿了。女儿送了几次精神病院,似乎不大见好转,又带转回家里,反反复复的几个来回,也把叔公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过了几年,我毕业回来时,家里也在城里盖了房子。叔公偶尔到城里来,也住到家里。母亲在人前待他还是不错的,炒几盘菜,给他上一点老酒,他也吃得津津有味。好像过去的事从来不曾发生过一般。姐姐气不过,总要在背后数落母亲:“你现在还管他那么多干什么?你不记得当年他是怎样欺负你的。”母亲说:“算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毕竟还是家里人嘛。”但叔公可能也感觉到了母亲热情中的那一份保留,以后到家里来的次数也少了。
叔公在村里也算是豪放派的人物之一了。他骂人总是骂:“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台湾派来的特务。”谁沾上这个骂,便十分的惶惶然,似乎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真的成了“特务”了,于是人们对他便敬而远之,看见他最多点点头就走了。
叔公的最后结局是谁也想不到的。据说那天,因为村电网改造,叔公家里线路没有搞清楚,叔公赶到祠堂和住在那里的工程队理论,工程队的人认为他老头子一个凶什么,便把他推了一把,叔公一下子站不住,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还想爬起来却爬不起来,待家里人赶来时,人已有点昏迷过去了。于是赶紧雇车送医院。
在医院时,我还去看过他,精神状态挺好的。家里人也以为没事,便拿了几千块钱和工程队达成私了。想不到,过了几个星期,病情急转直下,一个活生生的人说没也就没了。
如果不是碰到意外,叔公活到八九十岁该是没问题的,我想。
闻小泾,福建福安人,福建省作协会员。1980年代以来,有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发表于有关报刊,曾获《福建日报》多项征文奖,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三等奖等。有诗歌作品入选《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诗歌卷)》等各类选本。现为政府部门公务员。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