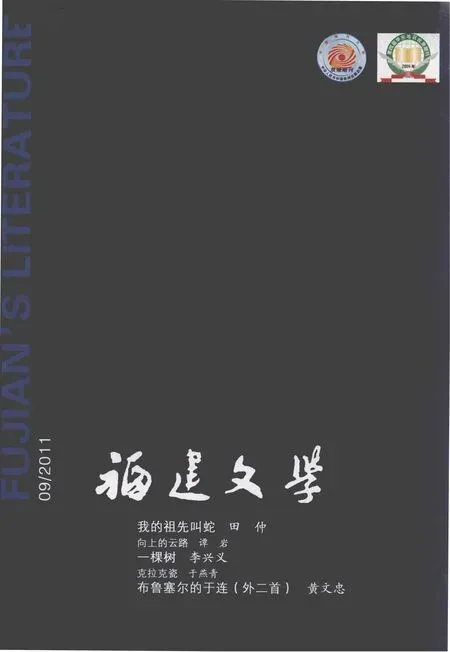爷 爷(外一篇)
陆永建
爷爷1904年出生,属龙,“属”得其所,一辈子云游四方。他生于杭州,八岁迁居上海,十四岁到南京学医。1941年上海沦陷后,先后逃难到重庆、四川、浙江等地,最后定居福建。
我从小就在爷爷家生活。那时,爷爷月薪五十多块钱,奶奶是家庭主妇,除了每月给在上海的太祖母寄10块钱生活费外,每天早饭后,爷爷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钱给奶奶,作为我们仨一天的伙食费。那时物质匮乏,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如每人每月猪肉半斤、面粉一斤、油三两、米二十三斤。除了空气、水和青菜以外,其他都要按计划供应。当时颇为时髦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四大件”,我们家已经有了两大件,至于自行车和缝纫机,我们家基本用不着。在我读幼儿园和小学期间,还没有“零花钱”这个概念,除了过年爷爷和父亲各给一块的压岁钱外,就是平时卖一些废品的收入,全年合计也不过六七块钱,但足够一年买小人书、学习用品和一些零食的开销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爷爷常教导我:“好木头,既能做棺材,也能劈了当柴烧。”我听不懂,爷爷接着又解释说:“既要学会做皇帝,还要学会做乞丐。”我由此知道,男子汉要经受得起大起大落和大风大浪的考验。
爷爷对我要求很严,学龄前,他就在墙壁上挂着一大一小两块黑板,他每天早上在小黑板上写五个字,教我识字,接着就要我每个字在大黑板上用粉笔抄十遍,晚饭前考试——爷爷读我默写,如果有一个字写不出来就要挨骂被打,直到考试合格,才能吃饭。如此几年下来,我在上小学一年级前,就已经认识五百多个汉字了。在读一年级的时候,爷爷让我用钢笔抄信,有一次,让我抄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才抄到第三行,就被站在身后的爷爷发现抄错了一个字,按照爷爷的提示,我立刻涂改更正,结果还是少不了被打,爷爷身材魁梧力气大,打起来痛得直钻心底,我一边哭泣一边重抄,很是痛苦。从二年级开始,爷爷就要求我没话找话给他的亲戚写信了,每次写信都少不了或多或少地被打骂,写信成了我一个沉重的包袱。此外,还要我临摹柳公权的《玄秘塔》,每天午饭后写一张纸。我现在还保存有小学二年级以来的书法习作,后来,书法和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每天早晨鸡一叫,爷爷就起床晨练,他总是第一个到单位上班,每次为病人治疗后,他都要用来苏尔洗手消毒,这既是一种习惯亦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待家人也很严厉。一天,我父亲在街上看大字报耽误了上班时间,迟到了半个多小时,结果遭到爷爷的拍案批评。但他对待同志却非常热情宽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同事都请爷爷帮忙要一张购买缝纫机的供应券,后来,爷爷搞到了一张票,但给谁呢,爷爷考虑到前不久身患重病,近半年时间每天都是这个同事到家里来打吊针,为了报答这份情谊,最后把票给了那个同事。平时,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病人,爷爷总是给予减免医疗费、手术费等。有一次,一个病人没钱买车票回家,爷爷知道后立即拿出10块钱给这个病人……奶奶得知后,责怪爷爷对家人抠门,对别人大方。爷爷却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1954年爷爷从浙江龙泉迁徙到福建浦城后,就一直住在后街那间古老破旧的四十多平方米的木板房里。有些衣服裤子破了,他就自己缝补一下在家里穿,有两双长筒袜子是三双改成一双的,有两件内衣是由多件旧内衣拼凑起来的。夏天由于买不到合适的汗衫,他就把破纹帐改做成汗衫穿,熟人看了跟他开玩笑说:“您这么著名的医师咋穿这个啊。”“没钱买呵”,爷爷笑哈哈地回答。冬天,闽北天气湿冷,他不用电热器取暖,坚持烧木炭取暖,一个冬天下来,一二十块钱就够了。为了节约用电,家里的灯泡一律都是15瓦的,后来又换成了8瓦的日光灯和3瓦的节能灯。为了节约用水,爷爷把洗脸用的长条毛巾换成了小方巾,我百思不解地说:“用水又不要花钱,隔壁就是水井,要用多少我去挑就是了。”爷爷却说:“要知足啊。”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悟出节约是一种习惯。
平时我的朋友到家里来访,只要在家门口叫我的名字,屋里的爷爷就知道是谁来访了,常常直呼其名,分毫不差,其耳聪目明和超强的记忆力让人惊叹不已。更为神奇并让我吃惊的是另一件事:2007年10月,我陪爸爸、妈妈去浙江龙泉走亲访友,在河村,爸爸专门到老房东家看望儿时的好友,并合影留念。第二天,我们返回到老家后把相片给爷爷看,我问他认不认识与爸爸合影的人。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我提示道,那个人就是解放前你们住在他家里的保长的儿子。“哦,是胡根生。”爷爷脱口而出,在场的人听后都目瞪口呆。
2005年2月,爷爷的脚扭伤引起股骨局部骨折,骨科医师要求他卧床治疗三四个月,并告诉我们说:“老人家想吃什么你们尽量给予满足,从临床上看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般躺个把月就没人了,何况他已经一百多岁了。”爷爷在卧床治疗的数月里,除了受伤的脚以外,仍然坚持每天锻炼,如举哑铃、按摩、气功等,结果不到四个月爷爷就奇迹般地康复了。爷爷顽强的生命力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运动。他常说“生命在于运动”,每天早晨5点起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二是食素。他告诫我们说:“病从口入”,三餐要少盐少油少辣,提倡吃新鲜菜,反对吃腊、腌、熏、炸的食品。爷爷上班到81岁才离开单位回家休息,但病人仍慕名找到家里求医,为此,他专门腾出一间为患者治病,一直工作到92岁。
2008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从福州赴老家过年,晚上八点多钟,爷爷给我父亲挂来电话,当他老人家得知我们还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浦城时,关心地说:“你们一路辛苦了,晚上早点休息,明天再来看我。”接着又跟我母亲说:“你要信耶稣啊。”这是爷爷留给我们最后的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去见他老人家时,他因脑梗阻已昏迷不醒。四天后,爷爷去了那个天国之家……
后 街
后街,在浦城城北一隅,东接五一三路中段,西连马车埂205国道,大概是因为当年南浦溪水路交通发达,取沿岸的一条街为前街,有前就有后,这条街远离溪水,因此就叫后街。近二三十年来,后街几易其名,改到现在许多人已不知它曾叫后街。
后街是浦城最古老最热闹的街巷之一,我曾在这儿住了三十多年,这一点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得到:凌晨三点多邻近的屠宰铺就开始工作,凭猪惨叫的声音大小和次数,我就知道宰了几头猪。板车拉着猪肉经过我家门口到供应点,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半斤。一会儿,雄鸡打鸣,邻居开的豆腐店石磨开始转动,将那些前一天用水浸得饱满透亮的黄豆磨成浆,然后沥浆煮浆,成卤后舀到一块木板上压成豆腐,再加工成豆干或豆皮,边做边卖。农民陆续进城沿街卖菜卖柴卖鸡卖蛋,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几个小摊贩在东方红小学门口做生意。卖烧饼的炉火烧得很旺,师傅把做好的烧饼胎整齐地放在台面上,再用一把湿湿的刷子在炉壁上迅速一刷,即在上面贴满烧饼,关上炉口两三分钟后,烧饼就做好了,刚出炉的烧饼色黄,入口脆香;还有卖油条、卖油饼、卖盒子糕的。那葱花和油炸的香味,缠绵得直钻心底,多少年来都不会忘记。
我的童年在奶奶家度过,爷爷是远近闻名的眼科医师,早年在南京中美眼科研究所工作,抗战期间逃难到浦城后一直住在后街。我们家的后门与五六户邻居的后院互通,分别住着闽浙赣等三四个省份的人,有医师、农民、工人、干部、教师等,各种方言通过灰蓝单调的服装联系在一起。除了我们家之外,他们都有一到两分的菜地,种有茄子、韭菜、豆角等,还有三四户人家养猪,其中一户是干部,养的猪较多较肥;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鸭,客人来了,就到鸡窝去摸鸡屁股。后院还有一口水井,生活很是方便。黄昏,男人打赤膊,穿拖鞋,左手端碗,右手拿筷,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或坐或站,边吃边聊;老人惬意地坐在家门口的石墩上,慢慢悠悠地摇着芭蕉扇……
隔壁是第三旅社,门口有一个古井,井壁苔痕青青,有提水的、洗菜的、洗衣服的,还有刷牙、洗脸的,把水井围得严严实实;晨雾朦胧中街边门口或立或蹲着一些人在刷牙,也有刷马桶的。卖酱油的担子走到跟前,拉着长调喊一声:“卖——酱油喽……”担子挨着马桶放下,主妇就三三两两地围拢上来。她们虽然身穿睡衣,发髻蓬松,却仍透出晚春般的缱绻,风韵依然撩人。
只要有时间,我总喜欢回后街走走。
细长的后街,两旁长满垂柳,常年一片翠绿,婀娜摇曳,绿影婆娑,映着泥墙灰瓦和木板房,古朴宁静,青石和鹅卵石路面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得油光发亮,属于戴望舒雨巷那种。放眼望去,满街多是单层木屋,两边的房屋向街心对开门面,一间紧挨一间,一座挨着一座,鳞次栉比。居民把晒衣服的竹竿横在自个儿门前,也有搭在对门屋檐下的,人们在后街行走时,头顶常常飘着衣服裤子和婴孩的尿布片。开店铺的,白天卸下门板营业,晚上嵌上,吃住都在里面,没有一间光洁通透的玻璃橱窗,原木的颜色被时光染成了酱黑色,却不失洁净整齐。
离我家一箭之遥的“水井头”(本地方言,水井周边的意思)有一座古宅,是后街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里面住有二三十户人家,它是后街的符号,斑驳的泥墙,古老的砖雕,长满青苔的瓦背,雕栏画栋的建筑。这份古老和宁静,只有走近它,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邻里的老人们聚在“大门头”(本地方言,门口的意思)抽烟、吃茶、打牌,谈笑风生;几个男人坐在街边的竹椅上下象棋,有时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过着自个儿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悠闲生活。
我家对面的东方红小学曾是我童年的乐园。操场旁边有一口池塘,里面少不了鱼、虾和螺,我们追逐嬉闹罢了,总忘不了到那儿,或在水面上飞瓦片,或塘沿摸螺丝。有时也会遇到个把高一两年级的毛毛头,俨然头目,吆五喝六,指挥着一帮年龄更小的光屁股。教室后面有一片三五亩的菜地,地里种满了蔬菜、辣椒和葱蒜;每逢夏季,藤条附在泥墙灰瓦上不停地延伸爬满了围墙,上面长满了凉粉籽,我常用竹竿把熟透了的凉粉籽打下来去换凉粉吃。
从教室到礼堂到办公室到厕所,连接路面的都是青石板和鹅卵石。一场小雨就浇绿了路面,湿润细腻、古典丰富,嫩草和青苔一夜间挤出石缝,爬上石阶,露珠晶莹,绿意充满了石间的缝隙。低洼处流着雨水,清清的浅浅的,一脚踩下,那水仿佛从石头中溢出。盛夏,校园也毫无暑意,四通八达的石头路让你沁凉无比,清幽的苔藓、灵秀的绿草和数十棵百年老树编织了一片阴凉,即使漏下几缕阳光,热能也已减半,还添几许斑斓、几分趣味。有时可见蟋蟀突然从围墙的石缝里弹出,飞得不远;知了在树上不停地浅唱,停了,另一只接着又唱;偶尔池塘里还会传出几声悠扬的蛙鸣……
哎,后街。
那是我儿时充满梦想和快乐的老街,黏糊糊的麦芽糖,五光十色的玻璃珠,竹节做的弹弓,木制的红缨枪;和小朋友从吴家穿陈家,围着猪圈捉迷藏;少男少女边跳牛皮筋边唱儿歌。那首伴随我童年的儿歌《月光光》至今还记忆犹新:“月光光,照四方。四方圆,卖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