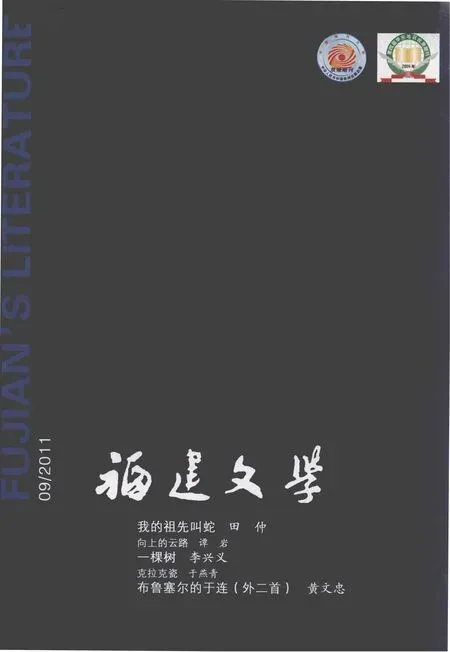向上的云路
谭 岩
这是一座荒凉的大山,位于三省交界的边陲。它的山峰直插云霄,常年顶着一片云雾袅绕,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云盘岭。一条爬上云盘岭去的公路时隐时现,在一片青黛色的山间,就像一条绕去绕来的云带,司机们也因此取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云路。
可是这条在旅游者看来充满了诗意的道路,却令过往的司机提心吊胆。山高路陡,峰峭弯急,路况一塌糊涂,隔三岔五,路旁总要歪倒了一部车辆,四个轮子朝天,或者半个车头撞在了岩石上,有人捂着带血的额头坐在那里呻吟;要不就又陷在了泥滩中,尖厉的马达声如同困兽的嚎叫,响彻在这片云雾袅绕的山林。
一个名叫余大发的人,既不觉得眼前的景色是如何之美,他天天要看这种景色,已快看了五十年;也不觉得路旁的事故是如何的惨痛,他总是冷眼旁观,早已成了一副铁石心肠。当他看见一车比一车拖得多、一车比一车堆得高的拖煤车,四个轮子在泥地上打滑,他就会狠狠地想,滑,滑,滑翻了才好!
自从这深山里发现了煤矿,一条公路也就钻进了山来,先前还见有养路的,毁坏的路面时见铺上了新鲜的泥土和石渣,可时间不长,这条公路就无人管了。无人看管的公路很快就变得大坑小凹,高低不平。路没了人养护,可钱还得赚,车还得跑,大大小小的事故也就避免不了,这些事故对别人是灾难,可对他余大发就是财富。只要一下雨,一听见山间传来汽车的轰鸣,一听见那异样的马达声响,这个住在半山的汉子就像猎狗听见了野物的踪迹,就会扛上锄头铁锹,一脸兴奋地去逮“猎物”。
他远远地跟随,或者干脆就坐在山坡上等待,等那些司机折腾得差不多了,蹲在地上,望着那两个深陷在泥坑中的车轮发愣了,这位守株待兔的旁观者,就会胸有成竹地站起身,提醒似的咳一声,于是那位蹲在地上一筹莫展,一脸焦头烂额的过路客,一抬头,就会发现这位扛着锄头和铁锹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时间长了,司机们都熟悉了他,有时见他站在路旁,就车也不下,抽着烟,扯着淡话,等他拿把锄头或锹,在车前车后一阵儿挖,撮,撬,然后从车窗丢出五块十块的钱来;如果见他吆喝了一声,冲身后的某个方向伸出了两个或者三个指头,不一会儿就跑来满脸兴奋的几条汉子,这司机心里就一咯噔,知道这不是五块十块就能解决的了,抓起那半包烟跳下车舱,脸上挤了一脸儿的笑,首先递给那包工头似的家伙一支烟。
山上的种田人没有不忙的,可这个家伙却像个闲人,一年四季在这条公路上游荡,不是坐在松树下歇凉,就是蹲在坡凹里烤火,要不像个无事佬,沿着这条公路一遍儿上,一遍儿下,那一件过时的衣褂一走一搧。
又是这个人!他靠什么生活?
坐在副驾驶上的一个正和司机调笑的年轻女子,从这云路来往了好几趟,每次都见到这位无所事事的闲人,不由产生了好奇。
谁?余大狼?——这个王八蛋!
司机一探头,也看见了前方坐在那里烤火抽烟的余大发。
可是这位刚刚还在咒骂的司机,一到路旁的那堆火前,就吱的一声踩住了刹车,摇下车窗玻璃,一脸儿笑地探出头去:
余哥儿,又在这儿享福呐!
说着,还抓起车窗台上的半包香烟,丢了过去。
一阵说笑,这才又摇上玻璃窗加上油门继续赶路。见身边的女子一脸的不解,这司机说,你莫看他穿得不怎么样,他过得比我们都好——这个老杂种!
正像这位司机说的那样,这位天天在路上闲逛的余大发,在云盘岭大小也算个人物,甚至称得上威风八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靠路吃路;这条云路最难走的那一截,刚好两边都是他的责任田,是他的老虎穴。车辆陷在了那里,他叫你明天走,你就不得不在这里过个夜;他开口说一百,你就不能少一分;你说碰巧刚加了油,没钱了,行啊,那就下点儿煤!一使眼色,一帮乡民吆喝着就要往车厢上爬。那群老老少少的山里汉子,众星捧月似的追随着这位山大王,因为跟着他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零用钱,烟钱,酒钱,快快活活的好日子。
可是这快活的好日子却苦煞了那些司机们,见了这山大王掏钱不说,还得赔上笑脸说好话。余大发也知道,只要一转身,那大哥长大哥短的司机就会咒他黑良心,是老杂种,是老不死的;那些笑脸相迎的乡亲们,背后也会嗤之以鼻地叫他余光棍。在云盘岭,人们说的光棍不单是指孤家寡人,还指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坑蒙拐骗的小混混儿。他余大发,就是这云盘岭路上的二混子。
没有人维修的公路,已经不负重荷,勉为其难了,可是这个家伙,却在推波助澜,加速它的毁坏。有意无意,他在山坡的田上挖一个水沟,改变了排水的方向,让暴雨横扫公路,好好的路面又冲出一条槽;路上已是高低不平了,看看前后没有人,又拿锹在那里挖几下,要不就从坡上掀块大石头,轰隆隆滚到了路中央。
要想畅通无阻,行啊!他早准备好了,一块木板,一捆高粱秸儿,还有要刨要挖的锄头铁锹,要清理路上的石头障碍物,人也站在了路旁;过坑的有木板,防滑的有高粱秸儿,清理滑坡的有人有工具,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抢修工,什么都替人准备好了。
这云来云去的云盘岭,过几天就会下雨,就会路滑,不滑路上也有几个坑,那些泥泞,那些坑凹,就是他的聚宝盆,就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储蓄罐,就是他打工领工资的地方。他的生活除了早晨起来打几个哈欠,从一个山弯转到另一个山坡,找人聊聊天,打打牌,下下棋,买买码,骗吃骗喝地在人家那里解决一餐肚子问题,就是扛着锄头,或者提一把锹,戴顶破草帽在公路上转,像个巡山的,等候那些过往的车辆,一心盼着那些轰隆隆七弯八拐着的车辆出个什么故障。
什么?黑良心?可人走到这一步,也不能全怪他余大发呀。余大发一想起这些事儿,就觉得挺委屈。没有人的时候,这位人前看似风光满面的家伙,就像秋天打了霜的怏茄子。
直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追求、有抱负的聪明人,只是幸运之神不太关照罢了。他总是以讥怜的目光打量他的那些同伴,那些山里的老实汉子,嘲笑他们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重、枯燥、沉闷的劳动,那爬上山去的载重车一样慢腾腾的生活节奏,他的目光一再越过那些遮挡着半边世界的大山,不断冒出开创新生活的新点子,亲自实践了一系列在他看来收入来得既快人又过得轻松的创收门道儿:贩过香菇木耳,倒过木材煤炭,根据市场行情和资金周转的情况,贩买贩卖的东西大到黄牛水牛,小到小猫小狗,曾经一天赚过意想不到的利头儿,衣兜鼓鼓地过着天天红光满面酒足饭饱的好日子,也曾翻遍所有的衣兜再也找不出一文钱,在年三十的头一天,嘿嘿嘿地厚着脸皮找上人家的门,挎着借来的半袋米,提着赊来的一块肉,长叹短吁地回家去,打发那一个又一个的年,熬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
这个世界过得最快的莫过于时间,还没有等这位叫余大发的聪明人实现他的宏伟计划,做完他的发财梦,二十几年光阴就像山腰飘散的云雾,眨眼就无影无踪了。一系列聪明的创收门道不仅没有让他过上人上人的好生活,连这山里他最瞧不起的种田的,他也是过得一天比一天不如人家了。在老婆孩子的啼哭声中,那一头瘦小的过年猪也被逼债的牵走了。曾经圆满的家庭到头来四分五裂,妻离子散:老婆跟人跑了;儿子离他走了。曾经的聪明人余大发从此不叫余大发了,叫余光棍了。
光棍怎么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余大发也知道,这是光棍都会辩驳的一句话,对人家并没有什么杀伤力;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扛着铁锹朝那条路上一站,那些不多不少的钞票就会跟车辆一样一个个听话地开进他的荷包,足够他这个上无老下无小的无牵无挂的人,维持打牌买码,抽烟喝酒的小康生活了。的确,除了那些他不知道该如何检点的衣着,酒比别人喝得好,烟比别人的档次高,有一回,一位车被陷住了的司机找上门去请他帮忙,一开门,竟然发现这个单身汉桌上还摆了几个菜,像上馆子一样坐在那里吃喝得有滋有味。
在别人眼里,这日子已过得很滋润了,可是,这位人前笑哈哈的光棍汉、山大王,也常常有暗自掉泪的时候。看见别人一家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再回到自己的那两间破土房,他就像掉进了孤独凄凉的冰窟窿。这位落魄的满脸悲伤的汉子,坐在灶膛门口,一边用湿漉漉的柴禾生火做饭,一边在浓重的炊烟里咳嗽着,时而抹一把辛酸的泪水。
他回想着曾经圆满的家庭,也像别人一样团圆热闹的家庭生活,像一条撒欢的小狗儿样在他身边跑前跑后的儿子,那些小却让人感到无限温馨的生活细节。可是这一切,仿佛都随着跑下山去的车辆的哐啷声,永远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山上,也有和他一样,成了差不多是孤家寡人的人,可人家会常常接到一两个问候的电话,接到一张汇款单,一个过冬御寒包裹,人家那孤家寡人并不孤单,有在远方的子女,有亲情的牵扯。每逢见到人家说起子女的幸福模样,这位总爱吹大话,说得嘻嘻哈哈的人,就会一下变得郁郁寡欢,刚刚还说得头头是道的挺直的脊背就一下塌了下来。他也有儿子,可儿子已上十年没有音讯,再说,跟着那个已改嫁他人的妈,说不定早已把这个穷山上的爹忘干净了。
想起孩子的妈,自己的那个婆娘,他就满腔的怨恨,他恨自己,也恨别人,更恨那些司机。是的,他曾经骗过别人,可也受过别人的骗:要不是那次市场行情出现意外,要不是他收了最要好的朋友的一叠假钞,他会亏得那么惨,会从此一蹶不振吗;要不是出于好心,收留那位出了事故,从车上跳下来,车子开到路下的高粱地的那位司机,那一脸络腮胡的家伙,在家住了两天,自己的婆娘能跟人跑吗?
一想到这里,余大发就恼从中来,啪地折断了一根粗柴,赌气似的两下塞进了灶膛。也就是老婆被拐——这是余大发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是他的老婆看上的人家——之后,他就恨上了那些司机,专门在这路上给他们找茬儿。有时也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太残酷,可一看到那些出事的司机至少还有亲人关照,自己落拓到如今一无所有,一颗本要柔弱的心就又硬了起来。
不知什么原因,余大发这段时间觉得过得很不顺。也许是几块钱一盘的牌总是打不赢,也许是买的几个码一次也没有中,还有可能是这路上的车辆少了,撞在他锄头铁锹上的事故少了,衣袋翻了几遍也翻不出什么钱来了,也可能是看见王老二那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又给他寄来了一张让人羡慕的汇款单,或者是这一向的阴雨,那盘在山顶山腰成天不离的云雾,压得让人喘不过气儿,总之,今天这位在家烧火做饭的汉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烦闷。
正当他把一把松毛塞进灶膛,锅里冒出热气儿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让他兴奋的声音。他像狗一样竖起了耳朵,脸扭向了门外。在那云收雨霁的山间,那一条云树掩映的公路上,传来的的确是大卡车的响声。
于是这张刚才还沉郁着的脸一下变得兴奋起来,就像猎人听见了狗叫,猎狗嗅见了猎物的踪迹一样,又精神抖擞了。就像猎人总会在猎物出现的地方下套一样,这家伙也为过往的车辆下了几个套儿——当然那些套儿不至于出现什么人命,日子虽然过得窝囊,可毕竟才到五十岁,还想好肉好酒地活几年——又刚下过雨,那些车不中这个套儿就会中那个套儿。烟盒也瘪了,酒瓶也空了,谢天谢地,财神就又送上门来了。
要不了一会儿,这位心头暗喜的汉子,摆出一副准备给人“帮忙”的架势,准时出现在他已设好的套口儿了。他坐在那棵他常坐的松树下,那块责任田的山坡上,屁股下横着一柄铁锹,悠闲地吸着烟,偏着脑袋望着坡下的那段公路,做好了守株待兔的一切准备。
随着轰轰的声响,那辆大卡车如期出现了,它从那个拐弯处,那开满杜鹃花的山崖绕了出来。凭余大发对车辆熟悉的经验,那是一辆崭新的东风牌,那个司机要不对山路不熟悉,要不就是才上路的小学徒,因为那车开得比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还要小心慢腾。
果然,看见两块田间的路上有一个大坑,那驾驶舱跳下一个小伙子来——这样的小家伙更容易对付;可接下来让余大发有些不解的是,这个年轻的司机,竟像非常熟悉这山里的情况似的,换成了别人都会束手无策,可这年轻人站在那里左右望了望,竟像驾轻就熟地一时跑到山后抱石块,一时跑到山下被树林遮住的田间抱秸秆儿。眼看自己设下的套儿要泡汤了,这坐在树下准备收钱的余大发坐不住了。哼!那秸秆儿也不是说抱就抱,说拿就拿的!
余大发卷起袖子,露出要打架的样子,手里紧捏着那把锹,沉着脸走下坡去,心里盘算着要首先给他个下马威,然后再狠狠宰他一下。不是新车嘛,有的是钱!他摆足了架势,提高了嗓音威严地咳了一声。
正低头铺垫着那个路坑的小伙子,听见声音抬起头来,刚看了一眼,就丢下手里的一块石头,慢慢直起身来,然后张开了口:
爹!
这一声爹叫得来势汹汹的人一愣,余大发停住了脚步,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可也就是一瞬,这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即刻布满了惊喜,或者天下当老子的天生对儿子有特殊的敏感,这个站在面前的大小伙子,让他一下看出了十年前,那个像条小狗样在他腿前蹦跳的影子。
小强!?
不错,这眉眼儿,这像小狗样爱皱鼻子的神情儿,就是他出门前还在念叨,还在想着的分别了十年的儿子。
十年前,余大发正处于他人生的最低谷,到处躲债,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子寄托在邻居家里,自身就无暇顾及,哪还顾得了天天糊得像个小花猫的儿子。虽然分舍不下也不甘心,可是听说了他的情况的老婆和那个开着大车的络腮胡子来接儿子的时候,也只好眼巴巴地让老婆拉着儿子的手走了。
没想到,事隔十年,这小子竟然从天而降,还开回了一辆崭新的大卡车。见他又惊喜又疑惑的样儿,儿子告诉他,这是他自己贷款买的,刚刚上路不到一个月。他一直没有忘记他这个当爹的,现在有了车,自己也可以作主了,就绕道儿开回来,看他这个当老子的来了。
走了这么多路,就数这云盘岭的路最乱,还差点儿滑到坎下去了!儿子说着又皱起了狗鼻子。
余大发一听,恨不得搧自己俩耳光,早知道自己的儿子会开车来,他怎么着也不会挖那些套儿,这儿子是才学的车,若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还有什么意思事活在世上!余大发想到可能带来的恶果,惊喜万分的他又感到阵阵后怕,悸恐飘上他的心头。头一次,这位对什么事都无顾忌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了自责和不安。
爹你怎么了?儿子见他刚才还喜滋滋的脸色一时变得十分难看,问道。
啊!修路、修路!——你歇会儿,我来!
余大发回过神儿来,忙把儿子推到一边,往手掌啐了一口,举起了铁锹。
儿子的归来,彻底改变了余大发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世界。
儿子把一辆新崭崭亮锃锃的大卡车,开到了家里的大门前,让那破旧的老屋顿时增添了光辉,也让这一提到子女就抬不起头的人挺直了腰杆儿。他抚摸着那簇新的钢板、车灯,乐哈哈地向村人、向伙计介绍,仿佛这都是他的功劳;当山下那些受他指使下套诈钱的人,上门来分给他一份钱财的时候,见了这车这司机,来人感到了十分意外,那余大发的笑也一时变得比牙痛还难看,一边使劲地使着眼色,生怕儿子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他向伙计们介绍儿子带给他的吃的、喝的、穿的,展示那那些衣服、鞋子、名牌的烟酒。他撕开一包包烟,打开那一瓶瓶酒,和伙计们一边共享,一边大肆宣扬,仿佛这儿子是世上最能干最孝心的儿子,他也是这世上最能耐最幸福的爹。
可儿子听不下去了,又皱起了狗鼻头,不满地扯着他的衣衫说,爹——
回头一见儿子不高兴了,这大吹大擂的家伙顿时偃旗息鼓了,还没出口的大话也如嚼得满嘴流油的肥肉一口吞了下去,喝得红膛膛的脸又嘿嘿一笑说:
好好好!我不说了。
伙计们这才发现,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原来却怕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金口玉言,儿子要他少喝酒,他果然以后就很少端杯了;儿子叫他不要买码,果然原先一有空儿就抢码报看的,现在你伸到他眼前他也不望一眼了;儿子叫他好好在家种几亩田,喂一头猪,这些原本会嗤之以鼻、从来不屑去费心的农活儿,这家伙竟然干得比谁都上心了,开口闭口,他都会说,我小强说了——
的确,儿子给他撑足了脸面,也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他不再感到孤独,生活也有了牵挂,一听见山路上传来轰隆隆的车响,他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抬起了头,猜想是不是他的小强又回来了。
他知道儿子很忙,忙着拖货,忙着还清银行的贷款。儿子说了,他还清了贷款,还要攒钱做新房,然后把他接下山去,去住那瓷砖贴得耀眼的大楼房。和伙计们一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余大发就忍不住地眉开眼笑,仿佛他就要关上他那一无所有的破旧房,去跟儿子住新房,享清福去了。活了大半辈子,余大发总算明白了,人活着,就是为后辈们活的,只有他们过得好有能耐,这人也就活得有头有脸有荣光。
又是一个雨后,山道上滑了坡,一大堆沙土拦在了公路上,也拦住一辆载重的大卡车,拦住了一位愁眉苦脸的卡车司机。驾驶舱里坐着他常带的那位女子,这时正掏出镜子涂眉画眼,他由于心情急躁,下了车舱,蹲在道旁抽着烟,望着那个一下雨就会准时出现在公路上的余光棍儿,这会儿他正挥舞着铁锹填坑铲土,忙得正起劲儿。抽烟的司机思忖着,这个牙齿比他手中的铁锹还深的家伙,这回又要诈他多少钱。就在一个月前,就是这个地方,车轮打滑,不到一支烟工夫的活儿却硬要了他一百元钱,何况这时已干了小半天。现在拖货的生意也不好做,上个月还亏了本——当这位心事重重的司机掏出他的皮夹子,要付钱的时候,破天荒,那个一望见人家的钱夹两眼就充血的家伙,这次竟然是望也不望,只是摆了摆手,说不要钱。
余哥儿,你这是——卡车司机满脸的疑惑,竟然怀疑自己听错了。
本是扛起铁锹,拿起放在地上的衣服走了几步的余大发,这时就又转过身来,望着这个愣瞪着大眼的开车的人,把两只沾满了泥的手在那件旧衣褂上背了背,说,有烟吗?
有有有!司机被提醒了似的,忙去身上掏烟。
司机掏出来一整包还没开封的烟,余大发却摆了摆了手,就你那打开了的。
哦——司机忙又从衣袋里掏出那盒半包烟,递给他。
不,就一根儿!
余大发叼着烟,自己点上,吧了一口,然后扛上了铁锹,望着这司机嘿嘿一笑,走了。
咦,这不是上次硬要了你一条烟,才放你走的余大狼吗?驾驶舱里涂脂抹粉的女子探出了头,也和那司机一样,闹不明白了。
就在这之前,那些受过气的同行们,一提起云盘岭的这条路,提起这条路上牙齿比锹还深的余大狼,就恨得牙痒痒的,还在商量什么时候要教训一下这条狼,没想到还不到一个月,这条专门毁路吃路的狼一下变成了羊了,变成一个不要任何报酬的志愿者养路工。
终于大伙儿知道了,狼变成了羊,是因为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和大伙儿一样在这条道上跑车了。
可不是嘛,这个以前像个二流子在公路上闲荡的人,现在是一有时间就在路上挖、铲、撮,过去的挖、铲、撮是在挖陷阱,现在,是在全心全意地护路了。没有多长时间,司机们发现,这条已被毁得不成样的一段公路,又恢复到了通车不久后的模样儿,淤平的排水沟修得像一条畅通的沟渠,经常滑坡的地方垒得像一封封坚固的石墙,大坑小坑全填上了石沙,打滑的地方也面上了石渣。有时开车经过,见这位义务养路工正在那个经常出事的悬崖边,赤着上身,哼哧哼哧地打着树桩,一截截危险的路段都护上了警示的木栅栏。说来了也怪,自从有了这个业务养路工,这云盘岭再也没有出过一次故障,一次车祸,上山下山,大伙儿握着方向盘放心多了。
司机们不再叫他余大狼,余杂种,开着车从他身边路过,会鸣一鸣笛,探出头打声招呼。不急着赶路的时候,那些和余大发岁数不相上下的司机,就会一减油门一踩刹车,把车停到了公路旁,拿着一包烟下车来,和那脱了上衣,正在路旁忙乎的余大发抽抽烟,拉拉家常;突然一阵响亮的鸣笛,见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正匆忙忙开着车打面前经过,车轮带飞了一块小石子儿,这余大发就会站起身来,冲着那远去的车辆喊:慢点儿啊,儿们!
仿佛所有的司机都是他儿子最好的同事,最好的朋友,和人说不上三句话,就会问:你看见了我的小强了吗?
他知道,这开大车的没有一个定数,是要五湖四海到处跑,既辛苦又操心,他帮不了儿子的什么忙,但有一条能做到,只要儿子在这条路上跑,这云盘岭的一截路,他就会维护得比所有的路段都要好。
只要儿子路过云盘岭,总要见见这个爹,有时太忙了,就在路上和他说几句话,从驾驶室里递给他一包吃的喝的穿的;有时吃了晚饭,又连夜开车走了,说是要赶时间,这时候余大发就会打着手电筒,不放心地跟着儿子的车送好远。突然看见前面的路面又坑了损了,他会急忙抱着一块石头上前去,两只脚又是踩又是跺,踩踏实了,才挥着手,一边看着儿子的车轮压过去。第二天一早,他准会又扛着锄头锹,来把那些坑凸的路段修葺得平平整整。
已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小强了,不知道他开着卡车到哪儿跑去了。儿子说春节回来的,春假过完了,也没有见他回来。他知道儿子喜欢吃熏香肠,熏腊肉,小时候曾为吵着要吃肉没少挨过他的耳光,这一年,他不仅耕种了已荒多年的田,年底还杀了一头大年猪,熏了好几串香肠,好几块腊肉,让他回家也给他的妈和继父带些去——儿子的到来也让他化解了对前妻的怨恨,是他们帮他带大了儿子,让他成人,也懂得了孝心。可是春天过去了,夏天到来了,挂在楼板上的香肠和腊肉都在长霉了,儿子小强也没回来。
见了那些过往的车辆,他总会问人家见到他的小强没有,有人说好长时间前,见过那辆车尾号696的140大卡车,有的却摇一摇头。
没有他的电话吗,打电话问问嘛。
有人出着主意。他有一个电话,那是儿子最后一次回家时,给他买的。可是他却很少打,因为只有顺着山路爬到山顶,这手机才有信号,他好不容易下了打电话的决心上了山顶,待掏出了手机,拨了号码,却又犹犹豫豫不敢去按那个键了。说不定儿子正在开车,正在经过一个危险的路段,他怕手机一响,就会分散儿子的注意力。他担心儿子的安全,怕万一出个什么差错。唉!我怎么像个娘儿们样了!他啪地关了电话,对自己一百个不满意。只要儿子好,就一百个好,一万个好!
可是见了那些过往的车辆,过往的司机,一有机会他仍会问:见了我的小强了吗?
那些车窗里的司机一个个摇头。后来,终于有人说,见了!上个星期我还见了他,出省了——
见这位父亲终于放了心,那位年岁大的司机接着说,你儿子小强说了,他忙得很,一有时间他就会来看你的——
再过一段时间,那些和儿子小强差不多岁数的司机们,见了路边这位修路的人,这个从驾驶室递来两瓶洒,那个抱下来一条烟,说是他儿子小强带给他的;儿子小强也真忙,此后真是很长时间没回来了,不是听说这回下广州,就是那回上北京,有时汇来几百元,落款都只是个余小强三个字,也没有说买车的贷款还得怎么样了,建新房的事儿又是个什么眉目。
带着对儿子的满腹挂念,余大发从山麓修路修到了山巅,他一边在云天相接的地方干活儿,一边盯望着放在大石板上的那个手机。只有到了山顶,手机才有信号,他生怕漏掉儿子打来的电话。可是,除了那些无用的短信,除了偶尔几个让他丢下工具,喜出望外又大失所望的,伙计们可怜他只顾修路,成天带着干粮,在公路上一干一天的清苦生活,请他去吃顿饭打餐牙祭的电话外,并没有盼到他最想要的电话。
突然的一阵响彻山谷的车鸣,几辆大卡车又开过来了,余大发停住了手中的活儿,扶着铁锹,跟这些司机们说笑着。车辆走远了,这扶着铁锹的汉子,还望着那些远去的车辆,想着什么心事儿。
那个多次与余大发打交道,从余大发的变化联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和责任的大卡车司机,身边不再带着那些涂脂抹粉的女子了,他正儿八经当起了师傅,带起了徒弟。有一回,路过云盘岭时,见余大发又在修路,他停下了车,去敬了一根烟。回到驾驶舱,车发动了,他厉声对徒弟们说,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也不准透露车祸的半个字儿!下次你们到了广州,再给他汇两百块钱——
云盘岭出了一个志愿者,一个义务养路工的事儿,被人层层汇报到了县里市里;这一条无人看管的公路,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又被重视起来。这一年年底,余大发作为护路的标兵,和谐建设的典型,志愿者的先进,被请到了县里的表彰大会上。作为受表彰的代表,领导请他上台讲几句,这位胸前戴上了大红花的汉子,面对台下突然安静下来的黑压压的听众,突然嘴一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