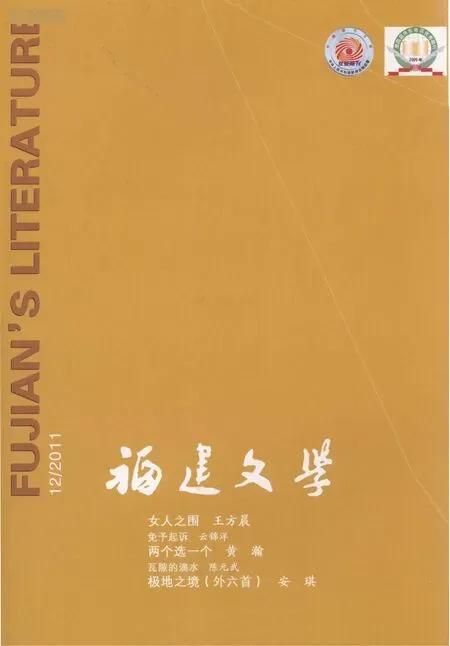无端是什么(外四首)
林宗龙
无端是什么?乌云像庞然大物,
在空中移动。哦,一道法令,即将颁布。
你被审判了吗?八月的野玫瑰,
已然颓败。你所看见的,难道都是
假象?落地窗前,一株抽象的盆栽,
线条柔美而晦涩的雕塑。硬而冷的身体,
是你给我的全部吗?我穿过布满
钢筋的水泥盒子,你可曾听见,一颗潮水般,
奔赴独立的心。我要的不是血肉和温度,
而是,可以放下重量的乌托之邦。
海水像音乐,涌来又退去。
每个清晨都是黄昏。
永恒的流浪者
当火车在暮色中的铁轨流动。
你不会像我这样保持
简单的快乐。倚着窗仰望着星空。或者,
翻出背包里的一卷报纸。
很多东西,在那里放久了
都变得不可靠。
你想象不到,我读到某则新闻时,
竟然会不知所措。
或者缘于一场苦难,比如洪灾中流离失所的
外族人民。又或者因为一则
无关痛痒的八卦。
你告诉我,它们已经过去了。
像六月,唯一能够让人惊喜的是:一些人
为了爱继续活了下去。
下雨之夜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
当我忘怀地抱着吉他,在这下雨之夜。
说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说,
那个十九岁就成家的男人,
做过锯木场工人,
当过药店送货员。这些细微而深刻的存在,
触动了我。在这下雨之夜,
我看见他,穿着雨靴,
在出租房外的香樟树底下
望着我,深吸完一口烟,然后穿过
那些狭窄而潮湿的巷子。
这些幻象,我并没有告诉你,
就像刚才,我们在阳台吃木瓜的片刻,
有人用锥子敲了下
我的肩膀,然后若无其事地说,
“河中的鲟鱼,已经上了岸。”
另一个性别的我
陌生的小镇更加陌生
街心公园的苏铁,蒙着一层薄薄的细纱
我会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停下来。我会穿过你曾出现过的
教堂和店铺
甚至会忘了你是谁
也许那是风的另一种形式
沉重的鱼尾葵,不断地在里面摆动
我知道你要说话了
你消失已久的身体
依然含混着丁香鱼的气味
我知道你到过大海
它的尽头,是长长的迷宫一样的走廊
我见过你从这里
消失。仿佛受到神秘力量的暗示
泉眼溢出水来
而我依然一知半解地爱着
那棵梨树的假象
引 力
我被什么支配着
弯下树枝一样的身体
和你在车站道别
我拦住蓝色的出租车
去你流过泪的地方
那里是爱的回忆
沾着薄薄的雾气
有时候,天气变糟了
我莫名地站在索桥上
看着运沙的船
莫名地划出一道水痕
可我仍旧一无所知
被什么支配着
走来走去,有时候
在梦境里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跟踪我
柔软的像流水
坚硬得像一块巨石
它们击中了我
让我战栗地用树叶
覆盖住那些
凹陷下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