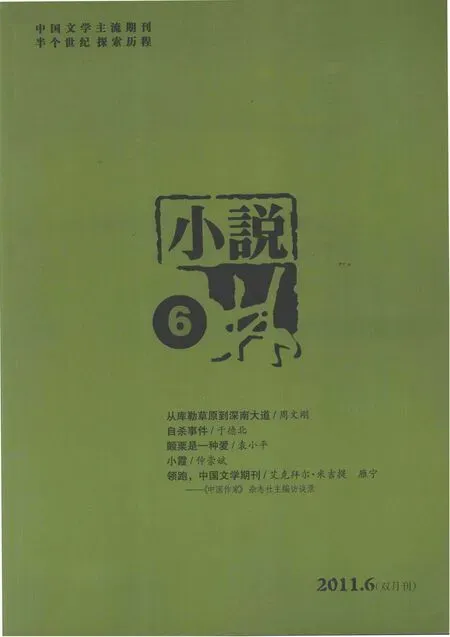狼在道上
■刘耀兰
黄江城里每天堵车早已不是新闻了,近来发展到城外那条乡下公路也堵。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一条一级公路有收费站,除了公车交的是公家的钱愿意从那条线路走外,其余的车都要绕道而行挤上这条乡级公路。邓家湾村就在路边,这条公路两边不是村落就是田地。近年来,这条道因年久失修,水泥路面破坏了,露出了硬硬的黄泥土来,再加上路面狭窄,事故频出,所以常常发生大拥堵。每当这时,村里人就全跑到路边看热闹。那些大小车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有时一堵就是大半天。有些司机心急火燎地骂娘,有些司机下车就在路边小便,有些司机无聊了,仰儿八叉地躺在那些开满草籽花的田里伸腿睡觉,还有的跑到路边地里偷红薯、甘蔗吃。吴村长向乡长打电话反映,可乡长说,这些事不要找我,你们逮住了就罚他的款。
乡长的话给了吴村长启发,他想道: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何不把握商机,借这条路脱贫致富呢?于是,吴村长就像得了上方宝剑,自己印了几大本收据,盖上村委会公章,派了外号叫二杆子三麻子四瘌痢的地痞和一群喽负责罚款。可是,事与愿违,当这些人戴上红袖箍,手拿收据上路时,那些司机却规规矩矩,丝毫没有犯上作乱的意思,罚款收入呈直线下滑。吴村长先是怀疑这些人吃黑,后来明察暗访,发现那些堵车司机一个个像乌龟一样把身子缩在车子里,见那几个地痞连大气也不敢出。
地痞也很着急呀,他们的收入可是跟工资挂钩的,没有收入他们哪有工资?有一个司机大概是尿憋急了,他躬着身子跳下了车,那个叫二杆子的一见,猛地跨了过去,唰地撕下了一张收据递过去。那个司机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会儿,然后赔着笑脸说:“我看看我的车胎有没有气。”转过身,急忙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虽说线路三两天堵车,可也不是天天堵,眼看几天没开张做生意了,二杆子们也心灰意冷了,他们如霜打的茄子——一个个蔫头耷拉脑地躺在那里睡觉,时不时懒洋洋地朝路上看几眼。
这一天,车子已经堵了大半天了,估计又是前面出了重大车祸。三麻子四瘌痢还在地上睡大觉,二杆子比以往更精了,他感觉今天肯定有收获。果然不出所料,前面那块红薯地里有个人蹲在那里,一定是有人趁机偷红薯。
他快步朝那块地奔去,在离那人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大吼道:“谁让你偷红薯的?罚款一百元!”
那人一低头露出白白的屁股,说:“拉屎。”
“拉屎咋的啦?污染环境,罚款二百!”
那人不慌不忙地答道:“那你家是把拉出来了的再吃进去?”
“你妈的个巴子!”二杆子怒骂一声,朝那人的屁股踢过去。
可是还没等明白是咋回事,他就被那人撂在了地上。三麻子四瘌痢一见二杆子吃了亏,便叫嚷着冲了过来,被那人三下两下就全撂地上了。二杆子哪里吃过这等亏,他跳起来又要挥拳打来。那人早就系好了裤子,他刚一挥拳就被稳稳地捉住了拳头,并将他的手腕慢慢往紧里捏,二杆子的脸也慢慢变了形,并由红变白起来。
“大哥,饶……饶命……”
那人这才放了手。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你认得我吗?”
二杆子摇了摇头。
“哦,那我不怪你。我就是王叫天。”
二杆子一听吓得腿一软,跪了下来,三麻子四瘌痢也战战兢兢地跪了下去。王叫天虽说也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但他的名声却让他们吓破了胆。
“大哥,我叫二杆子,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没啥手艺,就在这条路上靠捉人家偷菜偷红薯甘蔗罚俩钱混口饭吃,收的钱还要上交村委会。况且这里也不是天天堵车,很难捉到犯规的人,今天冲犯了你老人家,还请见谅。”
王叫天略一思索,说:“这样吧,我让我手下弟兄与你们合作,我们保证堵车,你们保证罚款收钱。具体如何操作,你们再看着办,你们每天交点钱就行。”
王叫天在他们的一片感恩声中,扬长而去了。
也真的是奇怪,就在第二天,那条公路就出现了堵车,而且一堵就是大半天。二杆子们兴奋不已,可是,正当他们想大捞一把时,那道上井然的秩序和待在车里一动不动的文明司机,让他们一个个傻眼了。一直到堵车结束,也没逮到一个不文明和违法乱纪的司机。
就在这时,王叫天和他那一帮兄弟们来了。王叫天说:“今天堵了近两个小时,你该给我多少钱?”
二杆子叫苦道:“大哥,现在的司机不知咋都这么遵纪守法,不要说没有人偷红薯甘蔗,就连向公路吐痰的都没有,我连一分钱也没收到呀。”
“别在我面前叫苦!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我保证堵车,你必须付报酬!这样吧,你今天就给我弟兄们五百元茶水钱,下不为例。”
二杆子不傻,他问:“我有一点不明白,大哥,你是啥办法让这条道堵车的?”
王叫天微微一笑,说:“你小子屁股没抬,我就知道你拉的啥,你心里是说凭啥一堵车就要我交钱给你,是吧?那好吧,你明天去看看就明白了。”
第二天,那条道堵车时,王叫天便来叫他去看现场。原来,那堵车是人为的,二台破农用车像是牛犄角样抵在一起横在道中央,两个人在那里谁也不肯相让,互相指着鼻子骂娘,不管后面的司机喇叭鸣得震耳欲聋,他们就是不让。
王叫天拍了拍二杆子的肩膀说:“明白了吧?那就是我们的人,你说你不给钱,他们的误工费谁付?”
二杆子找来了吴村长,说:“村长,我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
王叫天找上门来了,吴村长说:“谁经营我们不管,我只管收钱。我们把这条道的经营权转让给你,我们甩死砣子,罚款的人员由你们定,工资由你们出。”
王叫天哈哈一笑,说:“那咱们一言为定。”
就在当夜,王叫天便叫车拉了几大车土堆在路上,让来往车辆不能会车。他还在一处坡上洒了一层黄泥土,让上坡的车打滑。那时正值春雨连绵季节,三天两天下雨,那条道一般的车根本就无法顺利地开过去。王叫天和一帮兄弟,还有雇的那头驴子候在那里,一旦有车不能上坡,或者是有车被那条窄道上的车流挤到田里地里,驴子和他那帮弟兄便大展身手,将一辆辆车拉上坡或者拉上岸,大车五百,小车三百。司机行到此处也格外小心,可是不管多小心,总有那些倒霉司机中他们的计,一天下来他们的收入很可观。
这样一来,二杆子三麻子四瘌痢的眼睛红了,他们鼓动村民要求收回经营权。在万般无奈之下,吴村长向王叫天说了一肚子好话,并许诺过了一年后一定把经营权归还他,王叫天这才答应了。
收回了经营权,二杆子又都重新上岗了,并收了一些村民为股东。可是,没过多久,村民们又有意见,那些没参加的村民也纷纷要求合股经营。事情没那么简单,谁愿意把到嘴的肉分一块出去?于是,三麻子邀请一部分没有股份的村民经营着第二段,四瘌痢则与另一些村民经营着第三段。
还有一些没入股的找到村委会来,要求村里一碗水端平。吴村长说:“这我可管不了,我只管收钱,你们自己去协商。”
这些人大都是老实巴交的老弱病残的农民,见村里不管,也只能忍气吞声。
由于吴村长领导有方,开拓农村致富渠道,被乡领导破格提升为乡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兼村长,在乡里有他独立的办公室。吴村长在村里待的时候少了,多半时间是泡在了镇里新开的一家休闲屋里。
有一天,天空下着小雨,这可正是二杆子们忙碌的时候,路上停摆的车实在太多了。突然从小镇方向开来了一辆白色小车,那小车司机在使劲按着喇叭。二杆子不耐烦地骂道:“咋催的那么急,死人啦?”
好不容易把前面的车子从泥坑里拉出来,这辆车正准备加足马力跑过去时,也突然掉进那个坑里动弹不得。二杆子正吆喝着驴子拉车,三麻子赶来了,他拦在驴子前,说:“二杆子哥,咱们兄弟归兄弟,生意归生意,这里本来是我们的地盘,你已经拉了三辆车了,这次该我们的了。”
二杆子脸红脖子粗地说道:“你说的啥,三麻子兄弟?当初不是我叫你出来,你有这等好事?你别过河拆桥啊。”
三麻子也不让步,他说:“你不说这个我倒好些,你要提起这个我就有气!当初没单干的时候,我们多卖力,可你给我多少钱了?分单干了,你得好地段油水多的地段,拿我当傻子啊?”
正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时,四瘌痢也来了,他在路中一横,说:“你们都别争了,你们都开过张吧?可我还没开张呢,这辆车该轮到我了!”
三个人开始是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后来发展到动武了。那辆小车上下来了一个妖冶的女人,她打躬作揖道:“各位兄长别打了,请你们帮帮忙,车里有一个病人要送到城里医院抢救。”
二杆子见过这个女人,她就是休闲庄老板。要在平日,他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可今天不同。他骂了声:“臭娘们儿知道啥?给我滚远点!”
那个女人带着哭腔说:“求你们帮帮忙,他是在我店里玩的时候出的事,要是迟了出了人命,我在街上就混不下去了。看在人命关天的份儿上,你们就帮我把车推上来吧,我每人给你二百。”
那女人说着,就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拿出一沓钱来塞在他们手上。二杆子还在迟疑不决,那女人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拉着二杆子的手说:“兄长,我是王叫天相好的,你们是朋友,你难道连他的账也不买吗?”
二杆子这才把手一挥:“拉车!”
车子拉起来了,然后朝城里狂奔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二杆子到路上来上班,他阴沉着脸对三麻子四瘌痢说道:“你们知道昨天那车里躺着的是谁吗?”
“是谁?”
“咱们村的吴村长!他由于玩得太过兴奋诱发脑溢血,昨天到医院就死了,医生说要早来半个小时就有救,昨天我们在这里扯皮就扯了一个小时。”
四瘌痢小声说:“他把我们挣的钱贪污拿去求官、玩女人,死了怪鬼!”
突然,四瘌痢指着村委会的大门说:“你们快看,谁在村门口贴了对联?”
那是农村常见的,在春节时怀念逝去亲人贴在门口的紫色挽联。那对联的字体很大,字体很工整,竖联是:想办法以破道升官,动脑筋靠烂路发财。横联是:狼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