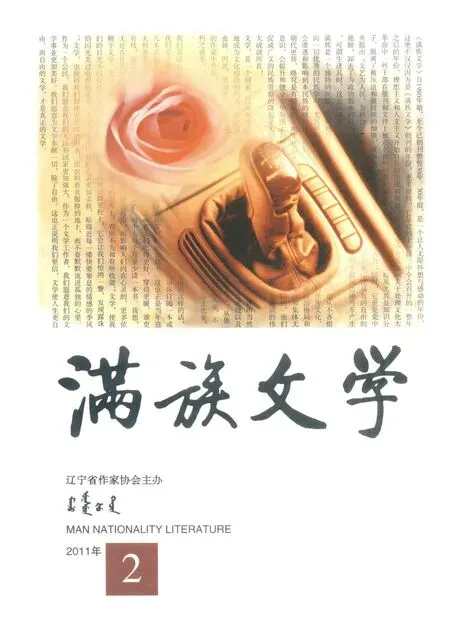话味儿
(满族)吴庚秀
话味儿
(满族)吴庚秀
我真叹服有的字典给一些汉语字、词下的释意非但十分准确,而且很有意味。“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向较深的地方挖”是“抠”字;“抓阄儿”是“从事先做好记号的纸团或纸条中取一个,以决定做什么事情或得到什么东西”;“人体上肢末端能够拿东西的部分”是“手”;“骨”是“某些动物体内起支撑作用的坚硬组织(这一注释我可觉得似有纰漏,龟鳖一类动物的外壳也是骨,称作甲骨,然却不是长在体内)”;“将臀部放在椅子等物体上以支撑身体”则很显然地就是“坐”……
是不是都挺有意思?可细想想,我以为家乡的一些方言比这更妙,且从中引发的一些故事又让人感悟多多,甚则令人警省。
我的家乡在辽东山区,那儿旗人(满族)居多。听长者讲,或是从史料里知道,现在的瓜尔佳(关)、富察(傅)、完颜(汪)、伊尔根觉罗(赵)、赫舍里(赫)等氏满人都是在200年前的清乾隆年间从长白山一带迁徙过来的。说是,当时连年征战稍息,朝庭号召居于白山黑水间的八旗满人南下垦荒植田,以兴族业,壮大朝廷势力。山青水碧、物产丰饶的辽东山区一带为他们所看好,便纷纷涌来,和后来的汉、蒙等族一道开发乡土,世代繁衍生息。
因是生在解放后,对于上面所述的事情我自然只是听说,并非真的“知道”。作为满族后生,我真切听到并且记忆清晰的是族人的语言,特别是他们的一些方言。幼年的时候,常听得他们从嗓里发出这样一个字音:“课”。倘有猪狗闯入院中,他们就会一边用棍棒往出轰赶一边大声喊喝:“滚出课!”父亲的哥哥我叫大爷,当然那个“爷”字也不发“Yé”音,而是说成“Yē”。大爷旧社会读了两年私塾,有点学问,因而我曾问过他那个“课”字的意思,大爷说,那是在旗(满族)话,是“去”的意思。后来我自下悟到,事情大约应是这样:满人学得了汉话后,虽渐而将自己的语言摒弃,有的却还保留下来,混杂使用,“课”便是,真有意思。
大爷还说,一屯子的旗人同时发出“Kè”声是在70年前。接着,他就讲出了那段故事——
那一年的一个暑日的正午,屯后大河上下静悄悄,河边的一丛柳毛子里,有轻轻的撩水声,闪动着白光光的身影。是屯中的几个少妇耐不得燥热,在那儿弄水爽身。正此间,又有七八条黑影幽灵般悄悄地急速地向那儿跃进。这是一小拨日本鬼子,他们刚才在河对岸的草丛中就窥见了这边的情景,登时兽性大发,急不可耐地从下游趟过河来,借河边茅草的掩护向目标靠近,欲行不轨。
少妇们因为忘乎所已地弄水嬉戏,全然没察觉到正在发生的意外情况。鬼子很快就挨近了那处柳丛,个个急忙剥衣解甲,把枪支也急急地丢下,便纵身跃入水中。
卒然而至的淫魔,令少妇们大惊失色,个个失声尖叫,奋力挣扎,想挣脱魔爪逃上岸去。怎奈色鬼体躯强壮,早已一人(或两人)一个地将少妇们紧紧揽住,且发出狂荡的淫笑声:“哈哈,花姑娘的,大大的这个!”
这工夫,那场景被一个人发现了。那人是我大爷。大爷那时才17岁,终日给大户人家放猪。当时他正想将猪儿从上游的河滩上往屯里赶,到屯边时,忽就瞧见了那一幕令他热血上涌的恶行。很有计谋的大爷觉得他一人不是那些畜牲的对手,正欲回屯求助乡亲,忽又发现河岸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定睛看时,原是数支大枪,心中按捺不住狂喜,便俯下身飞快地奔过去,把那些大枪统统揽入怀中,向屯中飞奔而去。这一切,兽行正烈的鬼子们竟全无察觉。
屯中的乡亲们听了大爷急切的诉说后,气得个个瞪圆了双眼。因为没人会放枪,就把那些大枪藏进烟囱里,人人荷锄携镰,蜂涌般窜出屯子,杀向河岸。有长者呼了一声,众人便齐声大喝:“小鬼子,你们这帮畜牲,赶快滚出课!”“小鼻子,王八蛋,都死课!”满语的那个“Kè”字,喊得若惊雷炸响,震得山鸣谷应。
结果可想而知,几名赤手空拳的鬼子被百余舞锄挥镰的乡亲全砍死在河里。那当儿,血气方刚的大爷还一镰刀将一名鬼子裆间的家什削去……
当然,家乡的方言还有不少,因为特感兴趣便格外留意,且自下一一作了注解。“该”即“街”的意思,如“我想上趟该”;“乌叉”就是猪臀肉;“乌突”即未烧开的水;“铺衬”就是破旧的布片儿;“圪孬”即碎草乱柴之类;“坐清”就是“将盛有液体的容器相对静止地搁置一段时间使杂质沉淀”;“tělē”就是“埋汰”;“雨作”即“舒服”;“歇咧”是“过分夸大”;“kèlāo”就是“某种欲望(食、性等)没有得到满足”;“左溜儿”意为“反正”,如“吃就吃,左溜儿我也饿了”;“遇底”意为“从来”,如“那地方我遇底也没去过”;“连项”就是“紧接着”,如“他挑完水连项就去扫院子”,等等。
大爷还说,比较起来,在这些乡人常说的方言中,“坐清”最有来历和故事。他的意思大致是,“坐清”来源于满人先祖摆粉子。摆粉子就是在秋季将刚刚成熟的新玉米浸泡数日,用石磨磨成米汤,再拿布口袋滤去皮渣,装入大缸里用棍棒搅动,一边搅一边念叨:“青娘娘站,白娘娘坐。”青娘娘是水,白娘娘就是玉米粉。据说,这样一念叨,粉子就会出的多(由此可以推断,“坐清”是汉语的音变,即由混浊到清净)。
坐清出的玉米粉,除了食用(包饺子、勾芡等)外,更大的用项是用来浆洗衣物,这也是满族先人的发明。说是有一回,一个懒汉把他穿的一件又脏又臭满是汗碱怎么也洗不净的夹袄搭在墙头上晾晒,被风刮入墙根下正在坐清粉子的大缸里,沾上了白白的玉米粉。懒汉觉得晦气,就扬手把夹袄扔到小溪里,过后想想又觉舍不得,便又去取,拿起来一看,那件夹袄竟然洁净如新。原来,上面的污物早随玉米粉一起漂走了。
大爷说,他快30岁那年秋的一天,一队解放军忽然进了小屯,说是要休整一下,然后打进县城,消灭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乡亲们看见,可能是终日转战南北无暇顾及的原因,兵们的衣裳、行李卷儿都“tělē”得够呛,油花花绉巴巴地像抹布。当时正赶上秋玉米已下来了,众乡亲未用核计,就家家摆起了粉子,用坐清出来的玉米粉给子弟兵浆洗衣被。浑身上下整洁一新的兵孩儿们大受感奋,抖擞精神杀进县城后,以神勇之势全歼了敌人,解放了县城。
关于“kèlāo”,大爷说他差点因为这句方言丢了命。那是他快50岁的时候,屯儿里来了工宣队。有天召集乡亲一起喝高粱米稀粥,吃咸菜。贴在矮墙上的报纸上写了这样几个大黑字:忆苦思甜牢记血泪仇。叫工宣队有点意外的是,大人小孩竟都吃得舔嘴抹舌。吃了一会儿,工宣队又叫当生产队长的大爷带头忆忆苦。大爷便端着粥碗开说:“社员同志们,大伙有的可能还记着,有的就不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咱穷人一年到头就吃这个。”说着,举碗伸嘴喝了一大口粥,咂了咂又说:“还别说,这玩艺还挺好喝呢,如今要是能喝上溜儿也不错了。这几年,大家伙是不是都kèlāo完了?一年到头见不着一点油星儿,啃榆树皮子喝菜汤,这么kèlāo谁能抗了!”大爷说着的时候,工宣队问身边的人什么叫kèlāo,待弄明白后竟勃然大怒,冲大爷吼道:“你住嘴!我看你这个老贫农队长是忘了本,黑了心,想替地主富农反把,造文化大革命的反!来人!”结果可想而知,大爷在懵怔怔间就被人踢倒在地,一顿拳脚打得口鼻出血,不省人事。
至于“雨作”,那是大爷说的最后一句方言。那一年,大爷是快90岁的人了。一天,他正在屯中自家开的小卖店里坐堂,忽然觉得脑袋迷糊,就趴在柜台上睡着了。去买货的人发现了,急忙把他弄到家里。可自此大爷竟一连两日两夜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躺在小炕头上眯着眼微微喘气。家人知道他已到寿路,快不行了,就赶紧张罗后事。至第三天正午,大爷已闭紧了双眼,呼吸也相当微弱。正这时,忽听屯街上发出激烈的吵骂声。大爷竟然忽地就睁开眼且声音也不是很小地说道:“准是那两个混小子,去把他俩给我找来!”正说着,就有两个三十出头的年青人急火火走进院子,一边大声嚷:“走,找大爷评评理!”跟着就进了屋。
原来,屯中的这俩青年是邻居,住房脊挨脊。头几日,一个在房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一个在屋顶安了电视卫星天线。按说,你安你的,我装我的,应该互不相干。可过后却出现了情况:安了太阳能的水却不热,装了卫星天线的电视信号依旧。两个就都怀疑是受了对方的干扰所致(事实上或者是产品质量或按装技术上的问题),因此互相要求拆除,可谁也不愿意,就吵了起来,甚至动了武把抄。
“你们哪!”大爷挺了挺身断断续续地说:“我就核计着,事儿怪透了,如今这年月,咱庄户人日子过得多雨作,要什么有什么还闹叽叽,真是的!不雨雨作作过日子……”说到这,张眼环顾众人片刻,又悄然闭住,再没睁开。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