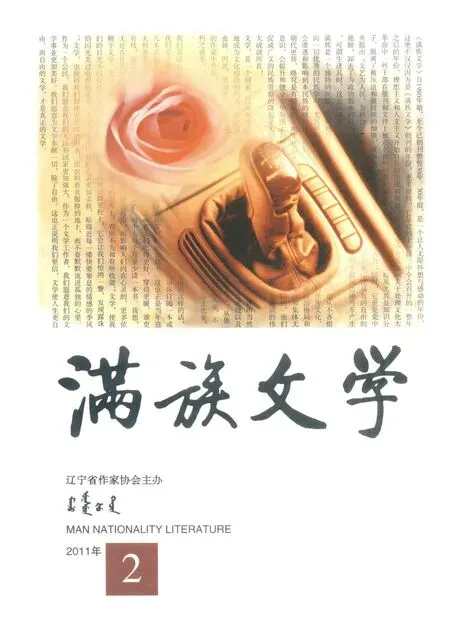天高地迥
杨明
天高地迥
杨明
一
凌晨四点,列车在一个无名小站上停靠一下,继续逆风疾行。
只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农村女子从这小站上了车,她脸上还挂着几分稚气,但明显已经是个少妇了,因为她怀里睡着一个胖娃娃。列车长静秋帮她找到座位安顿她坐好。她很快和为数不多的其他旅客一样在车轮的铿锵中昏昏欲睡了。静秋站在过道上向车厢两端眺望,透过门玻璃发现另一节车厢里,另一个列车员正坐在入口处的空座位上像旅客一样低头打盹,静秋忙走过去把他摇醒,低头对他说话。
罗诚光把这些看在眼里,笑了笑,他听不到静秋在说什么,但他完全猜得到。静秋在说,可别睡觉呀,让检查组的领导看见了,会罚死你的呀。静秋与那个刚上车的少妇年龄相仿,不过也只跑了一年车,但早已被检查组的领导们炼成金身,只要一上岗,全身的细胞立即绷成了一根根脆弱的弓弦,仿佛昆虫向天敌张开了微微颤抖的触角,高度紧张又高度灵敏。什么时候每个月底能把她那两千来块钱工资尽量完整地揣回家,她那触角才会稍稍休息片刻。和静秋相比,罗诚光年纪大了二十多岁,四十三了,却是个新乘务员,他今天才第二次登车。上班第一天登车的时候,静秋就叹着气对他说,罗师傅,现在检查组的领导越来越难对付了,我的前任刚刚因为“未向无票旅客核收足额补票款”而被抓了现行撤了职下了岗还罚了三千块钱,你可要事事小心呀。罗诚光问是怎么回事?静秋告诉他,一个衣着破旧的旅客无票乘车,验票时被列车长发现,列车长问他从哪上的车,他回答从始发站,到哪下车?回答说终点站。列车长便请他按章补交全程票费,238元。那旅客流着泪说:大兄弟,俺是个出门打工的,给老板拼死拼活卖了一年命连一分工资也没挣回来。俺这次去是讨薪的,不但没要回来,还让老板的人打了一顿,把我打屁了,差点没揍死。现在俺除了治伤吃药的钱,只剩下这些了。旅客向怀里一掏,掏出的钞票是一个汗洇洇的小团,展开一看,五十元的,里边还裹着几个一元的钢镚。列车长想了一下,对旅客说,你还没吃饭吧,这样,我不从始发站给你补票了,从验票时的前一站算起,四十七元,还能剩几块,再买包方便面吃吧。旅客眼含泪花颤着声音说:恩人呐,大恩人,要是天底下的老板都像您这样我们这些屁民就有指望了。列车长给他找了个座位,还小声对他开了句玩笑: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您就老实在这眯着吧,可千万别声张。车到终点站,那旅客下了车,和列车长紧紧握了握手,说了声:同志,可找到你了……恋恋不舍地离去。列车长的脑袋嗡地一下,脖梗后的头发根不自觉地就炸起来了,一溜烟跑到终点站调度室问调度员,今天有没有添乘检查的领导?调度员查了一下说有,路风纠查科的张科长刚刚微服私访了,列车长哀叹一声:完了……罗诚光听得拍案而起:这不叫钓鱼吗!静秋苦笑一声:罗师傅,我们这位列车长还真就姓于,他活该啊。静秋用一副久历江湖的口吻说,罗师傅,检查组的领导罚咱们的款他们是有提成的,起码能得一半,所以他们才那么有干劲有创意,咱就这工作环境,和你以前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你得适应,要迅速适应。
静秋从那节车厢回来,操起拖把拖地。现在,满车厢里只有她和罗诚光是警醒的。
二
列车行驶的方向是正东,向太阳升起和晨曦将至的地方前进。罗诚光凝视着车窗外,风驰电掣的速度分分秒秒地将飞逝的景色一点点带得明亮起来,仿佛一阵透明的风拂开了一层往事的轻纱。速度又是一支快意的画笔,窗外的景色就是一轴不断展开的黑白风景画,画笔在动感中为风景画重新进行润色和点染,颜色的基调首先是亮,露水一样无色的晶亮,然后才是斑斓的反射,赤橙黄绿青蓝紫。
罗诚光二十三岁那年从部队转业,到铁路林场工作,工作不久罗诚光在一次作业中为了掩护工友而被伐倒的树砸中了腰,留下了终生的残疾,他的腰上永远缠着护腰带,不能吃一点力,平时连久坐久站都不能坚持,走路时也比别人步态沉重。后来他做了近二十年的护林员,每天与青山为伴,长年的孤寂生活让他远离外界的尘嚣,养成了他习惯安静,亲近自然的习性。他觉得这样与世无争挺好,一度让他觉得山间那座背风而向阳的石屋就是他此生的归宿。
今年,他的归宿不再属于他了,推土机和施工队开进了山里。成片成片成材和未成材的树和苗被放倒和连根拔出。罗诚光心疼地想,连个树崽也不留下,以后拿什么去栽铁路两侧的防护林呢?罗诚光知道这不是归他该操心的事,他只知道这里不久将变成别墅区,林场让管事的领导给卖了,卖给做房地产的开发商了。他默默地看着住了二十年的石屋在推土机的履带下灰飞烟灭,转身离山而去。
幻想中的归宿没了,现实里的路还要走下去。罗诚光第二次转业,拿着一纸调令来到铁路列车乘务队报到。他的一个原来的同事,也是四十岁左右,早在去年就掌握了林场将要成为开发商囊中之物的确切消息,不像他,推土机开到了眼前才明白大限临头。同事办到手一张工伤证明,林场一易主就立即回家退养去了。罗诚光知道,同事壮得像一头牛,甭说工伤,连私伤都没有,简直比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都能干。从他不断地离婚结婚,最后一次又找了一个比他小二十来岁的老婆上就能得到很充沛的证明。罗诚光又想,这大概就是人与人的区别吧。同事就是离一百次婚也能引来妙龄女人投怀送抱,这叫本事。自己一辈子没结上一次婚,仿佛一条被女人们遗忘在岸上的鱼,这叫没本事。同事能空手套白狼弄来工伤证明,这同样叫本事,自己明明套着护腰带却两手空空,这同样叫没本事。
当年,罗诚光救下的那个工友是违章作业,林场领导对罗诚光说:如果给你报工伤,他肯定要受处罚,弄不好还会被开除公职,单位也会爱影响,所有同事的安全奖都会被扣除,你说你闹了归齐救了人也害了人吗,你能忍心吗?领导又说,小罗你放心,场里是不会不管你的,只要有我在,你永远是场里的第一功臣,永远让你享受场里的最高待遇。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领导当初说过的话和那位工友曾被罗诚光救过的事,早已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有开发商的建筑蓝图和推土机的轰鸣声。连罗诚光自己都快不记得自己是否真的受过伤了。
列车乘务队队长把罗诚光分到了静秋的乘务组,罗诚光的新职名是“见习列车员”。罗诚光觉得自己被见习了。见习期定为半年,半年间他要跟着静秋乘务组的列车员们学徒。列车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到站时开车门关车门迎送旅客,运行中不断扫地拖地清扫和保持车厢内卫生,可以说操作简单,过程乏味,只要有责任心和基本技能都能做得好。最让罗诚光打怵的就是扫地和拖地,他每每看着各节车厢他的年轻“师傅”们拿着条帚拖把汗流浃背就心惊肉跳。扫地拖地需要弯腰,他一个连久坐久站都视为奢侈享受的人,弯腰和登天基本上是一个难度系数。一节车厢近二十米长,“师傅”们拖完一节车厢一般十分钟左右。一次罗诚光鼓足了勇气悄悄抓起了拖布,二十分钟擦了五米长的距离,他只觉得有一万根钢针在他腰眼的同一个穴位上做针灸,他两手抓住拖布杆往下滑,不自觉就跪了下去。眼前就跟凌晨四点刚开车那会似的,黑咕隆冬啥也看不见。静秋看到了他这副样子,慌忙把他扶起来在座位上坐好,说,罗师傅,你急什么呀?她把补票夹递给罗诚光说:您放心,咱乘务组不会不管你的,这半年只要有我在,啥重活也不用您干,您就干最轻松的吧,帮我补票就行了。类似的话罗诚光听着耳熟,好像好多年前有的领导也对他说过,不一样的领导,话里的滋味也不一样。
像条件反射一般,罗诚光忽然觉得腰间又不能供给他足够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的力量了,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站得颤颤巍巍,双手撑住腰两侧。
也许是情绪的影响,站得稍有些猛,只觉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仿佛天阴了一般。
罗诚光很悲哀地想,饭碗啊,为什么非要弯下腰才能端得你呢?半年一晃就会过去,半年以后会怎么样呢?他扭头看车窗外,天忽然间竟然真的阴了,太阳失踪的瞬间正是最浑浑沌沌的时候,什么也看不清。
罗师傅、罗师傅——阴天了,车厢里黑了,麻烦你快去乘务室把照明灯打开……车厢远处传来静秋的喊声。
咔地一声,灯亮了,略显昏黄的灯光在黑云欲摧的窗外大背景中把车厢内小小的空间映得格外温馨。
罗诚光从乘务室出来,一下子不好意思了,一眼看到,那个稚气的少妇撩起了衣襟,胖娃娃贪婪地捧着一只白嫩丰盈的乳房吮得咂咂有声。罗诚光一辈子没见过女人的肉体,那灯光下昏黄中笼罩着的浑圆的象牙色让他大脑缺氧,胖娃娃忽然呛了一下,猛扭过头剧烈地咳起来,少妇的乳头勃然而出,淡烟色的,罗诚光那腰再也把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座席上,细听,窗外,喷泄而下的暴雨突如其来了……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避风塘,避风塘车站就要到啦,请下车的旅客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车——列车广播里忽然传来静秋那温和悦耳的女中音。
罗诚光心里一暖,觉得腰也不那么疼了。这站名多好,他心想。
三
车停了,到避风塘车站。
外边风很大,雨更大。
静秋临停车前去列车厕所门外,用不锈钢钥匙清脆敲了敲厕所门,叫:快点快点,出来出来,马上到站了。厕所门哐地一声撞开了,一个穿蒙古袍的大汉抓着腰带闯出来,不高兴地嚷道:叫什么叫啊,都让你给吓回去啦,你们铁路就这么对待阶级兄弟啊?怪不得都叫你们霸王条款呢。静秋笑笑,锁了厕所门。车恰好停了,静秋去开车门,下到站台上,迎客。
罗诚光的所有“师傅”们都下车迎客去了。整列车上貌似没有乘务员了,罗诚光看到,那稚气的少妇身边,一个三十来岁的,看上去很有气质的、文文静静的女旅客沉稳地站起来走到厕所门边,她顾盼流波,眼神左右一瞟,用手扭了一下门把手,门把没动,那女旅客就开始动了,手像电流一样,一把和静秋一模一样的车门钥匙晶光一晃就插进了锁眼里,咔地轻微一响,门乖乖地开了。那女旅客掏出一只笔和一个小笔记本,流利地记了几笔,然后站在厕所门边守株待兔。
静秋回来了,车又开了。女旅客很矜持地和静秋点点头,说,检查组的,掏出证件请静秋过目。静秋扫一眼证件,忙陪出笑脸说,哟,原来是刘主任,请到列车办公席去坐吧。刘主任说,不了,你是车长吧,请你把行车规章第二条第三款背诵一下。静秋迟缓了一下,张口背诵道:列车员要在列车到达每个大小车站前必须锁闭厕所门,停车时禁止旅客使用厕所……刘主任把手中的小笔记本一挥,说,好了,不用再背下去了,下面谈谈你明知故犯的问题,用笔记本一指厕所门:方才你为什么没锁厕所门?静秋愣了,看着厕所门嚅道:我锁了呀……刘主任笑了笑:这门明明开着,怎么处罚将取决于你的态度,可以罚A级,300元,也可以从轻罚B级,200元。你现在认真回忆一下,是不是临到站前忘锁了?工作失误嘛,可以谅解,谁都会有的。静秋轻轻叹了口气:那可能,是我忘锁了吧……刘主任痛心疾首地摇了摇头,说,什么叫可能呢,同志,看来你的态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啊。刘主任嚓地一声从小笔记本上撕下一张塞给静秋,命令道:拿着,A级处罚单一张,你签个名。
罗诚光心想,这已经不是在钓鱼了,这明明是在挖陷阱打野兽。
罗诚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他和静秋和自己所有的那些“师傅”们一样,都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制服衬衫,黄色的铜扣,黑色的肩章,白色的乘务员胸牌,是按照行车规章的要求统一着装的。
罗诚光悄悄脱掉了制服衬衫,光着上身站了起来,向厕所门走了两步,抬手指定刘主任:门是你开的!
什么,罗诚光声音不高却把刘主任和静秋都震得目瞪口呆。刘主任盯住罗诚光:你是干什么的?
罗诚光双手抱臂,冷笑道:这你管不着,反正我不是你的长工,你罚得着给你们卖命的人,罚不着我。他略偏偏脸看看满脸惊愕的静秋,用眼神稳住她。又向前跨出一大步,腰挺得笔直,与刘主任对视,说:看你像个人似的,原来只是披了一张人皮!
罗诚光的目光,他赤裸的上身,尤其是那条黑色的宽宽的功夫腰带(刘主任不认识护腰带)让刘主任莫名地慌乱,这一定是个在社会混的人吧?刘主任实在搞不清罗诚光的来路。
这其实怪刘主任自己。她只关注厕所门了,仿佛那上边贴满了钞票,罗诚光没脱制服时在她旁边走过几趟,她视而不见。
刘主任定定神,反问道:我堂堂一个国家干部,谁能证明是我开的门,谁又能证明不是她没有锁门?
你是干部,还是国家的?没看出来。罗诚光回头问都在向这边望的旅客:方才是不是她开的门?有人当即回答:是,就是她开的!那个穿蒙古袍的大汉走上前,一拍胸膛瓮声瓮气地喝道:我为这位车长妹子证明,是她亲手锁的门。我站不更名坐不改姓,草原雄鹰,牧民巴特尔!
刘主任对罗诚光说:你不是铁路员工,不懂行不要乱发言,车厢厕所门是谁都能随便开得开的吗,得有列车专用钥匙才行。
罗诚光指着刘主任的裤子口袋说:你有,就在这个口袋里,你敢让人搜一搜吗?
刘主任夸张地叫道:你要干什么?要非礼吗?
罗诚光笑笑,道:放心,我不会搜你的,怕脏了我的手。这位车长也是女同志,请她来搜你不会是非礼吧?我们懂得尊重妇女,如果你怕泄露了你的春光,这不现成的厕所,要不干脆到里边去,锁上门搜,你看如何?还是请你放心,这回车长更不会忘记锁门的,我们所有旅客全体监督,怎么样,你敢吗?
刘主任说:你倒底是干什么的,男子汉敢作敢当,说出来,你敢吗?
罗诚光说,你不配。
列车忽然减速,前方又要到一个小站了。
刘主任对静秋说:我明白了,方才是个误会,这厕所门你可能是锁了但没锁住,一定是门有故障了,马上通知检修员来修,绝不能给旅客造成任何不便。
刘主任没等车停稳便到自己坐过的坐位前拿起包匆匆下车了。
罗诚光回头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脱下的衬衫了,来回找了几遍也没有,愣在原地纳闷地伸着脖子四下瞅,看见那少妇把娃娃肥嘟嘟的小嘴调换了一只乳头,腾出的那只手若无其事地向背后一抄,往身前一递,大哥,拿着。
罗诚光第一瞬间把一个场景复原了——刘主任来到座位前拿包,露着乳房的少妇手如鹰爪像窗外的闪电一般把罗诚光的衬衫抄到身后。罗诚光的第二个瞬间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在中学文艺队里排演《沂蒙颂》,他演那个八路军小伤员,沂蒙红嫂先冒着生命危险为他引开来抓捕他的汉奸(这段戏原本《沂蒙颂》里没有,校园导演根据当时当红的革命电影《女交通员》优化到里边去的),然后又用乳汁哺喂他,为他疗伤。那小伤员痊愈后临归队前动情地抱住红嫂哭着叫了声:妈妈……(当然这又是中学校园导演的臆创)
罗诚光心想,她竟然管我叫大哥,她也就二十岁呗,我要是她那岁数结了婚她得是我女儿。罗诚光只觉鼻头发酸两股咸流哽上喉头,忙捂住脸低下头去。
大哥,咋了?少妇问。
没啥,没啥,罗诚光边穿衬衫边趁人不注意用衬衫的襟边擦干眼睛。
那衬衫上还余着少妇稚嫩的体香。
四
风停了,雨还在下。静秋的声音又在通知旅客——前方到站胡家沟。
窗外雨中的乡间土路像一根绳子,被罗诚光的视角忽而拉得笔直,忽而蜿蜒曲折。罗诚光的眼睛忽然瞪大了——有两个人,在雨中拚命地奔跑。
那是一老一少,年幼的在前,年长的在后,奔跑的方向与列车相同,他们却不看火车,只是专心致志地奔跑,年幼的在撒欢,年长的低着头用力顶穿雨幕向前冲刺。只一瞬间,便被火车远远抛在身后,像两颗流星一划而过……
又过了几分钟,列车停靠胡家沟站。
本来应该只停车两分钟,但对面上行线的信号灯始终是红色。车站值班员跑来告诉司机和静秋,对面有一列特快列车晚点了,将于二十分钟后从本站通过,你们的车在本站待避,等特快列车通过后才能开行。
罗诚光下车来到站台上,雨刚好停了。水泥站台上的雨水一汪汪地晶亮着,罗诚光抬头看,发现这是个刚建成不久的站,站舍和这一刻的空气一样,是新的。站舍的面积适中,不张扬但很醒目,红的墙,蓝的塑钢屋顶。天空也是蓝的,它们刚刚一起被雨水清洗过,大团的白云在天空里追逐。罗诚光进一步发现,这个站和一般的站不一样,周边没有建筑,没有人家,是大片大片的旷野,只有在目力穷尽处才隐隐可辨依稀的村落。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建一个车站呢?这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许这里将来要拓出一个新的城镇?也许在这附近发现了矿产,这里即将成为矿区?也许这里发现了旅游资源,将来要开发?但罗诚光觉得这些都与自己无关,只觉得这遗落在茫茫天地间的清新小站非常适合自己的心情。心情是不需要原因的。“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罗诚光想起了《滕王阁序》中的这两句话。
远方长长一声汽笛,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而来,从小站隆隆通过。风声过耳,罗诚光只觉衣袂飘飘。
上行线的绿灯亮了,静秋吹响口笛,站台上下来透气的旅客和乘务员们纷纷登车……
那一老一幼就这个时候跑到了,年幼者在呼喊:火车开喽、开喽——两个人抓着车门扶手攀上了徐徐启动的列车。
那年长的六十开外了,戴了一顶布帽子,一身的衣衫湿透了,肩上背了个土篮,里面是刚刚染过雨露红绿相间的果蔬。他放下土篮蹲在车厢连接处的地板上大口喘息。年幼的看上去比他小五十多岁,身上比他还湿,白色的小褂被雨水溻成了灰黄色,站在那儿像个小蒸笼一样,脑门和领口蒸腾着热气,他忙不迭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是卡通人物的画片,从厚度上看少说也有五六十张。看样子卡片没有被浇,却被体温护得潮了。他不放心地逐张检查着,看看有没有变形和损坏。那认真专注的样子让罗诚光看了嫉妒。在孩子眼里,卡片是整个世界。
那个老人的脸色让人想起岁月的风霜,他的眼神让人想起人生六十多年所经历过的忧患。而那孩子却忽然握着卡片笑了,那笑容让罗诚光眼前一亮,阳光一样的笑容,既灿烂着童真,又闪耀着青春的先兆。
罗诚光请他们到车厢里面坐。谈话中知道他们是爷孙俩。家在离胡家沟十里开外的屯子里,去双河镇看孩子的姑姑。罗诚光笑着说,你这老爷子,我在半道上就看见你们俩在跑啦……罗诚光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今天的车因为临时待避特快列车而晚点了,如果正点运行,这爷孙俩本来是绝对赶不上车的。罗诚光好奇地问:你们不知道列车时刻吗?老人憨憨地笑笑摇摇头,不知道,俺们只知道追火车。罗诚光更好奇了。老人说:今天孙子第一天放暑假,这小子从学校回来就对我说,去看俺姑姑吧,坐火车去。罗诚光说:万一你们追不上火车呢?老人又笑了,说,没想过万一。对了,俺爷们还没来得及买票呢。罗诚光出神了,想,做什么事,只管去做,不在意结果,这是这个老人一生的行为方式吗?这是这个孩子未来的一生里将要采用的生活方式吗?为什么唯独今天特快列车晚点导致了本次列车也晚了二十多分钟呢?原来这二十多分钟不属于全列车任何一个与旅行有关的人,这二十多分钟只属于在暴风雨中专心奔跑的一老一幼,是天赐给他们的吗?
罗诚光到乘务室里用自己的钱补了两张车票,回头交给老人说,今天不收你们的票钱了,奖励你们爷俩白坐火车,票您老拿好。老人惊谔地张大嘴巴:这哪行,哪有坐车不花钱的?谁奖的?罗诚光说:我,我说了算。老人指着车票说,可这上边明明印着票价钱嘛。罗诚光笑了,说,不是跟您说了我说了算嘛,我说要钱就要钱,我说不要钱就不要钱。这车上全归我管,不单买票,连检查罚款全归我管,我说罚谁就罚谁,我说奖谁就奖谁。老人的嘴巴还在大张着,真的?还有这事?罗诚光用力点点头:真的,有这事!
罗诚光去别的车厢转了转,过了一会回来的时候,老人拉住了他,老人从土篮里拿出一捆韭菜和几只尺把长的大尖椒,孩子的两只小手捧着两只胖乎乎的西红柿。老人说:没啥好的,自家侍候的,您收下。罗诚光慌了,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咋能收您这么重的礼呢。老人急了,您是不是嫌弃我们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罗诚光把韭菜和尖椒放在鼻子底下,贪婪地嗅着,鲜菜浓郁的气味竟引起了他强烈的饥饿感,他大口大口地用口水把那种从心底涌起的饥饿感强行吞咽回肚里去。
罗诚光下意识地回头看,那少妇靠在车窗边,头歪在一边衣襟不整地睡着了。胖娃娃也在她臂弯里拖着长长的口水睡着。罗诚光愤愤不平地想,你是吃饱了,我还饿着呢。他回身到乘务室取来一件长袖的外套,走上前给少妇轻轻盖在身上。
少妇睡得很踏实,没醒。
五
罗师傅,你来一下……静秋把罗诚光叫到一个空座席,面对面坐下。
罗师傅,静秋说,对不起,这个班回去以后你去找队长调班吧。
罗诚光没听懂,看着静秋。
咱们组你不能呆了,跟队长要求到别的乘务组去吧。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吗?罗诚光问。
罗师傅,当时刘主任不过就是想罚点款,这是小事,权力在人家手里,咱得认,得低头。你却出头了,她款没罚着却伤了面子,这就是大事了。往后她得班班盯着我,早晚会给我套上小鞋。不但对我,对咱组这个小小的集体都不利。而且最不利的是你,她早晚会搞清楚你原来就是咱组的乘务员。
我不怕——罗诚光脱口而出。
我怕。静秋扭过头,对窗外的风景说。我对你说过的,咱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性质,这里不是你的林场。你走吧,我不敢留你了。
腰间猛然又剧烈地疼了,罗诚光下意识地去捂腰,可双手像硬煞车一样在半路停住了,很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他不想让静秋觉察到他此刻的痛楚,不想让静秋看到他此刻需要支撑。
对不起。罗诚光说。
列车又走过了漫长的一宿,天又要破晓了,前方距终点站已经不远了。
罗诚光仍在凝望车窗外。他在想,生活是美好的,一路上的风景也是美好的,旅途中不仅仅有刘主任,还有少妇圣洁的乳房,还有蒙古汉子巴特尔,还有在风雨中追赶火车的老人和孩子,还有胡家沟那样天高地迥的地方……
列车向东,向太阳升起和晨曦将至的地方前进。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