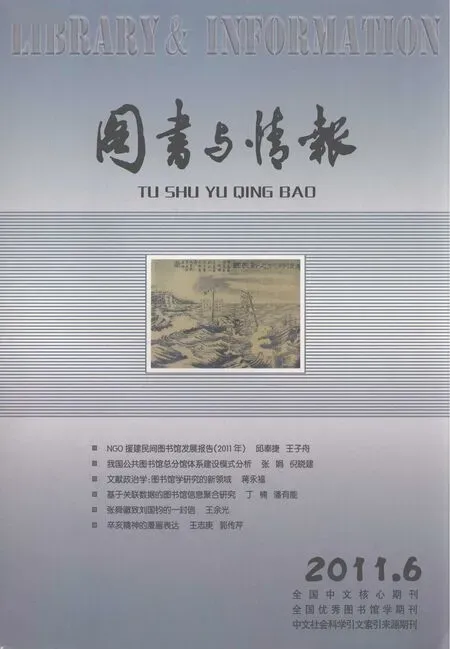文献政治学:图书馆学研究的新领域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1 文献政治学及其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什么是文献政治学?或者说,文献政治学是研究什么的学问?顾名思义,文献政治学是研究文献与政治关系的学问。从学科性质上说,文献政治学显然是文献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1]简单地说,政治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恩格斯在论述国家产生时认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这种保持“秩序”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政治权力。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分不开的,“无论如何,‘政治的’一般而言是与‘国家的’相互并列,或者至少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3]可以说,国家就是运用政治权力保持秩序的政治机器。
为了保持秩序,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加以控制,其中包括文献活动领域——文献的生产、流通、利用活动领域。在中国古代,秦朝曾发生过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自汉代始,历朝历代的皇帝大都亲自关心文献活动,许多官修书目、类书、政书、丛书就是在皇帝的过问甚至是亲自领导下编纂完成的。西方国家近代的书报刊检查制度,就是国家政治权力对文献活动加以控制的一种制度。沈固朝先生著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较详细论述了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由兴致衰的历史过程。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政治权力与文献活动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影响的历史渊源联系。研究这种历史渊源联系现象的学问就是文献政治学。
从图书馆学的角度看,文献源研究、文献阅读研究、文献整理研究(主要是书目、标引、编目等)、引文研究、文献运动规律(如普赖斯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等)研究等被认为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有人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4]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必须要研究社会的文献现象,包括文献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有“文献计量学”、“文献经济学”、“文献分类学”、“文献信息学”、“古典(文献)目录学”、“专科(文献)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文献编目(学)”等称谓,但尚未有人提出“文献政治学”这一称谓。从一般逻辑上说,如果上述“文献××学”成立,那么“文献政治学”自然也应该成立。从事实逻辑上说,既然文献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历史渊源联系,那么研究这种历史渊源联系的“文献政治学”也应该成立。吴慰慈先生认为,图书馆学与文献学之间是“同族关系”。[5]既然图书馆学与文献学是同族关系,那么图书馆学与文献学之下位类学科“文献政治学”之间当然也是同族关系。图书馆学既然可以研究 “文献计量学”、“文献分类学”等文献学之下位类学科,那么同样作为文献学下位类学科的“文献政治学”自然也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在我国,哲学、政治学、历史学领域一些学者的研究已涉及到文献政治学内容,如周光庆著有《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周裕锴著有《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李清良著有《中国阐释学》等等。不过,从这些著作的题名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从阐释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与文献政治学研究有较大区别。而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出现纯正的文献政治学研究成果。于良芝曾经使用过“图书馆政治学”一词,[6]但她没有进行专门的图书馆政治学研究。在我看来,图书馆政治学和文献政治学之间是相互交叉的关系。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文献政治学研究还是一个有待挖掘的新领域。
2 文献政治学研究示例
如何进行文献政治学研究?文献政治学研究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下面以对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目录编制中的 “经→史→子→集”次序结构安排和类书编纂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安排的分析为例予以说明。
2.1 分类目录的“经→史→子→集”次序结构
众所周知,汉代刘歆所编《七略》首创文献分类的“六分法”。其六个类目名称依次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略》中的首略为“辑略”,但此略为各略之总要,所以真正的首略是六艺略。六艺略又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个子目,①《七略·六艺略》名为“六艺”但却列出了九类,即多出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之所以如此,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解释道:“《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中也作了大体相同的解释,认为刘向、刘歆父子于五经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可见,六艺略的内容为儒家经典著作。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不仅完成文献分类的“四分法”体例,而且直命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由此“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形成;而清代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则为彻底贯彻经史子集四分法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自《隋书·经籍志》以来,中国的文献分类目录一直延续着“经→史→子→集”四部名称及其次序。那么,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为什么始终坚持以经为首的分类次序呢?这就需要我们弄清中国古人对“经“的理解。
《白虎通义·卷八·五经》曰:“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 《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 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宋人王阳明对“经”作了如下解释:“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7]《汉书·艺文志》云:“六经者,圣人之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知,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周予同先生对“经”作的通俗解释是:“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称。”[8]
经学知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经学载道、论道、传道,是所有知识的不竭之源,后世者只能通过经学才能体道、悟道,进而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语·周语下》云:“何以经国,国无经,何以出令。”《韩诗外传》卷五云:“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对此概括地说:“战国之文,皆源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另外,在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中,经书的首要地位还源于先人“文出于经”的观念。南宋陈骙在《文章精义》中认为,六经、四书“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这些认识,其实都在提出一个无形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答案就是:经学知识最有价值。②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在《教育论》一书中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后来学者们把这一问题称为“斯宾塞问题”。斯宾塞.胡毅译.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8,43。这说明,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最终旨趣不在于文献秩序,而在于 “明道”,即通过文献分类活动,把统治集团认可的“经义”(王道)凸显出来,使其法定化、常规化。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十九说得非常明确:“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
关于“经→史→子→集”的次第关系,乾隆皇帝有一段精彩比喻:“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原溯其源。 ”[9]这段话,毫无遮隐地界定了 “经→史→子→集”这种差序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经→史→子→集”差序格局,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的明确回答。这说明,“斯宾塞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早有定论,只不过中国古人认为“首重者经”而非科学知识。正因为“首重者经”,所以除了经学之外的其他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都被当作 “次等知识”而被忽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献分类方法实际上是为以纲常伦理秩序为核心旨规的统治秩序服务的工具。要言之,中国古代的文献秩序服务于伦理秩序、统治秩序,而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是文献秩序是否合理的最终依据。
2.2 类书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
自唐初纂修《艺文类聚》以来,中国古代类书的类目体例基本定型为“天→地→人→事→物”次第格局。之所以形成这种次第格局,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对 “天—地—人”三者关系赋予特定的秩序意义紧密相关。
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指出:“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在《天地阴阳》中又说:“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其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从“天、地、人,万物之本”,到“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其排序是“天→地→人→事→物”,而这正是《艺文类聚》辑录资料的编排顺序。由此断定中国古代类书的“天→地→人→事→物”大类排序导源于天人感应说,大概不会有太大异议。
清代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古代类书,“是书为编有六,为典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余,为卷一万”。其凡例详细说明了前四编按照天、地、人、物的顺序排列的理由:“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其中所谓的“三才”,即指天地人。陈鼓应先生认为,“三才说”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先秦道家天地人合一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10]
那么,中国古代类书为什么把“物”这个大类排列在最后呢?葛兆光先生的解释是,《艺文类聚》“全书最后收录的自然世界中的各种具体知识,虽然古代中国传统中本来也有‘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的说法,对这些知识有相当宽容和理解,但在七世纪,显然这些知识越来越被当作枝梢末节的粗鄙之事,《艺文类聚》把这些知识放在最后面,显示了这些知识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沉浮。”[11]其实,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把物理原理及其应用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观念极为普遍。《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上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刘歆总天下群集而奏《七略》,其中方技列于七略之末;《汉书·艺文志》将方技三十六家列于卷尾;《新唐书·方技列传》云:“凡推步(指天文、数学)卜相巧医,皆技也。”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技”、“伎”、“妓”三词同源。可见,在中国古人那里,无论是科学抑或是技术,终究不是正道,充其量只能称之为“道”的皮毛表象,是“形而下”之“器”。所以,在《艺文类聚》中,“物”这个大类共有 40 卷,按卷数比例来计算,整整占了《艺文类聚》全书的五分之二之多,然而,它却只能占据末尾之列。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确实是在追求一种秩序,但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文献秩序,而是给文献秩序以另外一种更深层的意义,或者说,文献整理活动所产生的文献秩序必须体现出更为深层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思想秩序(纲常伦理秩序)所支撑的权力秩序或统治秩序。
3 文献政治学研究的内容框架
关于文献政治学的内容体系,可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不同的内容体系。本文以“中国古代”为时空界限,把文献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文献“经典化”过程及其权力介入、文献整理活动中的权力介入、文献传播过程中的权力介入和文献阐释活动中的权力介入。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献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3.1 文献“经典化”过程及其权力介入
毋庸置疑,经典文献一经产生,其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极其强大而又明显的。而经典是通过“经典化”过程形成的。从历史事实上看,某种文献成为经典,不仅取决于该文献的思想内容本身是否 “深入人心”(内在价值),而且还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认同和宣扬。在中国古代,“十三经”的形成过程表明,某种文献能否列入“经书”范围,不仅取决于士人阶层的极力“推荐”,而且还取决于当时执政者的欣然“接纳”。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十三经”中的任何一经,如果不能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不经统治者的“同意”,就不可能入围于“十三经”之中。经典的形成过程是文献内在价值与外部权力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效果更为明显,如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于儒家经典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仅如此,“十三经”中的某一经在某一时代或朝代受到格外重视,往往也取决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如汉元帝、成帝以至哀帝时期,就出现了独尊《春秋》到独尊《诗》的转换。当时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麻醉人民,以掩盖矛盾,从而决定了《诗》比《春秋》更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是,当时外戚专权盛行,《春秋》所主张的“天子不臣母后之党”显然不利于外戚专权,而“《诗》则不然,它提倡‘温柔敦厚’,目的是培养温、良、恭、俭、让的驯服工具……所以,为了维护专权,外戚当时也特别提倡《诗》教。 ”[13]凡此种种,表明文献的“经典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权力的介入。论述和评价文献“经典化”过程中的权力介入的表现及其意义,应该成为文献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3.2 文献整理活动中的权力介入
这里的“文献整理活动”是一个广义概念,它泛指古代所进行的文献分类、编目以及编纂类书、政书、丛书、史书(正史书)等活动。从历史事实看,中国古代官方的文献整理活动中一直伴随着权力的介入。本文前面论述的分类目录编制中的“经→史→子→集”次序结构安排和类书编纂中的“天→地→人→事→物”次序结构安排,就是权力介入文献整理活动所形成的结果。当然,这种结果不完全是权力影响使然,还有这种结构安排符合文献整理所需要的客观要求的原因,但没有权力的介入,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历朝历代一贯遵循的“永制”。西汉第10位皇帝宣帝刘询召集的一次学术会议——石渠阁会议,其主要任务是“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最后“上亲称制临决”。所谓“上亲称制临决”就是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到了唐代,唐太宗令孔颖达编定《五经正义》,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结束儒学内部的宗派纷争,为科举取士和统一思想制定了“标准答案”。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统治者“御纂”、“钦定”的诸经注疏及各种类书、史书就达数十种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对文献整理活动过问最多的皇帝恐属清朝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江西巡抚海成查缴禁书“最为认真”,但由于他未能发现王锡侯《字贯》凡例内“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的严重“违碍”之处,乾隆毫不留情,立即将海成革职问罪。[14]诸如此类的皇帝亲自干预文献整理活动可视为权力介入文献整理活动的典型表现。这表明,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所表现的“整序”过程并非是完全的自足行为,而必须是按照统治者需要进行的“尊指”、“尊令”行为。揭示和批判这种权力干预文献整理活动的事实及其危害,应该成为文献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3.3 文献传播过程中的权力介入
文献传播的过程就是知识和思想传播的过程。正因为文献是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集权统治者们不可能对文献传播活动采取宽容政策,而是要加以严格控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朝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是权力介入文献传播活动的典型案例。焚书坑儒的直接导火索是博士淳于越反对废封建而立郡县的制度,称始皇不师古,于是丞相李斯认为鄙儒“以古非今”,应当禁绝“师古”的途径,其办法就是焚禁古书,绝其传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当时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于是建议“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可以说,焚书坑儒是用行政权力干预文献传播,进而阻止非正统思想传播的野蛮措施。明清时代盛行的“文字狱”现象,其实也是通过权力介入来限制文献传播进而规制思想传播的高压政策。如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正式制定有《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明确申明“字句狂谬,词语刺讥,必应销毁”。该《条款》中有这样一条规定:“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选及其诗词者,原系他人所采录,与伊等自著之书不同,应遵照原奉谕旨,将书内所引各条签名抽毁,于原版内铲除。”如果说,钱谦益等人的文献遭此厄运,是因为他们的文献中有“违碍”之处,那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拒收于《四库全书》如何解释呢?只能解释为当权者认为“奇技淫巧”无助于维护“三纲五常”之伦理秩序。据统计,乾隆皇帝亲自领导的《四库全书》禁书运动,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15]皇帝亲自领导“文字狱”运动,足见权力干预文献传播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意义。故此,阐明文献传播与权力秩序维护之间的关系,当为问先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3.4 文献阐释活动中的权力介入
中国古代的文献阐释活动源源流长。汉魏人长于注经,唐宋人长于疏注,明清人长于辨考,这种围绕经书而展开的阐释学问叫做“经学”。自孔子开创“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风以来,历代历朝的无数学者们皓首穷经,手捧经书注疏不停,撰写出了数百倍于原经篇幅的注疏著作。在“十三经”中,几乎所有的经都存在“一经多注,一注多疏”的现象。根据多种目录统计,“历代易学著作多达6000-7000种,其中现存于世界的亦近3000种”。[16]后世把古代阐释经典的学问起名为“训诂学”。 那么,古人皓首穷经、前赴后继地大量著述训诂著作的意图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明经”即明儒家经义。清人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对中国古代人来说,明儒家经义是每个有志者安身立命、登科升迁,进而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理想的必由之路。反复训解经义(即训诂活动),就是明儒家经义的具体实践。然而,中国古代的训诂活动也不完全是纯洁无暇的独立学术活动,其中贯穿着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说教,留下权力介入的痕迹。上文提到的《五经正义》的编定,以及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解》被确立为科举取士的范本,就是权力介入训诂活动的典型表现。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在许慎看来,文字训诂也要从“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高度来对待。即使是对诗歌作品的训诂,也贯穿着儒家纲常伦理说教。如 《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描写的是女主人公望见梅子落地,引起青春将逝的伤感,希望有男子来求婚。但毛传却作了如下解:“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这首呼唤爱情的恋歌之所以被附会成“男女及时”的颂歌,就在于它符合一条儒家礼规:“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所以蕃育人民也。”可以说,《诗经》中大量描写爱情的诗作大都被后来的训诂学者作了“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政治教化为旨趣的解释。对《诗经》的训解如此,对其他儒家经典的训解也大都如此,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赘述。总之,辨识和剖析文献阐释活动中的权力介入的表现及其社会后果,应该成为文献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4 结语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全面论述文献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和内容体系,而在于证明文献政治学成立的可能性。笔者之所以提出“文献政治学”这一新称谓,意旨不在于标新立异或“发明”一种新学科,而在于试探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向其他学科输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一直处于社会“公认度”不高的局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笔者看来,努力把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向其他学科输出,是提高图书馆学的社会“公认度”的必要途径。文献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有望被政治学、历史学、阐释学等学科“输入”,也就是说,文献政治学研究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向其他学科的输出。若然,笔者提出“文献政治学”的目的达到也。
[1]单继刚等.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3]卡尔·斯密特.刘宗坤译.政治的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0.
[4]何长青.文献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J].图书馆杂志,1992,(3):18-19.
[5]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修订 2 版,2008:33.
[6]于良芝,李晓新,王德恒.拓展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5.
[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54-255.
[8]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44.
[9]弘历.文渊阁记[A].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历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Z].北京:中华书局,1982:17.
[10]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7:179.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57.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13]晋文.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3):35-39.
[14][15]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3,74.
[16]周玉山.易学文献原论(一)[J].周易研究,1993,(4):3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