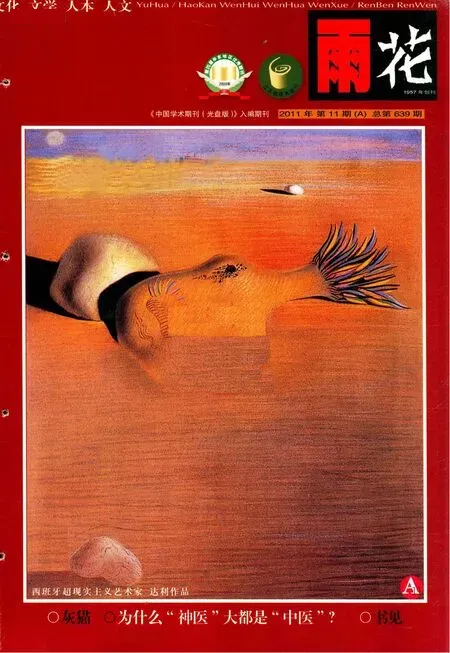《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阅读札记
● 席星荃
关于肉欲
郁达夫在1934年评论了这本小说。他说了一段话:“……梅勒斯迫不得已,就只好向克列福特辞了职,一个人又回到了伦敦。刚自威尼斯回来的路上的查特莱夫人康妮,便私下和梅勒斯约好了上伦敦旅馆去相会。肉与肉一行接触,她也就坚决地立定了主意,去信要求和克列福特离婚,预备和梅勒斯两人去过他们的充实的生活。”
我怎么感觉这里头有一颗钉子,就是“肉”这个词儿。在我们这儿的词汇里,“肉”就是“肉欲”,就是西方人说的性欲或性事。但西方人说性/欲没事儿,是中性的,就像说萝卜白菜;在我们这里很久的时间里就得小心谨慎了,这是个肮脏、龌龊、下流的私生子,不得不说起它则会涨红一张脸,眼睛低下去。郁氏到底是留学东洋的现代知识分子,敢于用这个词。然而郁达夫先生把这个中国特色的词用在查特莱夫人和她的情人身上,是大大地用错了地方。我们且来听听查特莱夫人(康妮)和她的情人(梅勒斯)在旅馆里的对话:
“我愿意和你一起生活。”康妮说。
“只要你觉得值得,”梅勒斯说,“我一无所有。”
“你拥有的东西比大多数男人拥有的都多。”康妮说,“好了,这你自己知道。”
梅勒斯接下来回答:“我恨金钱的厚颜无耻,我恨统治阶级的厚颜无耻。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一个女人呢?”而康妮则回答:“但是为什么要奉献?这又不是交易。咱们只是相爱。”接着康妮又说:“要我告诉你吗?要我告诉你吗?那个你有而别人没有、能够创造未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那勇敢的柔情,比如说,当你把手放在我屁股上,说我有个美丽的屁股。”
整个第十八章都围绕一个话题——柔情——开展,逐渐深入,最后康妮要求梅勒斯抱抱她,然后水到渠成,才是那场酣畅淋漓的性事。在性的过程中他们一直不曾中断有关柔情的交谈与探讨。
而郁达夫却把这样与性须臾不可分离的柔情挚意归结为一个“肉”字。这个字流露出郁氏灵魂深处对性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郁达夫是留学日本的现代知识分子,但他比留洋更早的“留学”是少年时期的传统文化教育,这是留在文化乡土王国的学习,主要是心的熏陶与习染,他没能彻底逃得开去。一不小心他就说出了那个“肉”字。
然而郁先生没能挣脱它的魅力,他的恋爱史和婚姻波折是当时的新闻。在他的生命中男女情事一直不曾离身,他最早与孙荃结婚,生有二男二女。但结识王映霞后演出了抛妻弃子的一幕。十二年后,王映霞离开他,他又跟相差近二十岁的李筱英同居。后来两人分手,郁达夫又娶了美丽的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在他的生命中,性的美满追求其实是跟他如影随行的,观念很多时候并不与人性或本能的行为举案齐眉。郁达夫历史地、必然地成为了一个矛盾物。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一本被禁的小说,而劳伦斯对它很不满,批评它描写的是“大脑的过敏意识”,是给性抹黑。劳伦斯自己出语惊人,把性说成人类“生命活力的源泉”,“强大、有益、必要”,“当我们通体感到它时,我们感激不尽”,并视为对当代文明危机和精神软弱的拯救。《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把性行为置于深刻的、发自本能的情感的光照之下,让心灵的彩虹为性的和谐架起鹊桥,使性之精灵在爱河之上翩翩起舞,灵魂升华,而肉体欢乐。无论哪一次性事之前,或之后,梅勒斯和查特莱夫人都有许多的心灵的试探,情感的碰撞。他们的性事有时候并不成功,然后成功了,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心灵和情感的呼应有没有成功展开并达成无间的契合。
劳伦斯是新的性观念的开创者,郁达夫是旧的性观念的保守人。郁达夫与劳伦斯,毕竟不同啊!
关于孤独
读这部小说,感受到的人物内心,欢欣是有的,孤独也是有的。就像冬天晒着太阳,向阳的一面身体微微温暖,而背阳的一面却透心凉。孤独来自几乎所有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康妮和梅勒斯。在他俩相互接触之前,这种孤独已然存在于双方的日常生活及其感觉中,在认识之后,甚至在初次的性事发生之后,孤独也仍然没有离开他们的内心。正是这孤独感,形成一股推力,推动着人物,相向而行,走到一起。可以把孤独视为小说叙述的主要动力之一。
康妮的孤独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她就是不安,“由于她与世隔绝,所以不安的感觉就疯狂地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为了逃避这不安,她常常丢下克利福德,“跑过猎园,趴在蕨草丛中。……树林是她的一个避难所,一个庇护地”。这不安使她自己隐隐感到了自己是在崩溃。她在猎园里瞎逛,恍恍惚惚,觉得生活像幻象,像影子,像回忆和文字,“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没有接触,没有联系!”——这最后的两个短句子点到穴位了!不仅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孤立无助,像是处于旷漠大野。
只有孤独才能感受孤独。正是同样孤独的米凯利斯的登场使康妮的空洞得到了暂时的填补。她第一面就问他:“可你为什么这么孤独呢?”“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看看你自己,你不也是个孤独之人吗?”
康妮有些吃惊,她思索了片刻,然后说:“有那么一点点!不完全像你那样。”
“我是个完全孤独之人?”
“怎么?你不是吗?”
于是,她和米凯利斯很快就上了床。然而这是一场错位的上床,因为他们的孤独在质地上是不一样的。康妮的孤独是精神性的,而米凯利斯的孤独则是由社会出身和地位造成的心理型的。所以,那一夜之后,矛盾显现,孤独重回康妮的内心。受到挫折打击的康妮,内心更加痛苦:“自从米凯利斯的事情发生后,她下定决心什么也不要了。……她只想把已经有的东西进行下去:克利福德、小说、拉格比、查特莱夫人的责任、金钱与名声,等等……她要把它们都好好料理下去。爱情和性之类的东西只是果子露!舔舔嘴就忘掉了。如果你心里不牵挂着它,它就什么也不是。特别是性……什么也不是!”
康妮的心声以这样赌气似的激愤的反语来表达,恰恰表明,爱情和性在她的心灵里多么难以割除。但是,仍然是她的孤独使她超出孤独:康妮敏感到了梅勒斯身上的孤独——说也奇怪,康妮的感知仅仅从一段身躯而来——树林深处梅勒斯独自洗浴时的身躯:“她看见肥大难看的马裤褪到纯净、精巧、洁白的臀际,胯骨若隐若现,那种孤独感,那是一个生命的纯粹的孤独,深深感动了她。那完美、洁白而孤独的肌体,它是属于一个独自居住、心灵也孤独的生命的。”
仅仅是一瞥之间,康妮就如此深刻地感觉到了对方的孤独,这是灵魂的感应,是心灵之光的吸附。这导致了两颗心的磁性关系。以后我们还要说到,康妮有能力欣赏梅勒斯的腰臀,梅勒斯也有能力欣赏康妮的屁股,他说康妮的屁股是世界上最美的屁股!
不同的是,康妮要解除孤独,而梅勒斯却要保护自己的孤独。第一次在林中小屋交欢之后:“他怀着几乎是痛苦的心情望着她走开。在他原打算独守孤独的时候,她又把他与人世间联系在了一起。她使他失去了清静,一个想要孤独的人的那一点点苦涩的清静。”新的焦虑和两难选择的苦恼折磨着他。
劳伦斯就是劳伦斯,他在这里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普世的人的心灵的痛苦,写的是人类情感的深邃性和丰富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将如之何也?性这个怪物,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欢乐,可是,几乎它每一回的驾临,在其艳光四射的辉煌之下,也必然同时带来了浓重的恐惧的阴影;它带给当事人以芬芳的快乐,却也在幸福的颤栗中升起了彻骨寒意:世上所有的欢乐,一样也不能少,却一样也不能多。人呵,人,你将永无宁日吗?
孤独的摆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搏斗的过程。在一个极度欢乐的幽会之后,康妮和梅勒斯获得了幸福与满足。然而刚一分手,梅勒斯得到的是更大的痛苦:他残酷地感觉到自己的孤独状态的不完整。他需要她,共享那片刻的完美和安睡。
孤独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孤独又是不同的。从米凯利斯,到康妮,到梅勒斯,甚至那个可怜的瘫痪的丈夫,他不是也有孤独吗?孤独来自不同的人生困境,来自不同的生存感觉,最后到达灵魂深处,生成有力的噬咬,人是无法抗拒的。这本小说里的人物都有抗拒,试图捉住它,摔死它,可是,谁也没能做到。
像一对现实生活中的夫妻,精神与肉体总是矛盾重重,难以建立起和谐;平衡总是暂时的,倾斜总是永恒的。
法国当代文豪安德烈·马尔罗曾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法译本写序,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男女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和作者对他们的赞颂给予肯定。而英国诗人A·赫胥黎把劳伦斯比作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赞扬他对人类生活哲学的贡献。马尔罗有马尔罗的道理,但我更羡慕赫胥黎的眼光。与其说康妮和梅勒斯他们具有反抗精神,不如说那是一种追求精神——追求超越生存压力,达到人性本原的欢乐。
简洁如刀的叙事
劳伦斯这部小说有一种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有时候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比如转换。第三章里写米凯利斯来到,其中写到米氏乘坐一辆漂亮的汽车抵达,还带着司机和听差,写他的衣着,写他的神气,这些用的是男爵克利福德的视角,采用了他的心灵独白式语言:“他并不是……他并不真是……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啊,根本不是他外表所意味的。……成功,这个被称为婊子女神的东西,正跟随在米凯利斯后面。”下一段却是作者的第三人物叙述,然后转为康妮的叙述,再然后突然——我强调的就是这个“突然”——转接对话场面:米凯利斯跟克利福德关于金钱、关于成功的对话。由心灵化、情感化的叙述转入对话描写十分干脆利索,省却了一切时间、地点、场景、氛围的交代,这真像电影里的蒙太奇组接镜头,但并不使读者有突兀之感。
劳伦斯的简洁明快却又奇怪地同细腻具体结合得极好。第二章开头写康妮回到格拉比之初,对失去性能力的丈夫和那种府第生活的态度,是不露声色的,只是暗示“康妮和他相依为命,与他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颇为现代的关系。他受到的伤害太大了,终生残疾给他心灵以极大打击,他无法再轻松,无法再自然。他是个残物。所以康妮充满感情地支持着他”。康妮帮助克利福德写小说,“这使她激动,使她忘我”,至于内心世界,感情世界,作者只是十分含蓄地交代了一下:“除了顺其自然外,她还能怎样?于是她就顺其自然了。”这些闲笔之后,作者直接写到:第二年冬天,父亲在拉格比对她说:“康妮,我希望你不会因为客观原因而不得不独守春闺。”“独守春闺!”康妮含混地答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能?”
接着写父亲也对克利福德说同样的话:“她瘦了……憔悴了。她原来可不这样。她可不是那种干干瘪瘪的瘦沙丁,她是美丽的苏格兰红斑鳟。”
读者透过这两句对话可以具体而细微地感觉到康妮身心的变化,由此而感觉到其情感和精神的隐性疾患。从而省去了正面的直接的叙写,——如果那样写,该是多么困难而又乏味。有了这段对话,才顺理成章地出现后面关于康妮的那些矛盾的描写:一方面她和丈夫一心扑在克利福德的工作上,他俩对这一工作的兴趣日益深厚;另一方面,康妮感到“到目前为止,生活也是如此:空空洞洞”。“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种简洁不仅仅是语言的技巧问题,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智慧。在这本小说里读者常常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定位,失去了情节的轨迹,仿佛空穴来风似的,生动的对话突然出现,比如,第三章写米凯利斯其人,前面好好地交代他的出身,性格,成功,社交和他的务实、机智……突然,作者插入了对话场面:
“金钱!”他说,“弄钱是一种本能。挣钱是人的天性。这是没办法的。……”
“可总得会开始呀。”克利福德说。
“啊,没错!你得进入。置身局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一旦你上了道,就想停也停不住了。”
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场景没有气氛,一切都没有。而且这场对话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没有交代。这场对话消失在康妮和米凯利斯各自的心理刻画文字中。这几页叙事与描写(对话)水乳交融,不显痕迹,特别干净利落,剪除了转换语言,自然天成,而各个人物的性格、心理、其间的关系却在其中表现出来。
出乎意料的政治
我绝对没有想到,在这样一本描写个人私情的曾经名声狼藉的小说里,竟然会看到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宏论,而且,读后你不得不感到书中人物的言谈有些道理,而且惋惜这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政治名著,否则,它产生的作用也许能够减缓人类社会某些可悲的动荡,少走弯路。
这部小说写成于1928年,我不知当时俄国的革命进行到什么样子,那已经过去快一百年了,想想真是太遥远了!但是小说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事,是一帮贵族闲人侃大山侃到的。他们当然开始于性的话题,接着就转移到了布尔什维克,查尔斯·梅,也叫查利的,首发宏论:“……既然感情和情绪也非常明显是属于资产阶级分子范畴,所以布尔什维克得发明一种没有感情和情绪的人。那么单个的人,特别是有个性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了,所以必须镇压。你必须得将自己淹没在更大的事物里,淹没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里。……每一个人都是机器的一个零件,机器的动力是仇恨……对资产阶级分子的仇恨。我认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
这里的关键词是“个性”“镇压”“机器零件”“仇恨”。我不想说什么了,我只是忆起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贫穷落后,封闭,僵化。对于年轻人,那时,我听到的最严重的批判就是给他戴上一顶“个性强”的帽子,我就因为这顶帽子而被拒绝入团。与之相应的是提倡听话,无个性无原则的听话,也就是惟命是从,官方的说法是“甘当革命的螺丝钉”。——螺丝钉不就是零件吗?而且比一般的零件还要微小,还要无足轻重。可是,那时代,你不当螺丝钉由不得你,不当也不行。无论主动被动,生在那样的时代,你就是一颗螺丝钉,被一只无形而不容置疑的手强按在某个位置。
至于仇恨,那是跟斗争紧密相连的,那是斗争的年代,斗争的岁月,伟人的话满天飞,“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天昏地暗,而斗的动力当然是仇恨,没有仇恨怎么办?可以人为地制造仇恨。
劳伦斯在1928年写出了以上的话,这令人惊诧。我想他那时听到了俄国的一些传闻或真相吧。可是,中国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如法炮制,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人难道没看过劳伦斯的小说吗?郁达夫不是老早就写了评论吗?如今,时间过去了近八十年,中国人终于明白了,不斗了,改革开放又过去了三十年,再进一步,懂得了“和谐”的好处了,这已经超越了劳伦斯,超越了当今世界许多现代观念——尽管“和谐”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老词儿。真值得额手称庆!
劳伦斯借人物之口骂布尔什维克,可劳伦斯并不是政治右派,他是小说家,超脱于政治派别之外。你看他,骂完了布尔什维克紧接着骂起工业社会来了,把两者相提并论,借汤米的嘴说:“这也是对整个工业理想的绝好描述。简言之,那就是工厂主的理想,只不过工厂主否认驱动机器的动力是仇恨。”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一下子把视点提到高空,俯瞰人间,超越了狭隘的社会学的视界,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来谈论了,查利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只不过我们给了它一个另外的名字。我们以为我们是神……像神一样的人!这与布尔什维克如出一辙。如果你想既不当神也不当布尔什维克的话,你就必须是人,有一颗心和一个阳具……因为神和布尔什维克是同样的东西,都太完美了,无法是真的。”
这里说的“心”,代表感情;“阳具”,代表人的本能和本性。劳伦斯在小说里一直对所谓的“精神生活”深恶痛绝。这里的心和阳具就是与精神生活相对的,两者互不兼容。布尔什维克也好,工业理想也好,工厂主也好,精神生活也好,都是脱离了人的本性的昏妄,是趋向于神而脱离开人的妄想。所以单身汉汤米就瞧不起自己是个精神生活者,他说:
“请注意,我并不真有智慧,我只是个‘精神生活者’。有智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有了智慧,人的所有部位,不管是便于说的还是不便于说的,就都会活跃起来。阳具昂起头,朝任何真正有智慧的女人问好!雷诺阿说他用阳具画画……他画得美极了!但愿我也能用我的阳具做些什么。”
这里,阳具又跟“真知”“智慧”“创造力”紧密联系了,换句话说,阳具就代表了智慧,是智慧的直接体现。那么,可以反过来说,阳具的高昂,就是智慧的胜利!而“精神生活”却并不代表智慧,而是一种意识疾患,是残缺,是偏颇的生活观念或价值取向。它排斥本能的肉体欲望,正是走向了智慧的反面。
绕了不大不小的一个圈子,我们现在似乎明白了,劳伦斯为什么要骂布尔什维克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他是借骂布尔什维克垫底,宣扬他的性的观念。这部小说既是一部探讨性的观念或者说探讨男女关系深层真相,又把它与人的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完美相联系的作品。所以,《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并不是一部单纯言情的小说,这是意旨遥深的心灵的叹息与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