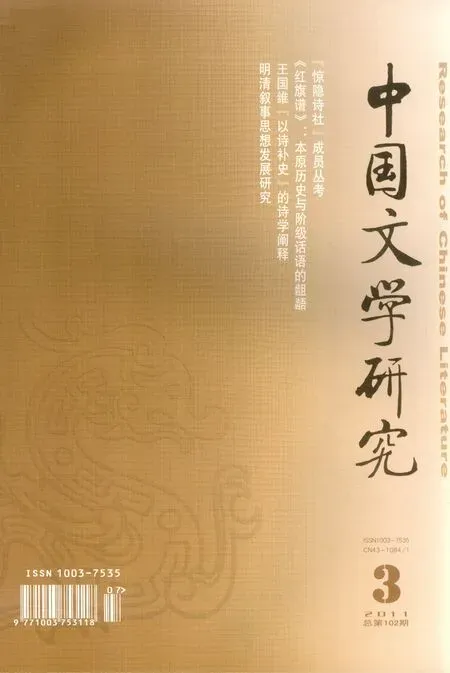老舍影响下“京味”戏剧影视的发展与新变
李春雨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北京 100083)
从历史纵向发展来考察“京味”戏剧的话,20世纪50、60年代,在老舍的影响和带动下,“京味”戏剧初成规模,随后由于“文革”的发生,“京味”文学也随之中断,及至新时期,以苏叔阳、李龙云等人为代表,明显承接了老舍“京味”话剧的传统和风格,不仅使老舍奠定的“京味”话剧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且使这一创作达到一个新的境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时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浪潮语境下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京味”戏剧及影视等不同类型的作品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正蕴含着“京味”文学包括戏剧影视所面临着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一、当代“京味”戏剧影视生存空间的变化
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当代“京味”戏剧影视经历了几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作家创作心态的变化,又有文学样式自身的繁衍,更有时代生活不断的充实与演进。
十七年:老舍“京味”话剧的生成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是老舍作品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当时,不仅老舍创作本身影响力巨大,而且在北京人艺第一代编导演的全力打造下,在确立了曹禺、夏衍的风格后,也确立了老舍的“京味”风格。老舍这一时期的几十部剧作都是在那个“大跃进”、快马加鞭、大干快上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与“十七年”特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空间密切相关。这些作品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结合,体现出那一时代文学作品共有的一些特点。老舍话剧在这一个时期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京味”风格,既有老舍自身生活与创作的积累,同样也有一种个人政治热情与时代精神的契合。老舍是以“穷人”之身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新社会、新北京的文化建设热潮之中的,他“应党之声,应人民之声,应革命之声”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创作为明确具体的社会功利服务。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中,老舍直言相陈:“创作须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老舍十易其稿,最终完成了《春华秋实》,及时地反映了“五反”运动中的很多情况。“赶任务”成了老舍当时戏剧创作的一种特殊的形态。然而,老舍这样一种看似单纯的充满热情的创作心态,其实是很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它既反映出老舍作为一个正直的、充满正义感的作家所具有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同时,它又反映出作家的创作动因与创作效果不都是成正比的,过于冲动的热情如果不是源于自然的创作欲求,有时往往会带来思想与艺术的失衡。老舍这一时期的一些话剧,就明显地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无论如何,老舍的话剧创作在这一时期是逐渐走向成熟的,并在总体上到达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尤其是他的“京味”风格,在话剧创作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炉火纯青的体现,尽管他的“京味”也带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但是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老舍剧作中的“京味”特色与地域风情,是不可能完全由时代或社会因素决定的。虽然时代社会的强势影响会对这种风格特色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特色与风情的根本因素,往往还是作家的个人体验与思想认识。所以,这一时期的“京味”戏剧及“京味”文学,主要是老舍和一些北京地域风情比较突出的作家所创作和形成的,而其他许多作家的创作,可以显现出普遍的政治热情,可以与时代社会形成明显的呼应,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那种特定的“京味”风情是难以出现的。在这里显示了一种时代社会因素、作家个人热情与生活体验等多重关系的复杂存在。
新时期:“京味”戏剧的发展期。经过十年“文革”,及至新时期到来,文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更大的自由空间,文学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得到了加强,时代、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文学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和淡化,这使得包括“京味”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的发展,获得了必要条件和一种新的可能。这一时期的“京味”文学特别是“京味”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一种可贵的自觉发展意识。这种“自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苏叔阳、李龙云、何冀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京味”剧作家及编导演们,自觉地吸取前一个阶段老舍“京味”话剧的风范与影响,在继承和延续老舍风格方面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对老舍的“京味”剧作,从取材、戏剧结构、形象塑造到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着一种接力式的传递;另一个方面,这些新的“京味”剧作家和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创作和编导演中,自觉地形成了新的“京味”风范,他们的自觉意识更多地体现在一种自身风格的形成上。在这一代人的“京味”剧作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老舍的影响,但同时也看到了“京味”戏剧新人的崛起以及他们的不断创新。可以说,从老舍奠定的“京味”戏剧创作到新时期的结束,迎来了中国“京味”戏剧创作的一个真正的新的高度与高峰。
近20年:“京味”戏剧的变异期。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市场大潮的猛烈冲击,全球化语境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大量影视作品的涌现,也使得“京味”话剧在种类、题材上发生了变化。老舍对“京味”戏剧、影视的影响已经不知不觉地溶解在一种多重因素纵横交错的新的语境之中。老舍的风格还在,老舍的影响犹存,但他的存在及影响已经被时代社会的多元化潮流推向一种新的发展态势之中。
新的时代社会氛围在给中国文学包括戏剧、影视创作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空间和发展条件。那种“京味”文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的正宗地位,受到了多方的挑战,各种区域文学风情的互相融合,包括中外文学的更大范围的交融,成为一种趋势。年轻一代编导演对传统的反叛,先锋的、时尚的、实验的戏剧对传统话剧的挑战等等,都使以往比较正统的“京味”戏剧的发展路径不能不随之出现改变。
事实上,电子媒介对传统“京味”戏剧的影响,在上一个阶段即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化和电子化更加迅猛的发展,这种影响愈加强烈地体现在更多的层面,其中包括与电影、电视剧的竞争,更突出的是近年来网络的强劲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子媒介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方式,戏剧作为一种体验式消费受到的冲击更大。以老舍的作品为例,《骆驼祥子》最初由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它的魅力;随后,人们看到了《骆驼祥子》的电影,新的视觉艺术方式,代替了以往人们对作品的接受形态;之后,又出现了《骆驼祥子》的电视剧,在多集的、内容丰富了多少倍的这样一个欣赏过程中,人们以又一种不同的方式在面对老舍的作品。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社会特点,肯定对老舍作品的“京味”意蕴进行了一种改变,不管这种变化使老舍的“京味”更浓了,变淡了,还是变味了。总之,老舍及其影响下的“京味”戏剧在变化着,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变化的力度还会不断加强。
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京味”影视的发展状况。从某种意义上看,老舍当初创作话剧的大众化追求,近年来透过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手段而真正得以实现了。“京味”话剧虽然一直有铁杆的支持者,但作为在剧场里表演的艺术形式,它只能是一种“小众艺术”,其影响面和传播速度远远不及影视和网络等传媒手段。从“京味”电影《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大腕》、《有话好好说》、《洗澡》等的上映到《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家有儿女》等“京味”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以看到,“京味”文学作品正以新的艺术形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而影视和网络又以其特有的功能,不断丰富着、挖掘着和展现着北京生活的底蕴,“京味”文学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态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无论表现手法、技术手段以及生活的步伐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些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依然是那特有的京腔京韵,它们吸取了一些传统“京味”最基本的元素——北京方言、情调、作派、幽默等等,正是这些元素使得“京味”作品大放异彩。比如电视剧《我爱我家》,表面上看是一部典型的“耍贫嘴”式的室内情景剧,它没有什么丰富的情节和深刻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洋洋洒洒数十集就那么几个人物在一个家庭居室里“贫来贫去”,但这部剧在神州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走出国门,从开播起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热播不止!其播出时间之长,演播面之广,在多如牛毛的国产电视剧中是出类拔萃的,它的魅力在哪里呢?说到底就是北京人的那点精气神,就是北京人神侃中的那份幽默,就是北京人特有的那份大度与大气。人们从这里感受到了北京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脉搏,感受到了北京人特别是北京普通市民的那种亲切可爱。而在所有这些当中,我们都能隐隐感受到一种东西的存在——这就是老舍“京味”戏剧的传统。
二、当代“京味”戏剧影视自身的新变
2005年初,《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规定了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其根本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北京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二是要保持和弘扬北京城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一战略定位,既决定了“京味”传统文化在北京发展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又表明了“京味”文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显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的“京味”文化或“京味”文化的传统,在日趋全球化的语境和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面前,明显地来到了一个重新选择的关口。由老舍所奠定基础的“京味”戏剧,在时代社会的新变中同样面临着自身发展中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京味”语言的问题。老舍的“京味”话剧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确立了整个“京味”文学和“京味”文化的重要标志,这是“京味”戏剧在今后的发展路途上所必须坚持的。实际上,无论“京味”文学怎么发生新的变化,包括文学语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语言的“京味”或“京味”的语言始终是包括“京味”戏剧在内的整个“京味”文学的最为显著、也最为根本的一个标志。的确,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和感受到,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以及语言的丰富多变,当下的“京味”戏剧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现象和表达方式。在近年来出现的大批“新京味”戏剧影视作品中,以往传统“京味”作品中的那种老北京底层市民的“贫嘴滑舌”,老字号麻利儿的吆喝,以及老北京见面礼特有的客气的套数话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新京味”作品中充满青春气息的、富有时代动感的那些“京味”的调侃、诙谐和幽默。虽然这些“新京味”的语言与传统“京味”戏剧语言的趣味有了明显的不同,但人们依然能够看到,从传统“京味”戏剧语言到“新京味”戏剧语言之间一脉相承的路数和关联。在此之中,老舍所开创和奠定的“京味”戏剧语言根基、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是如何吸取更加广泛的艺术题材、寻求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以老舍自身的话剧而言,虽然也有对社会现实的表现与呼应,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历史的回顾,是一种来自个人真切体验的北京传统文化情结,以老舍为代表的传统“京味”话剧具有深刻的文化蕴涵,但主要的取材是老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并由此展现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对文化传统的反思,这种文化姿态,对“京味”话剧基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给当今的作家们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文化表现模式。但当今的作家们在新的社会氛围下,必须面对更加复杂的生活情境。随着整个北京城的不断开放,当代“京味”话剧也越来越表现出更加宽容和多元的文化姿态。近年来的“京味”戏剧作品,明显拓展了文化视野和取材范围,既有对北京底层市民生活的继续关注,也有对整个北京城市发展以及各阶层人们的命运的关注,既有对北京文化传统的执著的开掘,又有对北京日益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开放的、多样化的文化姿态的表现,其文化视野和艺术取材,已经从传统的表现方式走向了一个明显的更加开阔的境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代“京味”话剧在文化批判的追求方面,既继承了老舍“京味”话剧的传统,又表现出一种更具主体意识、更富深度的现实文化关注与创作意识,这也是“京味”话剧在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活力的重要原因。以老舍为代表的传统“京味”戏剧,往往以一段旧历史的终结而告结束,对历史的回望和对传统的沉思,构成其创作的内核。如果说,他们是以历史为基点来对文化进行审视,那么,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京味”戏剧作品,则把文化的关注点从历史更多地延伸到了今天的现实,以及今后所要面对的新的生活。如在中英杰的《北京大爷》中,作为历史象征的那座老四合院,已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更重要的,它是北京人现实生存的一个空间,在这里,德大爷及其子女这一大家人,不仅要面对这所老房子带给他们的怀旧、感恩的情结,那种家产代代相传的生存方式,他们所有人,包括德大爷,更多地是必须面对今天、明天应该怎么办。与这个老四合院本来毫不相关的广东人、上海人都神兵天降般地来到这座院落,他们突如其来地介入这座祖传房产的生存与去向问题,不管你北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现实就是如此。而这座祖传老宅的命运,远远不像老舍《茶馆》中的裕泰茶楼那样简单——主人上吊、茶馆关门,一个时代就那样结束了,《北京大爷》展示的恰恰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更加丰富、更加精彩、更加多变的生活在等待着这个祖传老屋及其家人去承受、去应对、去演绎。现实的生存、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新京味”戏剧作品深度关注的核心问题。2000年,根据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全国热播,人们看到了贫嘴张大民这样一个崭新的北京底层市民形象。毫无疑问,从小说作者到电视剧的编导演们,对贫嘴张大民及其所代表的底层北京市民,继续给予了较为深刻的文化批评,对他们某些狭隘的眼光、某些自我满足的心理、某种安贫自乐的心态不无尖锐的揭露。但是,在贫嘴张大民等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了老舍剧作中那些没落贵族的气息,甚至也没有了过士行等人剧作中的那些底层市民的闲情逸致,而更多的是一种面对生存现实的挣扎与奋斗。张大民所关心的一系列生活的琐屑问题,特别是房子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相当一大部分中国人同样在面对、在思考的现实生存问题。《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仅仅让人们看到了张大民这样一个底层市民面对生存困境所表现出来的幽默、通达、宽容的生活态度,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了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进程中,底层市民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而紧迫的生存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仅属于张大民,更不是一个已经远离我们而去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属于我们今天在北京、在中国生存的绝大部分人,这个问题非但今天没有解决,它还在继续发展,还在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明天。或许,这就是《北京大爷》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剧作在思想深度上新的进展,这也是新“京味”戏剧影视的一个重要的新颖之处。
三、当代“京味”戏剧影视面临的挑战
具有深厚底蕴和传统的“京味”戏剧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来自外部以及自身的多方严峻挑战:一是随着北京由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古都日益走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京味”戏剧也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地渗透进了外国文学、文化的因素,如何拿捏好中外融合的尺度,这是一个需要及时应对的题目;二是戏剧特别是话剧的发展,明显地受到来自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等多方面的强劲冲击,如何在这种情势下保持自身的魅力,增强表演性,增强吸引力,使原来相对稳定的院落式、客厅式的基本舞台更加富于变化,这也是“京味”戏剧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三是虽然“京味”戏剧始终有一批比较稳定的观众,但随着“80后”、“90后”越来越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也使得戏剧要做出相应的变动,如何处理好“京味”传统与青春元素、时尚元素之间的关系又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然而,“京味”戏剧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就是它所具有的机遇。事实已经表明,无论是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是以影视及网络为代表的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都不可能完全取代由那些“四合院”、“胡同文化”所展现的“京味”文学包括“京味”戏剧的价值和意义。在影视、网络、“现代化”、“全球化”等强劲的时代新潮面前,“京味”文学包括“京味”戏剧不仅没有走向终结,而且找到了、并且仍在继续探索着自己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首先,北京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进程的加速,使北京传统意义上的“城”与“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为“京味”戏剧的表现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传统“京味”戏剧专注于表现底层市民的命运及北京文化的历史底蕴不同,也与新时期至近年来“京味”戏剧继续关注底层市民的现实生存状态及北京文化的发展变异有所不同,今后的“京味”戏剧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宽容的心态面对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及中国的首善之区这三位一体的新的历史发展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城”与“人”都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时代角色的意义,北京城不再是单纯的文化标志,北京人也不再是传统的老北京味十足的北京市民。作为今后“京味”戏剧所要表现的主体形象,“北京人”将是一个多元并存的复杂的组合体,包括不断增加的中外新移民,包括在北京“漂”着的各色艺术家,包括在北京流动着的百万务工大军,这些人群将不同程度地成为今后“京味”戏剧新的描写对象,有的甚至可能成为新的创作主体。这不仅不奇怪,而且是有根据的。当年老舍笔下的祥子,不就是一个外来的“务工”青年吗?老舍在那个小小的“茶馆”里,虽然以底层市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不是也集结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吗?新时期以来的“京味”戏剧,不是也逐渐拓展了对北京人描写的艺术视野吗?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北京“城”与“人”的发展和变化,“京味”戏剧在故事题材和人物描写等方面都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其二,当今语言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多种地域性语言,甚至包括外国语言对传统“京味”语言的冲击,虽然影响到所谓传统“京味”语言的“纯正”,但是,“京味”语言对上述多种语言的吸取和演变,同样显示了“京味”语言的魅力和张力。这一点在最新的“京味”戏剧影视中有突出的表现。比如近期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家有儿女》,其中成人的语言、儿童的语言、社会的语言、家庭的语言都混杂在一起,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语言表现力和感召力。但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在某些地方最能出彩的仍然是和“京味”相关的那些语言要素和话语表达方式。这一点,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三,传统的“京味”文学包括“京味”戏剧,它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有一种独特的情调,这种情调是和北京传统的城市文化、人文素养密切相关的,这个特质显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展现出新的景象。但在这种变化中,“京味”戏剧寻找到了合情合理的发展方向,把老舍开创的“京味”戏剧的特有情境,引向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境地。这就是说,不管北京的“城”与“人”随着时代社会怎样的发展变化,北京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居民,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调、文化品位,总是在发展中世代相传的。比如,越来越多的胡同和四合院被一座座高楼大厦和一条条宽阔的马路所取代,以往老北京的那种邻里之间,乃至一个四合院里大家族之间的亲情关系,可能就此消失了,但是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城当中,又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社区。在社区里面,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交往与交流,社区文化代替了胡同文化。而在新的社区文化中,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景象,却同时也保留了许多老北京的文化传统,北京的社区建设甚至包括老年社区,都特别注重文化品味的建设、文化气氛的营造,这些永远使北京保留着自己的情调,而这些也必将成为今后包括“京味”戏剧在内的“京味”文学呈现自己鲜明特色的重要的文化底蕴。
总而言之,“京味”戏剧不会走向终结,它正在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走上一条更加广阔的发展之路,而其间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老舍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