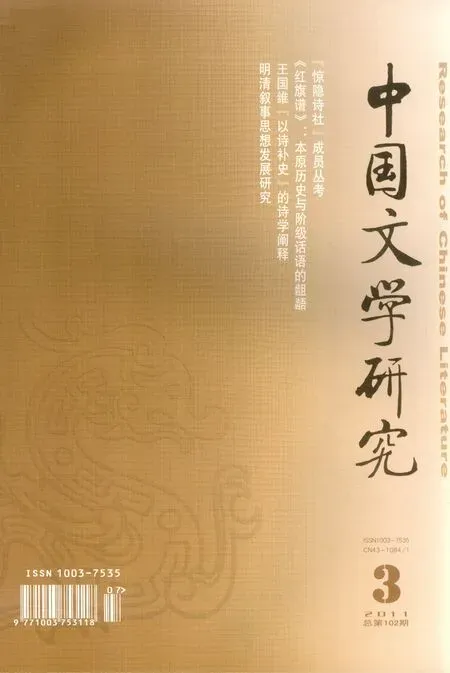中国古代渔樵文学“材与不材”思想辩证研究
殷学国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材与不材的思想命题出自《庄子·山木》〔1〕,在《逍遥游》和《人间世》中亦有相关的论说,亦可表述为“木雁两难”。清人田雯《春日十首》其一:“才与不才兼木雁,隐能终隐伴渔樵”,是对此思想命题的诗语表达。其中,“才与不才兼木雁”表明了诗人自处的生命态度,“隐能终隐伴渔樵”则将归隐渔樵作为这种生命态度的实践路径。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语象,渔樵成为历代文士回应时代问题和抒写情性的象征和意象。渔樵意蕴之丰富复杂恰是文人心态之曲折幽深的表征。在渔樵文学中,材与不材命题包涵三层意蕴:士人的自我定位、作为“他者”的工具价值和全生的生命祈向。〔2〕下面分层述之。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诗中虽无“不材”之类的语词,但以“不材”自处的意味十分明显。渔樵文学中,士人常以“甘分”渔樵表达自处“不材”的人生定位。
欲效微才今未用,沧波甘分钓鱼翁。(陶安《壬辰清明日,客有携酒城东,邀陈致中、谢行可、程子舟、马希穆及余游月盘洞天,偶遇张文泰,遂同饮欢甚。行可,以老杜清明二诗次韵纪事,因就韵赋。》)
我本渔樵徒,世乱甘贱贫。(蓝智《有作》)
自有平生烟水分,何曾轩冕视途泥。(陈献章《晚酌示藏用诸友》)
一、自我定位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隐逸之士多以“不材”自居。〔3〕杜荀鹤《自叙诗》:“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宁虽然三位诗人或因不遇或避世乱或出于性向,原因多样,但自处闲散则一。
不过,“不材”仅为表象,士人隐处渔樵者胸中自有一番“经纶”。但世人不知,常以庸常视之。华岳《狱中责廷尉》“堪笑苍生无眼力,不知豪杰在樵渔”句表达出对有材而遭构陷的愤慨。诗中“豪杰”乃有材之士,“樵渔”为“不材”之位。以有材而居不材之位难免遭受“戕害”,可见以不材自处并非全生之万全之策。诗中隐含着“有材者居其位”的政治诉求,但有材之士又如何由不材之位中挺拔而出?
鞲鹰敛六翮,栖息如鹪鹩。秋风飒然至,耸目思凌霄。英雄在承平,白首为渔樵。匪无搏击能,不与狐兔遭。长星亘东南,壮士拭宝刀。落落丈夫志,悠悠儿女曹。(杨基《感怀》)
“英雄在承平,白首为渔樵”句一方面道出“时势造英雄”的人才观,另一方面指出英雄由潜在向现实转化的社会条件——乱世。不过,为成就英雄和功名事业而致天下苍生于刀兵水火之中的观念,实属中国文化中的异端,乃纵横家之术,而非传统士人的入世路径。中国文化所表彰的是那些无意功业、为拯救天下苍生而出山、功成身退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因结束乱世、开创一代文明而被奉为英雄。
如上所述,那么甘处渔樵、以不材自居者的价值何在?士人的“不材”定位,不仅隐含着其处世之道,亦包含着其价值诉求。
隐居求志随所乐,不在渔樵即耕凿。……尊居万乘不可屈,子陵当年年耕富春。(李昱《题叶叔亨南溪耕隐》)
应门僮仆能延客,旁舍渔樵竞卜邻。莫羡夔龙扶圣代,总输巢许得天真。(薛蕙《早春南园作》)
由薛、李二氏之诗可知,以不材自处者能“随所乐”、“得天真”,而“天真”、“快乐”〔4〕的背后则是置身于社会规范和秩序之外的自然和自由。相对于社会所带给人的规训和教化,天真和快乐体现了为人的目的性和心灵解放的功能。不仅如此,“不材”的自我认同还体现了维护人格尊严的自觉性。
不向长安饥索米,那知回首羡鱼竿。(施闰章《题枫江渔父图为徐电发检讨》)
暂离城郭无多路,便觉渔樵地位尊。(余京《秋杪登清宁道院与漪亭学庵同赋》)
施诗谓权门干求营贷不如江湖闲适自足,余诗认为红尘纷扰有损渔樵尊严。以上二诗皆于渔樵与朝市的对待关系中窥见自处不材对于维护主体人格尊严的意义。一般而言,个体相对于他者的尊严来自自身的独立性,而能否独立取决于个体是否为他者的所用。正是由于严光不为光武所用,才换来光武“不能下汝”的感叹,〔5〕帝王之“不能下”正见出严光人格尊严相对于政治权势的高贵。从这个层面而言,材与不材则意味着有用或无用。
二、工具价值
从逻辑关系而言,有用无用之辩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物相对于他物的工具效能和对于某种行为的价值判断。
莘野凄凉渭水遥,事功无复在渔樵。但令一第先余子,自可清名动圣朝。(刘宰《勉王甥》)
试问乘轩遮道客,何如归去狎樵渔?(吴芾《如老堂》)
刘诗谓时世不同,渔樵于今日意味着不材无用,只有通过科举入世才能实现事功目标;吴诗认为与世俗权势相比,归处渔樵对主体具有更大的价值意义。从二诗可见,工具效能和价值判断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一物只有入世、为“他”所用,方能实现其价值、达致外在价值目标,但不为世用又具有养生和畅神的内在价值。有用无用除了个体的自觉定位和价值选择之外,尚为社会因素而左右——身逢暴君无所用材,而太平盛世则不必求用。
千古感说难,逆鳞不可调。所以商山客,倏焉托渔樵。(王世贞《读史有感二十首》其四)
生逢尧舜功名薄,迹混渔樵计术疏。(黎民表《和公实燕台感秋》)
王诗谓身逢不可以调鼎喻说之暴君,有材而无难以施用,不如全身而不求用;黎诗谓太平盛世,无所用其材,无所用其材正见出天下太平无事。“渔樵无事官无逋,民不识吏亡追呼”〔6〕与“画出江村太平意,渔樵无事岁丰登”〔7〕二诗句所表达的亦是无事太平之意。当然亦不乏自托不材以求仕进者,如耶律铸《嘲渔父》所谓“若为逃世网,却记钓名钩。自是惊飞尽,群群海上鸥”,诗中之“不才”表现只是一种策略,里面包裹着机心。
正是由于所处时世不同,有材之士的用世表现亦有所不同,但这种表面的不同之中亦有其相通之处。赵汝鐩《出处辞》:“太公严子陵,皤然两渔人。文王尚西伯,光皇已中兴。太公所以竟卷饵,子陵所以归垂纶。趋向固异辙,出处同一心。当日遭逢傥易地,两翁亦必随时而屈伸。钓台高兮渭水清,或隐或显俱彰千古名。”姜子牙和严子陵分别代表了历史上有用于世和无用于世两种人格典型。二人都曾渔钓,都曾与帝王遭遇,后世都享高名,此二人之所同。吕尚垂钓待文王,严陵垂钓避征召;吕望出而天下平,严陵天下平而出;吕望封地为诸侯,严陵寂寞守高台,此二人之所异。诗作的重心在于指出二人的共通之处——“出处同一心”。此“一心”系指二人之出处用心。赵汝鐩会得此心而不言,后人未曾会心则质疑严陵之用心〔8〕,至近人蒋智由始明确点出其用心所在。
羽翼风云天下安,幽人秋水渺无端。磻溪烟雨桐江月,今古乾坤两钓竿。(蒋智由《两钓竿》)
吕望、严陵或出或处,二人用心非为一己功利,亦非为一家一姓之权位,而是为天下之太平。吕望助文王、武王兴周伐纣,拨乱反正、开创有周一代之文明;严陵乱世不出、治世不处,倡东汉一代之气节,实有以道德维系天下政治一统的潜在作用。“谁信幽居便忘世,渔樵亦自有经纶”〔9〕,时世不同士人用世之具体形态或异,但经纶天下之志未尝泯灭。
由上举严陵之人格范型可知,无用于世亦有经纶天下之用。此亦是无用之用命题的内涵之一。无用之用所否定的是单纯利己的或为他的工具价值,所肯定的是主体自身的、具有终极意味的价值。惟此,无用之用具有不为樊笼所限的超越意味。
吴中烟水越中山,莫把渔樵漫自宽。归泛扁舟可容易,五湖高士是抛官。(黄滔《寓题》)
诗人谓自处渔樵并不容易,归泛扁舟不是对仕途功名的直接否定,而是亲历仕途后的超脱。在这里由仕途到抛官存在着一条具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径路。逻辑径路的先后反映了价值评判地位的高下——仕宦低于隐退,不得已而退隐低于主动归隐。范蠡和张良在中国历史上受到高度评价的缘故即在于此。与此相反,在传统文化中,对那些通过挑拨生事而建立功名者,评价甚低。郑善夫《至日长陵陪祀》:“怅极两京兴废事,小山何意起渔樵。”〔10〕“起渔樵”即征召隐者出仕,“小山招隐”典出自《楚辞》。《招隐》系淮南王刘安为招隐士出仕而作的辞赋。诗句表面是询问宗亲藩王何故要招聚智谋之士出山入世,但深一层的意思是质疑隐士为什么要出山干预人间是非。以上是郑氏上述诗作的古典,而今事则指向燕王朱棣的重要谋臣——姚广孝。姚氏本僧人,法号道衍,帮助朱棣谋划“靖难之役”、夺得天下。〔11〕姚氏行径类似战国之纵横处士,通过挑拨生事捞取个人名利,实为天下动乱之祸首。近人汤鹏《姚广孝画像行》云:“道衍一变古今局,入守缁衣出冠缨。”一谓道衍之行状,出入朝堂与寺庙之间,上朝着冠缨,入寺着缁衣,不僧不俗,不伦不类;二谓道衍立身行事之怪异,按照一般规范,出世为僧道,入世求仕宦,而道衍恰恰相反——入守缁衣出著冠冕。汤诗意在揭示道衍立身行事有悖社会规范,从而表达对任意妄为者的针砭。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而言,材与不材命题所关注的是有用无用之辩。中国传统文化更看重无用之用,强调超出世俗功利的无为,而贬斥任意妄为。无用之用既与有用相对待,又包含着有用。只不过这种有用不是工具效用,而是道德价值之用。
三、全身与全性
“材与不材”命题一方面揭示出人生在世的困境,另一方面意在解脱,在超脱此困境,在全生。〔12〕人之生命有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之别。〔13〕《庄子》所设想的解决方案中“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与“乘道德而浮游”、“物物而不物于物”之间的内在矛盾,其症结正在于以解决自然生命困境的方式来解决精神生命之方法误用,同时也表明了从学理上分疏全自然生命与全精神生命之必要。前者谓之为全身,后者谓之为全性。
在渔樵文学中,全身一方面表现为追求平安的愿望,如王炎《幽怀》:“但使身安岁中熟,敢辞老境落樵渔”,表达了中国普通百姓千百年来的共同愿望——“身安岁熟”;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养生的追求,如强至《侍次陛对已再见春感怀成篇》:“始爱古人轻禄仕,拟将生理付渔樵”,以禄仕〔14〕与渔樵对举,表明诗人以“生理付渔樵”并非仅仅为了全身远害,还有求养生之道、营卫自然生命的考虑在内。二者皆属于生民之普遍愿望。不过,能否全身尚有待于社会条件。
寤寐江湖得暂归,攀条凄绝柳成围。纵然五亩保安石,已似千年悲令威。忧患叠乘家半毁,风骚重主意多违。此身若有承平日,犹愿烟蓑守钓矶。(冒广生《过水绘园》)
诗中水绘园是明末诗人冒襄与当世名姝董小宛栖隐之所。当时,如皋水绘园与虞山红豆馆(钱谦益与柳如是居所)齐名。诗人系水绘园主后人,过先人旧业抚今追昔,攀条、悲鹤诚属当然。可贵的是,尾联点出安身与天下承平的关系,一方面天下承平始能安居,不然的话,颠沛流离、刀兵水火,纵有华厦名园,即使不遭焚弃亦无以安居;另一方面,安身仰赖生资供奉,太平之世始能很好地治生守成,有业可守才能够奉养尊亲。“愿守钓矶”道出诗人守业之愿望,而守业则为安身立命之基础。安身立命诚属传统中国人最根本的愿望,亦属全身之核心的内涵。
从字源的角度而言,生、性同源,在甲骨和金文中尚未分化,均为“”。由此可知,性的本义应指与生俱来的禀赋能为。在这个意义上,全性即包含尽性尽材之意。不过,传统文化并不片面强调尽性尽材,而更强调才性施展的具体情势,认为一己尽性不如天下无事。从心理结构而言,性意味着个体人格,全性即意味着维护个体人格尊严和品节高洁。
卖鱼生怕近城门,肯到红尘污人处。(王恽《清江引为僧永真赋》)
不近红尘就是为了以隔离的方式保全品格之高洁。除隔离之外,全性尚有另一种形式——“逃”。相对于尽性尽材而言,二者皆属于全性的消极形式。
钓水复樵山,逃名宇宙间。(倪瓒《题渔樵友卷》)为什么要逃名?耶律铸《渔父答》认为:“世路披天险,名声足是非。”声名是非不仅危身,亦足以乱性。置身山水林泉正是为了跳出是非红尘,不至于因私利萦怀而汩乱心性。不过,逃名尚为刻意,玩世则不必逃名远遁。罗洪先《秋日玉虚山斋》;“渔父早知从玩世,丈人何事苦逃名”,表现出对逃名与玩世关系的思考。从义理的角度而言,性又指最高的价值原则。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价值原则不是忠孝而是仁义。〔15〕全性系指践仁履义,而践仁履义难免危身。在全身与全性相矛盾时,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毫不含糊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表明了中国文化重精神生命甚于自然生命的价值观念。
虽然践仁履义与全身在实践层面存在着冲突,但并不妨碍士人探求全身与全性的融合。吏隐〔16〕即属于二者融合的一种形态。黄云《林先生官舍新成》云:“混迹渔樵真吏隐,日携吴酒对君倾。”“混迹渔樵”、“日携吴酒”,吏隐既能避免劳神苦形,又因生活淡泊而不至于荣身而害生。吏隐诚然可以全身,但能否全性?
昔居郎曹更宪府,理是渔纶断樵斧。十年吏隐人不知,却道渔樵自今伍。(邵宝《送彭佥宪还莆田》)
诗中谓“理是渔纶断樵斧”虽系喻说,但多少道出吏隐者某些真实的状态——不纠缠具体案牍事务以保持精神的相对超越。功成身退是全身与全性融合的另一种形态,功成对应全性,身退对应全身。
若嫌荣禄早收身,归与渔樵共隐沦。(参寥《访荆国王公》)
男儿老大功须立,晚岁渔樵愿未违。(林弼《题方漳浦自述诗后》)
白发回天粗已了,江湖迟子入扁舟。(汪荣宝《咏史有寄》)
在参寥上人的诗中,收身隐沦仅是一种策略;但在林诗中,功成身退则具有人生设计的意味;汪诗中功成身退由人生模式变为召唤结构,具有心理上的内驱力。在功成身退形态中,全身与全性分别对应人生之不同阶段,具有线性结构的特征,而无为之为形态则意味着在无为全身的同时,对社会施加影响实现政治理想,〔17〕强调“全身”与“全性”之间的感发呼应,则具有非线性的空间结构特征。黄滔《避世翁》云:“自古隐沦客,无非王者师。”诗中“隐沦客”与“帝王师”对举,正是有见于无为之为的深意。黄仲昭《题睡渔父图》:“莫向江湖轻钓客,太公千古树奇勋”,亦逗出上述旨意。在历史载籍中,严光以人格品节直接影响东汉一代的政治和士风,王通以自己的道德学问作用于门生、进而对唐代政权的建立产生深远意义。〔18〕作为实践无为之为的典型代表,严光和王通的人生实践对后世士人的立身处世具有范式意义。
全身与全性由分指而融合,由自然生命而过渡到精神生命,最终在道德生命中实现统一。所谓“道成肉身”不仅谓理念的形态化与对象化,亦指政治道德理想的以身担荷与担当。在这种担当中实现全身与全性的合一。
四、结语
材与不材命题存在着从自然生命向精神生命和道德生命的逻辑转化。逻辑转化的背后活跃着试图解答如何全生这个问题的精神动力。如何全生即是如何在世的问题。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视野中,人生在世是一个悖论——既是一个不断“文化”、造就和尽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异化、不断戕害天性的过程。悖论源于意义世界的多元并存,悖论表面上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实质上则深化了对生命问题的理解。多元的思想世界不仅为理性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还为在世实践提供了多重参照维度。
〔1〕《山木》:“庄子笑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南华真经:卷七〔O〕.四部丛刊初编子部.
〔2〕《说文解字·木部》:“材,木梃也。”徐锴注:“木之劲直堪如于用者。”《正字通·木部》:“材,木质干也。其入于用者曰材。”从上面的说明可知,材与不材首先是一个与生偕来的、既定的事实,亦即所谓的“禀赋”。其次,还是一个有用无用的问题,入于用者曰材,不入于用者为散木。最后,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并非有用材木的所有部分都是“材”,其用于自身营卫的枝条、根株部位就不堪于用,只有枝干部分才谓之“材”。文字意义的解说未必尽合乎庄子原意,但材与不材命题本身亦是一个在后世的解说和使用中意蕴不断丰富的过程。
〔3〕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不才”即是隐处江湖草野的士人对自己身份、地位自我定位和评价的宣言。见陈贻焮等编.增订注释全唐诗〔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255.
〔4〕中国文化传统中,“乐”有孔颜之乐和濠梁之乐的区别。前者来自道德的自足感,后者来自观物的体验。濠梁之乐又有惠施、庄周之辨。惠施所强调的是身体的幸福感,庄周所强调的是由形式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后者具有共通的基础,而前者只能独享、无法共通,此乃濠梁之辩的关键所在。
〔5〕见《高士传·严光》和《后汉书·遗民列传·严光传》。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下〔O〕.文渊阁四库本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5-966.
〔6〕详见陈棣《钓濑渔樵行送严守苏伯业赴阕》诗。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全宋诗(25)〔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017.
〔7〕详见方回《题王起宗小横披水墨作工密势》诗。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全宋诗(66)〔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1815.
〔8〕郎瑛《七修类稿·诗文类》著录宋人题严子陵诗云:“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岂是钓鱼人;当时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处寻?”此诗之问昧于严陵之用心。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严光之不事光武,以视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弗获已而废君臣之义者也,故子曰:‘隐者也。’隐之为言,藏道自居,而非无可藏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乱,继汉正统,修礼乐,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贤者以道赞襄之,而光何视为滔滔之天下而亟违之?倘以曾与帝同学而不屑为之臣邪?禹、皋陶何为胥北面事尧而安于臣舜邪?”王氏之言有为而发,责严陵之行而意在惩明末空谈心性、不治事功之弊,恕之可也。不过,严陵之行为毕竟与沮溺之辈不同,沮溺劝阻、嘲讽济世之士,而严陵则自行其是,并不是己非人。如果说沮溺是狷狭之流,而严陵则狷而不狭。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17.
〔9〕详见陈著《出门寄弟睹子得》诗。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全宋诗(64)〔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209.
〔10〕文渊阁四库集部王立道《具茨诗集》亦收录该诗。王氏诗集曾为后人补录,复遭馆臣删汰,亦非本来面目。王氏集中亦收录和诗,该诗阑入的可能极大。且王氏小郑氏二十岁,王氏1535年始中进士,官翰林编修,不与陪祀之事,而郑氏1518年已任职礼部员外郎,参与仪制、祠祭诸事,与该诗题目相符。
〔11〕《明史》卷一百四十五:“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為第一。”张廷玉等.明史(13).北京:中华书局,1974.4080.
〔12〕高启《偃松行》云:“明堂屡兴不见取,得全正爱同支离。”是诗有见于不材与全生的关系,而未及见有材与全生的关系。不过,对于材与不材命题所隐含的全生意识仍是有所发明。高启.大全集.文渊阁四库本,1230-119.
〔13〕关于身与性的区别以及全身与全性的关系,乾隆对欧阳修《伐树记》的评点曾有所论及,“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尔,岂曰身之云哉?性全则身亦全,忠烈之士陨身沟壑,然而全受全归也。身全而灭其性者,入于禽兽之路矣,身又奚论?抑又闻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彝伦攸叙,斯尽矣。……若夫郁结轮囷于山巅涧澨之间,猿狖之所号,狸狌之所居,以此为不夭斧斤,抑知此正所以为夭哉。”(见《御选唐宋文醇》.文渊阁四库本,1447-503)乾隆所谓身系对自然生命而言,所谓性系对人伦关系而言。全性即是尽人伦之责任,深层的含义就是尽忠尽孝,与笔者所谓精神生命尚有距离。不过,其论述对于笔者的思考不无启发意义。
〔14〕禄仕,为禄俸而仕、不求行道。《诗·王风·君子阳阳序》:“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郑玄笺:“禄仕者,苟得禄而已,不求道行。”孔颖达疏:“君子仕于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为禄食而仕。今言禄仕,则是止为求禄。”可见,从动机而言,禄仕是为了全身远害;从实际效果而言,仅止于得禄而已。见毛诗注疏〔A〕.唐宋注疏十三经〔C〕.北京:中华书局,1998.98.
〔15〕忠孝是传统观念中的道德规范,而非道德原则。忠孝不能两全所表达的就是道德规范间的冲突,如何裁决当以道德原则为尺度。忠合乎义的原则,而孝合乎仁的原则。二者不能两全时,尽忠的行为若同时合乎仁的原则,则取仁;尽孝的行为若同时合乎义的原则,则取义。如果在义理层面不能区别、判断时,则需依赖策略性的人事安排来解决这种冲突。古人于兄弟中常留一人尽孝,其余尽忠,如文天祥即是一例。
〔16〕从语源而言,“吏隐”最早出现于唐人宋之问《兰田山庄》诗,“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为农且用天。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独与秦山老,相欢春酒前。”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和实践模式,则大量出现于魏晋之际。吏隐者,身居衙曹、别有怀抱而无所作为,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谓之为高士。
〔17〕价值原则是政治理想的抽象,政治理想是价值原则在设想中的具体化。
〔18〕礼赞严光的诗作不胜枚举,且易见,不赘述。元好问《闻崇安县学立碑》诗有句云“礼乐愧河汾,兴唐竟谁予?大隐堂前水,滔滔自东注”,所表彰的正是文中子兴唐的巨大功绩。见顾嗣立编《元诗选》,文渊阁四库本,146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