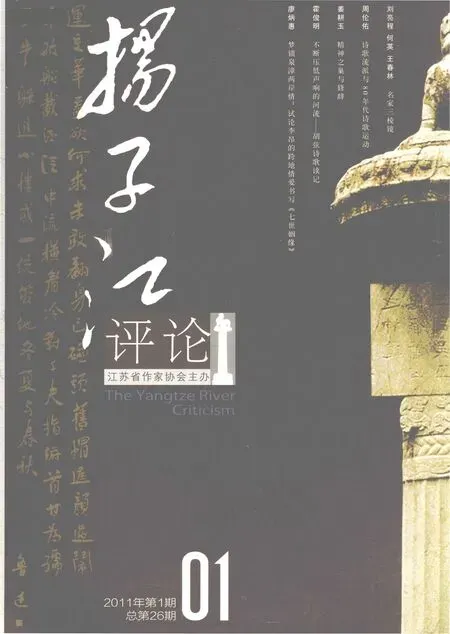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
——胡弦诗歌读记
霍俊明
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
——胡弦诗歌读记
霍俊明
在写作和批评都失范不堪的年代谈论诗歌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总有一些诗人属于让我有话要说的部分,这其中就包括胡弦。胡弦的诗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南方的河流,很少惊涛骇浪和泥沙俱下,而是呈现出当下时代诗人少有的宁静、自足和不断试图倾听、回溯、发现和创设的可能。这是一条不断降低声响的河流,它虔敬的姿态使得现实和想像都获得了共时呈现的广阔空间。胡弦诗歌的安静质素又是特殊的,准确地说是一种“怪诞”的安静。胡弦的诗歌无疑首先是生发于隐秘的内心深处的“教堂”,当然这种内心的呼应也同时指向了当下性和“永恒性”,关涉了个体、生存、时间、“现场”、“社会”和历史共同形成的复杂场域。胡弦的诗歌既是具有个性化的“现实”感又同时有着强烈的“超现实“的冥想、独语和“虚构”的成分。
胡弦的诗歌话语方式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有某些启示,换言之诗人用诗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来发声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诗人、诗歌和活生生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和清醒地面对了自我、生命、生存、世界的时候,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黑暗、荒诞、惊悚和困惑的时候,我们是仍然继续前往还是停下来或者折回?而很大程度上胡弦的诗歌恰恰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即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发现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场所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在我看来,胡弦是没有被当下主流的时代写作所限囿和污染的诗人,在胡弦的诗歌世界里最为显豁的事实就是诗人所迎授与拒绝的“个人”生活的核心和边界。胡弦的诗歌相当沉静,沉静的个体呈现的却是诗歌和生存以及历史和传统深处无处不在的各种声音的回旋和深入。胡弦和他的诗歌就像是不断压低了自我声响的河流,他在前进或回旋的途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倾听、回应了河流两岸、河底和上空的各种事物所焕发出的最为本源、最为自然也最为撼人心魄的声响。
胡弦近期结集在诗集《阵雨》中的诗歌呈现出了一个诗人的谱系性和可能性,呈现出特殊的诗歌质地和纹理。知性、记忆和现实性与寓言性相榫合的文本凸现出不无显豁的时间体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的冲动以及对具体或虚拟场景的钻探式的叩问。我似乎看到在南方场域斑驳的时光影像中诗人缓缓走动的身影,看到了一个时间水岸的彳亍独语者,看到了追光关闭之后空旷而黑暗舞台上的无边的寂静。一定程度上胡弦是对“身边之物”投注了尽可能宽广的考察和发掘的诗人,而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他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没有在当下诗歌写作中流行的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赞美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尽管胡弦的诗歌也闪现出了农村、农民、搬运工、市场、股市等当下“流行”的意象和场景,但是这些场景在诗歌中的现身是诗歌性的,它与诗人的既密贴大地又有些“高蹈”性的情感、经验和想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场景上我看到了与生存和现场密切关联的历史性谱系与诗人落寞的情怀,如“纸币里/藏着国家的血压”(《农历九月初五》),“街边,有个电工抱着电线杆,像在交媾”(《交织》),“磨光的石板路,越来越接近穷人的耐心”(《随摄像师航拍一座古镇》),“即便是在隐秘的乡村,仍有/不为人知的力量在作出决定”(《雪中的意杨林》),“昨天的股市中没有新星出现,只多了/几个吞光的黑洞。一场/来自天堂的雪,也不能把汇率和房市中的/尘埃压低。/但它们仍停在房顶、树梢上……/浮动的白仿佛厘清了/万家灯火和天上群星的关系”(《天文台之夜》)。这种“还原”和抽丝剥茧的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恰恰是在多个向度上再现与命名了诗人所经历的生存方式和想像方式。而在当下一个写作如此多元、媒介如此便利的语境之下,诗人很容易跌坠入自我幻觉、日常叙事以及伦理冲动的天鹅绒当中去,很容易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维度的前提下堕入不介入、不担当、不决绝、不抵抗的暧昧与讨巧中来!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而胡弦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感知方式和话语型构,从而展现出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精神寓言和诗歌向度。胡弦的诗歌保留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汉语先锋诗歌的“玄思”、“知性”和“高蹈”的一些质素,但是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胡弦诗歌的“及物性”和“个体主体性”的繁复容留和张力性的拓殖。在最为常见的日常化景象中,诗人首先拨开日常云雾背后的细节和纹理,并进而在这些被凸现出来的细节和纹理上发现和关注着更为重要的过程性意义。诗人和诗歌的现实感显然不是来自于书本知识和国家主流话语非文学力量的规训,而是来自和生发于实实在在的平常而细小的景物和细节之中的及物性的真实感和“现实”感,所以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岁月的真实/来自个体对庞大事物的/微小认识”。正是在此意义上,摩擦和冲撞更能使诗人具有真切超拔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所以胡弦能够在水龙头、旧衣服、候车室的椅子、嘎嘎作响的房梁等这些“日常”事物面前发现诗歌的“现象学”,“旧衣服的寂寞,/来自不再被身体认同的尺度。/一条条纤维如同虚构的回声,/停滞在遗忘深处。/在镜子里,我们不谈命运;/在酒吧,那个穿着线条衫的胖子/像在斑马线里陷入挣扎的货车。/长久以来,折磨一件衣服/我们给它灰尘、汗、精液、血渍、补丁;/折磨一个人,我们给他道德、刀子、悔过自新。/而贯穿我们一生的,是剪刀的歌声。/它的歌开始得早,结束得迟。/当脱下的衣服挂到架子上,里面/一个瘪下去的空间,迅速/虚脱于自己的空无中”(《更衣记》)。这些“存在”的事物长期被悬置和忽视,只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境之下它们才得以重新出现,这些在场的缺席者恰恰应该是由诗人来予以重新擦拭和完成的。但是看看博客时代的诗歌写作和同样泛滥流行的题材化写作,在高分贝的个人化叙述和国家话语美学的双重合唱声中,我看到的却是不断被悬置和流放的“现实”,看到的是更多的事物、场景以及人心被淹没在物质化和功利性的后工业时代的诗歌粉尘之中。而胡弦恰恰是在时间性上关注着“身边”之物,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梵高笔下的农鞋。在这些悬置性和省略了过程意义的老旧事物面前,虚空、劳累、变动、磨损、消耗、拉扯、挤压、撕裂等这些词语一起呈现了诗人情感空间的共时性。生存与时光洒下的盐粒不能不让敏感的诗人感受到一阵阵的疼痛。
在这些诗歌中我听到了久违的生发于个体主体性和现场以及想象性场景之间冲撞的诗歌的闪电和更为持久和富于膂力的声音。诗人也因此在一个阅读、写作和批评看似自由实则失范的年代里让词语和想象力同时得到“获救之舌”。在这条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中,在不断的躬身向下探询和精神头颅的仰望中,我不断听到真正的导源自自有万物以及生命骨骼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响声。然而这种可贵的声音诗学却被喧嚣狂躁的不断加速度前进的列车遮蔽和碾碎,而只有诗歌和诗人(少数意义上)能够淬炼出对话和盘诘的耳朵与心脏,“只有在火车上,在漫长旅途的疲倦中,/你才能发现,/除了火车偶尔的鸣叫,这深冬里一直不曾断绝的/另外一些声音:窗外,大地旋转如同一张/密纹唱片。/脸贴着冰凉的玻璃,仔细听:/群山缓慢、磅礴的低音;/大雁几乎静止的、贴着灰色云层的高音;/旷野深处,一个农民:他弯着腰,/像落在唱片上的/一粒灰尘:一种微弱到几乎不会被听见的声音”(《窗外》)。我不知道诗人为什么叫“胡弦”,我不知道是一种因为诗歌对话产生的巧合还是我的主观臆想,我不无惊异地发现胡弦诗歌中的几乎无处不在的诗歌的声响(还包括一些事物的“失声”),这种特殊的声音诗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我们进入一个诗人以及文本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胡弦的这些诗歌的各种频率和调性的声响仍然挥之不去,当然这些声音有些是具象化的,有些则是象征和隐喻层面的,如老人在朗诵的声音(《下午四点》),诗歌中不时闪现的独语和对话的声音(以引文的形式出现)、河水的流逝声、钟表的滴答声和嗡嗡作响的换气扇(《搬迁》、《比喻》、《时钟一直在安静地走动》、《旧胶片》),磨损的曲子(《舞蹈》),琴声、刹车声、风声(《交织》),汽车发动的声音(《晨》),卖花声、车声、餐馆里的喧哗、蓝(花)鹊和鸟的叫声、悬铃木的铃声(《礼物》、《林中》、《明故宫遗址》、《有些事确实发生过》、《描述》、《夏夜》),雨声、深涧的水流、诵经声、吟咏声、露水的滴落声、钟声(《晚雨》、《初冬》、《牯岭》、《雨中》),无声奔流的江水(《随摄影师航拍一座古镇》),蟋蟀的歌唱(《路》),洋镐的声音(《冬日黄昏》),眼神的噼啪声和“没有声音的说话”(《素描》),失传的琴音(《弹奏》),撞钟的声音(《夏日》),水声、涛声(《江堤》、《山谷》、《瀑布》),哭声(《黑夜之歌》),风声(《鸡鸣寺》),树叶声(《春天》),弹奏的曲子(《二月》),说话声(《谈话》),椅子的嘎吱声(《候车室的椅子》),搅拌机的声音(《山西潞俯瞰》),嘎嘎作响的房梁(《方式》),火车的吼叫声(《经过》),打雷声(《河水》)……这些光影声色的交响和繁复的声音的不绝于耳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诗人的感叹——“世事沧桑话鸟鸣”。各种来路的声音显示了世界的如此不同和体验的差异,它们共同弹响了诗人历久弥新的敞开的胸怀。
胡弦近些年的诗歌始终坚持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又不乏戏剧性、历史性、想象性的同时寓含强大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据此诗歌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真实内里以及更为沉暗的个体生存的体验和时间的巨大黑色斗篷下的生命的寒冷和同样寒彻刺骨的记忆。想象力在诗歌中不无重要,但是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缺乏的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因为无论是对于个人的记忆还是对于家族乃至历史化的记忆和想像在中国化的语境尤其显得重要和不可替代。更多的时候不是诗人和诗歌在说话,而是非诗和某种庞大的东西在发言。所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当代诗人返回诗歌源头的一种最为稀缺也最为有效的方式,胡弦诗歌中的“刘集镇”、“公车镇”、“杜楼村”、“古镇”、“庐山”、“废弃的古运河”、“莫干路”、“古祠堂”、“意杨林”、“东风河”、“郭洞村”等体现了这种能力,“煤矸石路上,偶有从徐州开来的班车。每当烟尘散尽/田野上的雪,似乎更白,也比原来更加寂静。/如果多站一会儿,远处,祖父母的坟便依稀可见,/——他们去世多年,当时,已很少被提及”(《记一个冬天》),“这是我感到陌生的安静。/从前,这里有刺槐、塔柿、酸枣、蒿草……/每当有人走过,/会惊动老鸹、黄鼬,或者某只假寐的野猫。/——高高低低的林子,那时为何不觉好?//而现在/也许只有还乡人感到稍稍不安。/严格的株距,来自新的种植法,并非/为旧事物作出的标记。/树干都笔直,它们的成长,看不出有过迟疑的迹象,/万千小枝指向天空。我察觉到,/此中,有我不熟悉的渴望”(《雪中的意杨林》)。
在这些压低声响的河流上你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景象?听到了什么久违的令人动心或厌弃的声响?诗人的河流仍在流淌,这一切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心和语言深处的良知的“祖国”和“母语”的回声,“阳光灿烂,浑黄的水中滚动着沙粒,比往常/更加湍急。/有人取水,洗衣,有人顺着河岸向东岭走去。/而沙粒将在哪里沉落下来?它们微小的身躯里,是否/还留有昨夜的广阔雷声?/……灰青的鹅卵石重又沉入河底,只有岸边的几颗,露着/圆圆的小脑袋。”(《河水》)。
┝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