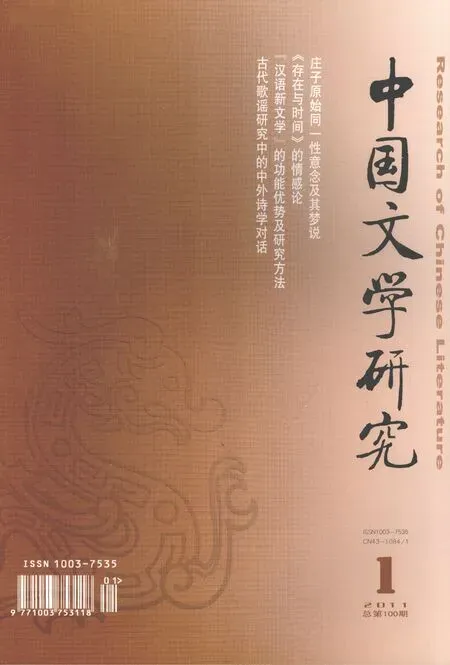论钱钟书早期在文艺观上对五四传统的反思
罗新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是处于新旧文学观念对峙、转化、嬗变的动态过程。在这一矛盾相攻的过程中,钱钟书先生是一位超然观望、理性反思之人,他精湛的西学素养使他对传统文学于中外文学的互参比照中表示批判不予盲从;而他同样渊深的旧学根柢又使他对新文学及其观念在继承与发展的辩证态度下予以怀疑不敢苟同。本文就此展开讨论,以期爬梳出钱氏对启蒙文学传统的具体态度与倾向,显示其独特的文学观念。
一、关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
在近代中国思想界,进化论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每个领域都有人借此破旧立新,文学界也不例外,并且进化论的文学观在众口喧腾的新兴文学思潮中异常响亮。“五四”启蒙主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首先祭出的理论大旗便是进化论。新文学先驱们,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都是以这种洞悉历史前进规律,明了历史进化目标,并以顺应历史进化趋势的智者姿态来倡导新文学运动进行新文学活动的。
新文学的这种历史进化观念到了30年代便成了文学传统,人们在讨论文学历史时自然将其作为理论前提。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就是以这种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来判定历史上的文学复古与逆流现象的。在此书中他说:“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历程中应有的步骤。”“凡是作家,总无有不知新变的,刘昫这样不主尊古,不主法古……这当然因为他是史家。他本于历史的观念以批评文学,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而不为批评界的复古潮流所动摇了。”这种观念不意激起了钱钟书先生的激烈反对。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复古》的批评文章,指出郭先生的毛病在于将“文学进化”与“事实进化”即自然进化混为一谈:“‘事实进化’只指着由简而繁,从单纯变到错综,像斯宾塞尔所说。‘文学进化’似乎在‘事实’描写之外更包含一个价值判断:‘文学进化’不仅指(甲)后来的文学作品比先起的文学作品内容上来得复杂,结构上来得周密;并且指(乙)后来的文学作品比先起的文学作品价值上来得好,能引起更大或更高的美感。这两个意义是要分清楚的,虽然有历史观念的批评家常把他们搅在一起。(甲)是文学史的问题,譬如怎样词会出于乐府,小说会出于评话等等;(乙)才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承认意义(甲)文体的变更并不就是承认意义(乙)文格的增进。反过来说,否认(乙)并不就否认(甲)。‘后来居上’这句话至少在价值论里是难说的。”〔1〕(p504)在钱钟书看来,文学不同于一般的简单事物,它作为人类特有的审美对象自有其独特性、复杂性,是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合而为一〔1〕(p479),所以事实进化是一回事,文学进化又是一回事,事实的进化并不就表示文学的进化,文学的进化在包含事实的进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审美价值的进化。然而审美价值的判断是与人微妙复杂的内在主观世界紧密相联的,并不像一般的自然进化的世界那样有一种以事物的繁简判优劣的客观划一的标准,所以他告诫人们,在谈论文学的进化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简单机械地认定“后来居上”。
不仅如此,钱先生还认为,专就历史事实而言,对于“进化”两字也得仔细斟酌,不能随便谈论,因为,“进化”包含着目标,除非我们能确定地知道事物所趋向的最后目标,否则“我们不能仓卒地把一切转变都认为是‘进化’”,事实是我们并不能确定知道事物所趋向的最后目标,因为据他引证:“即使对天演极抱乐观的生物学家像 Julian Huxley,对于文明的进步极抱乐观的史学家J·B·Bury都不敢确定天演的目标。”所以,他认为,“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郭先生所谓的历史进化观念只是一种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恶来确定‘顺流’、‘逆流’的标准”的个人主义,“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历史观。”〔1〕(p504)
这样,钱钟书在批评郭绍虞先生对文学进化论的理论运用时,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操作性。依他之逻辑,要谈进化,必知进化最后目标,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中又无人能确知进化的最后目标,那么进化的方向也就无法确知和把握,况且文学进化还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无论谁轻言文学进化,都是主观的,非历史的。这样一来,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理论前导的“五四”新文学革命及其革命性成果白话文、新文学就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历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即它们并非如启蒙主义所坚信和论证的那样,是自古以来文学进化的理所当然的目标和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关于“文以载道”与“言之有物”
新文学理论的确立,是从对传统文学观的批判开始的。在这批判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文学观的核心命题“文以载道”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所列第一事就是针对“文以载道”观的。稍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以革命家所特有的激烈之言辞论道:“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2〕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进一步对“文”之与“道”作了切分,他说“古人以为文当‘载道’”,其实,“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3〕五四先驱们对文以载道说反对的同时也提出了言之有物说,所谓物就是指思想与情感;这一主张相比于“文以载道”说,更注重作家的主体意识、内在体验以及文学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因而更加切近文学的本质特征。此说后来自然成了新文学文艺批评之圭臬,新文学作家与评论家衡文论学时往往以之作为衡量写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
然而到了30年代,“五四”的这一“破”与“立”就受到了当时尚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钱钟书先生的深刻反思。1932年周作人先生出版了他关于新文学发展源流的学术专题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在书中周氏将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而且以为这两派此起彼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基本面貌。并且像“五四”其他新文学理论家一样,周作人也是主“言志”而绌“载道”的。对于此种倾向,钱钟书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对之进行了猛烈批评。他认为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与“诗以言志”来分派,失之斟酌,因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谈不上是彼此截然独立的两个派别。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周氏等人扩大了古人“文以载道”观中“文”的概念的内涵,误以“文”为现代文艺理论中的文学之概念,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他说:“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文以载道’中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谓‘文学’”。〔1〕(p81)而且他在《论复古》一文中进一步认为“文以载道”根本就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只是道学对语言文字的基本要求而已,“‘文以载道’只限于道学的范围”。〔1〕(p507)
钱钟书对“言之有物”说也从学理上依据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进行了清醒而理智的辨析。他认为中国文评重内容轻形式,且内容与形式截然判分,失之粗浅:“盖吾国评者,囿于题材或内容之说——古人之重载道,今人之言‘有物’,古人之重言志,今人之言抒情,皆鲁卫之政也。究其所失,均由于谈艺之时,以题材与体裁形式分为二元,不相照顾。而不知题材,体裁之分,乃文艺最粗浅之迹,聊以辨别门类,初无与于鉴赏评骘之事。”〔1〕p487-488
钱钟书认为题材与体裁这种内容与形式范畴的划分只是方便分类,对于文艺欣赏,甚而至于作为评骘文学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则为无稽之谈。因为“自文艺鉴赏之观点论之,言之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同一意也,以两种作法写之,则读者所得印象,迥然不同……故就鉴赏而论,一切文艺,莫不有物,以其莫不有言;有物之说,以之评论思想则可,以之欣赏文艺,则不相干,如删除世眼之所谓言者,而选择世眼之所谓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为文,亦随言而共去矣。”〔1〕(p490)显然,上述理念与其深受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熏陶不无关系,早就有论者指出钱钟书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批评的密切关系。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形式学派从文本本体论出发,激烈地反对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他们认为,必须“中止文艺作品只是模仿(即占有内容)的常识性看法”,而代之以形式主宰一切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文本只是似乎是有内容,或者说内容是文学作品形式的功能,文学作品“说的只是它自己如何产生,如何构成的事情”。〔4〕马可肖莱尔在《作为发现的技巧》中说:“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谈内容就根本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我们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内容即经验与完成了的内容即艺术之间的差别,就在技巧。”〔5〕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到形式主义的重形式轻内容或干脆以形式取代和包括内容的做法,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充分重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和审美性的态度,在实际上克服了传统理论忽视形式的倾向。则又不失片面之真理。
当然钱钟书所论,虽从形式出发,着重强调形式对于文学之重要性,但并没有走向形式主义偏重形式的极端化,他只是针对“五四”过于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评文的偏颇,引起人们对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加以充分重视,而并非忽视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他又说:“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看作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么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所以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1〕(p407)可见钱钟书是注意到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的。
三、关于“无病呻吟”与“修辞立诚”
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钱钟书主张文艺的真伪取决于艺术修辞,而并非以事实的真来断定文学的价值。他拿王充《论衡》里的经典之论作为批评之靶。王充在《论衡·对作篇》里写道:“《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非苟调文饰词,为奇伟之观也。”〔1〕(p488)王充所言被许多谈艺者啧啧称道,而钱钟书却以为,如果单就考镜思想而论,此言自有其道理,如果指文艺而言,“则断然无当也”。因为在他看来,虚实与真伪并非同一概念,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而无真妄之别,显然王充混淆了概念;再者,如果真伪的裁断取决于“世眼”,那么文艺所言,可说都为“世眼”所谓虚实,也就无文艺可言,不过逻辑上也还说得过去;如果取决于文艺自身,那么所谓真妄,就必须视所言之美恶为断,而不能像王充所说,以言语之美恶取决于所言内容的真妄,因此钱钟书认为王充犯了循环论证之弊。
通过对王充的批评,钱钟书自然导出了自己独特的文艺观,这就是颇有几分形式主义色彩的“修辞立诚”说。他以为新文学先驱们所谓“不为无病之呻吟”,“言之有物”只能就作者文学修养而言,而不适用于读者的文艺评赏,在他看来,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词立诚之说也,因而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1〕(p489)这里,钱氏把“能使人信”,即作品的可接受性作为判定真伪,有病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要“能使人信”,读者可以接受,认为“真”,就可以说作者所言也为真,作品也才可以说是佳作。因为,“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疹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的有病与否而已”。所以说,“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非必‘诚’而后能使人信也,能使人信,则为诚矣”。对此他在《谈艺录》中引经据典作了进一步论述:“至遗山《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即词章若自肺肝中流出,写心言志,一本诸己,顾未必见真相而征人品”〔6〕。“写心言志”都“未必见真相而征人品”,由此可见,在钱钟书看来,艺术之真(修辞之诚)与生活之真(所言之物)之差距何以道里计。
休谟曾言:“理智传运真和伪的知识,趣味则产生美与丑和善与恶的情感。”〔7〕钱钟书也曾指出:“逻辑不配裁判文艺。”〔1〕(p238)这都是说,对于文艺欣赏而言,“病”并非可以通过“理智”“逻辑”等理性之力“诊断”出来,而只能听凭读者的审美感受,感受有“病”即是有“病”,感受无“病”,即使有“病”也为无“病”。钱钟书此种“修辞立诚”之说乃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依据形式主义观点对之作了充分的引申发挥,用以批评“五四”文艺理论建构的粗疏与失之严密,应该说进退有据,言之成理,但又不免恃才使气,说话过头,以致有趋向极端之嫌。“五四”所谓“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强调的是文学要依据事实,反映生活,抒发真情,主要是从题材——内容方面来说的,就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造的基础而言,“五四”所论无疑本质上遵循了艺术规律,只不过过分强调却又忽视了文艺自身的审美特性。钱钟书所论正与之相反,在对古代文论否定之否定中体现出背离于“五四”的独特性和倾向性。
四、关于文学的通俗化与平民化
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钱钟书针对新文学惟“俗”是举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惟有一至平极常之理,而并世俊彦佥忽而不睹:夫文学固非尽为雅言,而俗语亦未必尽为文学,贤者好奇之过,往往搜旧日民间之俗语读物,不顾美丑,一切谓为文学,此则骨董先生之余习耳,非所望于谭艺之士!”〔1〕(p491)钱钟书此论对于新文学在俗的提倡中突显的通俗化平民化倾向不满之态溢于言表。接着他表达了自己文学精英化追求:“窃谓至精文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素人俗子均不足与于此事,更何有于平民。”可见在钱钟书眼里,文学乃一高贵殿堂,非一般凡夫俗子能轻易涉足。故他指责当时倡导平民文学的文艺界之所为乃“假借平民,大肆咆哮”。〔1〕(p492)
新文学因思想启蒙而发生,这历史地规定了它的接受主体必然是大众平民,于是文学的审美品格也得大大降低,以适应平民化要求,因此古人那种含而不露,哀而不伤,不愠不火的文学叙事自然显得不合时宜。新文学作家们为了思想启蒙的需要,追求更多的是以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生动叙事来感染人,打动人,以达到教育人鼓舞人的社会效果。如文学研究会作家,从文学为人生的目的出发,不仅要求情感的真,而且要求情感的“烈”,在他们看来,“今日底时代,就是战斗的时代”〔8〕。这种特定的时代状况要求与之相应的饱蓄热情的酸泪的文学,只有这种具有“血”与“泪”的强烈情感的文学才能达到改造社会与人生之目的,可见可歌可泣正是他们“追求”的美学效果。然而钱钟书却从文学的审美性出发,对之大泼冷水,认为文学不是政治选举,不能以感人之多寡断优劣,也得看感人的程度,以及所感之人而定。
钱钟书曾对“俗”有过专门讨论,他认为俗其实是一个事物的数量问题,多数即是俗,他说:“‘俗’的意思是‘通俗’,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价值贱的,照经济常识,东西的价值降贱,因为供过于求,所以,在一个人认为俗的事物中,一定有供过于求的成分,由‘通俗’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特点:俗的东西,就永远是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一种遣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是卡莱尔所谓‘不要崇拜大多数’的‘大多数’,是易卜生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大多数’。”〔1〕(p60)本着这样的观念,难怪他会如此强烈地批评基于启蒙普及目的的文学的通俗化平民化,以及感动大多人的可歌可泣的审美追求。避俗必然求雅。典故是雅的集中体现,也是古人作文的一种最常见的修辞手法,它通过借用故事陈言曲达隐晦幽微的情思,使文章显得古朴、典重而雅致,透露出浓重的精英化贵族化气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本无可非议。但古人用典之风走向极端,凡事凡景凡情都不自铸词造句,而以典故表达,造成文章语意含混晦涩,不知所云,却又难免影响文化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所以以启蒙为指归的新文学的通俗化平民化追求,首先反对的便是典故的运用。而新文学的创作发展也确实遵循了这一文艺原则,很少用典,甚至根本不用典,“老老实实讲话”,以使“别人看得懂”。
钱钟书对此不以为然,他多次为用典辩护。在《致张晓峰》一文中,他指出:“在原则上典故无可非议,盖与一切比喻象征性质相同,皆根据类比推理来,然今日之典故尚有一定之坐标系,以比现代中西诗人所用象征之茫昧惚恍,难于捉摸,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矣。”〔1〕(p409)之后他又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论不隔》里再次强调:“词头,套语或故典,无论它们本身是如何陈腐丑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根据着类比推理来的,尤其是故典,‘所谓古事比’”。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试图将典故陈套语等古典文学手法进行现代阐释,使之获得了现代语境中的合法地位。当然,钱钟书文学审美上的典雅化追求,并非仅仅停留在辩护与倡导上,更贯彻在文学创作上,他的散文、小说,就是仅凭大量使用中西古今各类典故这一点,就可以将之与现代文学主流区别开来。
五、关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学文艺观构成了现代文学文艺批评与理论的主流。〔9〕如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理论,鲁迅“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10〕观点,以及陈独秀“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的思想等等,都是社会学文艺观的具体表现形态。主张“文艺为人生”的文研会主要成员的茅盾更是泰纳实证主义文艺理论的践行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等左翼文艺理论家则基本上操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强调文学是时代精神、社会人生以及阶级意识的表现。
钱钟书曾给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加赛德教授的哲学著作《现代论衡》写过一篇书评,称其为旁观者,因为在他看来,加赛德教授是一个独立于现代主流意识之外冷眼旁观,别有“偏见”之人。加赛德教授以为一个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钱钟书认为这一点“不无道理”,而且告诫那些一般地把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认为是思想或文学造因的人,“尤其要知道这个道理”。从此种“道理”出发,他以为“与其把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不如把思想和文学解释实际生活,似乎近情一些”。如果说“把思想和文学解释实际生活”是因为文学或思想虽高于生活却也体现了生活反映了生活,那么此种讲法与主流的社会学文艺观的差异并不明显,但其试图否认政治制度、社会形式对文学的影响,差异就一目了然了。更有甚者,他根据加赛德“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个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1〕(p139)并且此种“心理状态之所以变易,是依照着它本身的辩证韵节,相反相成,相消相合,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跟随这种韵节而改变方式”的观点,进而认为那些讲时代精神的人颠倒了时代与精神的关系,不是时代决定精神,而是精神决定时代。加赛德的观点从哲学角度看来,无疑是一种客观唯心论,他否认了一般以为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线性的因果序列关系,以为有一种神秘的变易的辩证韵节,相反相成,相消相合,他事他物无以支控。
加赛德的理论,钱钟书融会贯通,将之运用到了文学历史现象的发展沿革的因果解释上来。钱钟书虽不持休谟习惯联想之说,以否定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果联系,但显然休谟的怀疑主义精神对他深有影响,他对人类理性把握事物因果必然规律的能力缺乏信心,他说:“故吾侪可信历史现象之有因果关系,而不能断言其某为因某为果。”基于这种考虑,他放弃了对文学现象沿革所内含着的因果关系的探求,主张“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因为在他看来“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于是在中国社会学批评那里盛行一时的“Taine之书”,在他那里,竟“可为例禁”。这是因为他深感当时的主流社会学批评家,“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从而将因果关系机械化、简单化。在他看来,事物虽有因果和必然,却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探知的。所以他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指出:“不欲言因果则已,若欲言之,则必详搜博讨,而岂可以时地两字草草了之哉!”钱钟书这里显然直接针对的是泰纳的实证主义文艺观,但其对主流社会学文艺观的批评却也是很明显的,因为他根本的主张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平行关系,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因果必然性,他说:“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况,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映射阐发,正可由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较之社会造因之说,似稍谨慎。”〔1〕(p482-483)
总之,钱钟书对新文学主流文艺观的反思与批判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其中既有对其理论前提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的质疑,也有对其具体文艺观点,如关于文学的内容、形式、受众、功用等文学的各种构成性要件的相关理论的逐一批评。如果说钱钟书对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的反思与怀疑,是试图直接抽去新文学大厦得以建立的理论根基,那么他对新文学的具体文艺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就是从微观方面对它进行的具体拆解。这种批评体现出,钱钟书在文艺观上与五四主流的背离。钱钟书对五四文艺观的批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视为是西方现代审美化的文艺观对西方近代社会功利化的文艺观的质疑与反思,它要求文学从沦为思想启蒙工具的附庸角色,回归到自身审美的主体地位上来,这对于深入认识文学的艺术规律,促进文学向现代转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我们不难明白,钱钟书对“五四”主流反对传统文艺观的否定之否定,并非如保守派一样,只是为传统的文艺观念辩护,走向复古的道路,而是要在否定之否定中使文学真正地恢复自身审美之本色,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1〕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2(6).
〔3〕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3(3).
〔4〕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66.
〔5〕马可肖菜尔.作为发现的技巧〔M〕.//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140.
〔6〕周振甫、冀勤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57.
〔7〕〔英〕休谟.人的知解力和道德原则的探讨〔M〕.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3.
〔8〕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N〕.时事新报,1922-08-11.
〔9〕宋剑华、陈剑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31.
〔10〕戴逸主编.二十世纪中华学案:文学卷1〔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