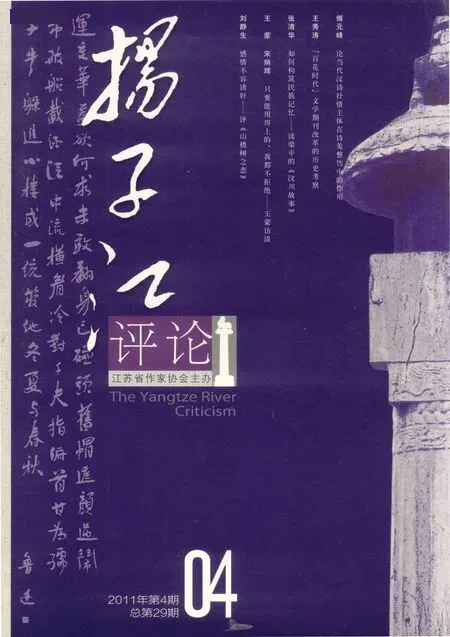新写实小说的叙事镜像与精神症候——一种基于时代语境化的知识考古学分析
郭彩侠 刘成才
伴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化而“浮出地表”的新写实小说,支持着文学研究者关于“纯文学”最后一次天真的幻想。浏览诸多的评论文章,我们会发现,施加在新写实小说身上的是“个人性”、“日常生活”、“零度写作”等一系列被评论者提升到本体论意义上的激赏式语词,这种评论其实是1980年代主流文学观念的延续。主宰着19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所谓的文学自主论,文学摆脱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学自主论之上的文学进化发展观。将文学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关系,这种盲视恰恰忽略了政治无意识对文学的潜在的规训作用。
身处今天语境中的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新写实小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构筑过程中,有哪些知识被不断地遗失和扭曲了,又有哪些知识被忘记或被改写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当代文学之所以会形成今天的这样的局面,是以这些知识和思想的被遗失、改写、扭曲、忘记来作为条件,甚至是以我们对这些知识的残忍来作为代价的,以至于我们后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偏执理解被当做是想当然的,我们从未曾对我们的这种偏执理解加以质疑。但是,我们所要质问的是,这些被遗失与扭曲甚至被改写的知识是不是真正消失了呢?它们是依然作为“他者”继续存在于我们对当代文学的知识理解当中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给转换了角色就藏身在我们的当下理解之中?
文学研究界已经被固化的评论普遍认为,新写实小说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市场经济语境、日常生活叙事、情感的零度写作。①本文将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语境化“重返”式的解读,运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1980年代语境中的新写实小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诉求的认识性装置,通过“重返”1980年代时代语境中的新写实小说,力图揭示出权力、制度、意识形态等对文学与人的规训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规训的隐秘成规。
一、市场经济语境:现代化的权力“镜像”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重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入80年代末期,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转型加剧。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在一片“下海”声中悄悄变化。神圣的革命理想、英雄的启蒙业绩被人们忽视,原来为人们所不屑的“物质”堂而皇之地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则。民众崇尚世俗,沉湎于日常生活的快乐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取代了精神的乌托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不仅表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而且潜在地承认了世俗人生的生活需求高于社会理想。“经济人”取代了“政治人”、“道德人”,个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成为个人的生存意义。现代化为导向的市场经济语境为日常生活写作提供了可能。“‘现代化’在世界各国进入工业社会时具有普遍主义的特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世俗化’。‘世俗化’促使文化日益普及,同时也促使文化日益浅薄。它的弊病在今天也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世俗化’是由工业化带来的传播媒介的变革决定的,也是工业社会为发展自己的再生产所必须做到的。”②
早在1985年的《小鲍庄》和《桑树坪纪事》已显示出了写实小说发展的新趋向。1989年,《钟山》第3期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共8期,发表小说28篇,1991年第3期(为最后1期)后自动取消了该栏目。1989年《钟山》与《文学自由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并发表评论文章。接着《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上海文学》等期刊都发表了成组的探讨新写实的批评文章。这一系列的漂亮“动作”使得“新写实”成为了一个文学史事件。因此,与其说“新写实大联展”展示了创作的实绩,不如说它的理论争论引发了特定历史语境下意识形态权力、现实主义批评、现代主义批评的多重矛盾。
“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自我设计这词儿很流行很时髦,但也只有顺应现实它才能获得有限的收效。常常是这样:理想还没形成,就被现实所替代。”③在日常性和世俗性的“烦恼人生”面前,“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普遍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厌弃,传统文学中对理想主义的炽热与向往,对人生价值和意义进行形而上思考的真诚与执着都被日常性的生存经验、好好过日子的世俗性所取代。小林是单位里的一个小职员,也曾有过宏伟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和热切的追求。作为大学毕业生,他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但几年便很快淹没在普通人群中,终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一地鸡毛》)短短几年,小林由一个有个性、有激情、胸怀远大抱负的大学生蜕变为一个庸俗的小市民,他不再有什么理想,只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刘震云自己也认为“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的不是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于是我们被磨平了……过去有过宏伟的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④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还与市场经济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相关。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学体制产生了强烈冲击。随着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文学传媒(主要包括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机构)不得不面对市场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纯文学期刊的定位也开始越来越向市场和读者倾斜,以期寻求能够立足于世的应对良方。在《昆仑》、《漓江》、《小说》等相继宣布停刊之际,《收获》、《上海文学》、《山花》、《十月》及《钟山》等刊物则把握住社会转型的良机,积极应对市场挑战。为了迎合读者多方面的需求,它们注重杂志的包装与可读性,而在市场导向下,学期刊策划的重要性更日益凸显。“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无疑是文学传媒一次非常成功的操作案例,以至于今天提起“新写实小说”,马上就会联想到《钟山》。正是由于《钟山》在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中着重倡导一下新写实小说,除了以突出篇幅刊登新写实小说(以中篇为主)和理论探讨文章外,还将积极创造条件举办新写实小说评奖活动,筹备出版新写实小说集。“它是一次别具一格的小说聚会,一个精明的办刊策略,一个审时度势之后的文学话题的设计,一个文学批评的利比多宣泄,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成功已经是在当代文学史上记载了醒目的一笔。”⑤
可以看出,市场经济这个现代化的手段对新写实小说的规训主要采取的是采取内在的方式实施的,即葛兰西所说的“认同”,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并非通过外在的控制而是通过内在的“认同”来实现的,而这种“认同”并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建构”。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让外在的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化为你的内在的要求。⑥
对新写实小说要坚持“永远历史化”的原则,把它放置到八十年代特定的中国社会政治语境中去加以理解,考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政治的内在关联。在福柯那里,权力是一个“生产性”(Productive)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来,权力不是某个组织、集体或者个人的所有物,权力渗透于社会的所有层面之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支配关系。权力来自四面八方,它无处不在,正是权力的结合或者纷争才构成了巨大、复杂而纷繁的形式本身,社会机制正是权力的战略形式。按照这样的逻辑,没有一种社会装置能够置身于权力之外,当然也包括“文学”。“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政治。
二、日常生活叙事:意识形态霸权的新神话
关注日常生活,对生活做流水账似的原生态记录,是评论者对新写实小说众口一致的评说,“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诉说世界的原生态。具体地说,就是作家把自己创作的情感降低到零度,以避免作家的主观情感和主体意向的干扰,对生活进行纯粹的客观还原,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实性”。⑦这基本上沿袭了《钟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对“新写实小说”的界定:“所谓新写实小说,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⑧在新写实作家看来,生活“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去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消融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楚道理。”⑨“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⑩
以还原日常生活的理念来看,池莉无疑是最符合标准的。她主要讲述的就是武汉小市民的家常里短和柴米油盐,《烦恼人生》的“镜头”追随着主人公印家厚一天(从凌晨4点到当晚11点多)的生活:“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儿子夜半坠床,清晨不情愿地离开暖融融的被窝,煮牛奶,排队入厕,哄儿子起床穿衣,抱着孩子挤公交,赶早班轮渡,吃早点,进厂门迟到,奖金被克扣,食堂的午饭里吃到虫、下班回家听到住房要拆迁的消息……事无大小重轻,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展开。通过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烦恼、苦闷、矛盾、纷争,几乎与生活同步,展现的全都是原生态的、活生生的世俗种种,而不对之作任何提炼或升华。其实,重要的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原生态记录,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写实小说对这种原生态日常生活的安之若泰。《一地鸡毛》中小林觉悟到:“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暖凉”,“这天夜里睡得很死。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来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新写实小说家甚至自负地认为:“过去强调的是艺术真实,现在则强调生活真实,比过去的真实更进了一步。”⑪
但是,“作家所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中性的,公正无私的;种种权势与意识形态隐蔽地寄生于叙事话语内部,它的唯一任务仅仅是展现事实的‘真面目’。”⑫在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表述之中,恰恰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话语诉求。新写实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正契合了1989年后的社会与文化氛围中对精神困境既敷衍又关注的彷徨心态。这种所谓的原生态日常生活叙事,其实是被写作者“看”出来的,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不如说是本质上的价值观。小说家强行取消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用一种形而上学的“减法”,消减掉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解构理想、诗意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把日常生活提升为“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⑬。
我们今日的重返力图揭示的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政治话语诉求,把握和诠释日常生活神话的文化意蕴及其背后的复杂的权力网络和结构关系。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中的,“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只有在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个人构成主体的这一作用这个范围内,主体范畴才构成一切意识形态。”⑭社会个体常常觉得自己在意识形态的想象关系中仿佛是自主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按照自身的需要召唤、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内化于主体之中,使他并不觉得接受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强加给他的,认为是自己自主选择的。意识形态从而成功地掩盖、扭曲、压抑了人与现实的真实关系,实现了自己的神秘化,这就是詹姆逊意义上的“政治无意识”。
19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原有的价值理念受到冲击,原有的人生信仰失去了神圣的光圈。国人不再盲目地憧憬未来,而是专注于既定的现实,致力于眼下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国人无奈地接受现实,对社会重大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所期求的仅仅是凭借自己的辛劳,管好自家的柴米油盐,牢骚满腹地沉溺于庸常的生活之中,而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期盼的。我们沉迷于新写实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所忽略的正是这种叙事的意识形态性质。“叙事既包含着人们通过叙事表达出来的欲望和幻想,即叙事的对象或内容;还包含着人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即意识形态立场也即叙事的立场。”⑮在这种日常生活叙事弥漫的同时,文学被细节充满,历史没有了,深度被抹平了,历史的动感也消失了,只剩下“细节肥大症”了。⑯
在1980年代中国日益深广的改革开放、进一步现代的社会知识语境中,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并进一步的神化,将日常生活与政治对立起来,等同于所谓的幸福生活,当做一种天然的非意识形态的准则加以接受,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日常生活已经被充分的全球化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完成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借助日常生活叙事制造出暗藏着的陷阱,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在的社会与制度就是历史上最好的社会与制度。意识形态终结了,政治消失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奋斗、去欲求、去爱了”⑰。日常生活成了“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成了“日常生活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s)。⑱
在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语境中,关注个人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写作视角,从来就不曾仅仅是单纯的文学审美选择,它自身包含着丰富的价值立场和浓厚的历史意味,这注定了文学展开日常生活写作的复杂性。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虚构了一种超阶级的、普遍的日常生活。在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中,日常生活成了社会大众的图腾,国家与资本都在其中发现了彼此的利益和各自的合法性,日常生活也就成了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共同打造的现代新神话,引导者大众的社会梦想,拥有了意识形态新霸权。我们此时要牢记左派对我们的警告:“不要忘记日常生活的政治性。”
三、情感零度写作:回避现实的犬儒主义
新写实小说出现时,“主流意识形态有所衰落,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解体,知识分子扮演的启蒙角色已经无力在历史实践中起到实际作用,主体性及其历史神话也已破灭”⑲,人文精英知识分子渐渐丧失了话语权。他们由启蒙者转为体验者,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面临着“失语”的价值危机。“当主流话语的乌托邦许诺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日益遭到人们冷落与遗弃而无奈地退出文化中心之后,在市民文化消解抽象而走向直观,消解理性而走向官能,消解深度而走向平面的价值重估的社会转型期,新写实小说找到了自己的表演舞台,适时地填补了价值真空,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承载体。”⑳“作家放弃了指点迷津式的启蒙导师的立场,只是表明知识分子转变了传统的叙事立场——依赖政治激情来争夺庙堂发言权,以及在知识分子议政的广场上应和民众情绪的个人英雄的立场,而转向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㉑
因此,新写实小说家在创作中力图回避传统的“导师”角色。“作家并不比别人高明,所幸的是作家不必像哲学家,不必自信真理在握才动笔写文章。他可以把包含着真伪美丑好坏的混沌不清而又生机勃勃的生活记录下来,让高明的读者和更加高明的后人去分析评判,成为诞生真理的土城。”㉒“对于宇宙来说,人类不过是个孩子,作家哪里又是什么先哲呢?我一点儿也不认为作家是天降大任之人。我写,只希望能切切实实地与读者一道咀嚼我们的生活,认识我们的生活,享受我们的生活。”㉓让生活告诉你吧!这就是新写实作家所取的态度。王干对新写实的这一特征作了十分精当的评述:新写实作家“在叙述小说时在叙述这个世界时是相当谨慎的,他不敢轻易作出判断,小心翼翼地描述,决不武断地说‘世界就是这样的’,非常保守地留下空白,留下很多间题由读者在阅读时进行‘作业’去完成世界的构成。”㉔
在写作中,新写实作家则把自己的倾向性和价值趋向尽量地隐藏于生活和人物形象之中,使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避免对生活原相过多介入。方方的《风景》、王安忆的《小鲍庄》、刘震云的《单位》、叶兆言的《艳歌》等,对日常琐碎无序的生活和人的心态不作任何主观化的过滤和理想化的升华,客观地、不动声色地呈现人的存状态和生活流程。《小鲍庄》沉滞凝重的、带有偶然性的生活现象,范小青笔下不带主观色彩和观念框架的苏州小巷风情,叶兆言《艳歌》写恋爱、工作、分配、生儿、过日子、闹家庭纠纷等一系列既无悲剧色彩也无喜剧色彩的平淡人生等,这些作品无不以审美态度的客观化使作品呈现出生活的原色。
但是这一零度写作的意图真的能够完全得到实现吗?南帆谈到:“新写实主义的另一个著名的写作策略即是‘从情感的零度写作’。新写实主义希望作家应当放手让人物演出,新写实主义作家取消了热奈特所谓的叙述者的‘思想职能’。他们不想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独立。”同时认为“文学应当在生存的表象后面附加什么,作家应当在种种形而下的骚动后面给出一个精神家园。文学当然有义务告知与揭示现实所包含的平庸。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必须同时具有反抗平庸的功能。即便是反抗不合理的现实,文学的反抗精神仍应保持在艺术的维度之上,存留在审美方式之中。这即是审美与平庸的抗争。”㉕而大量的新写实小说“越来越倾向于表象化,大量描写现实的作品依据个人的直接经验,热衷于表现偶发性的感觉、堆砌感性直观的场景,人们完全忘却历史、回避任何精神负担。”㉖
放弃对人类精神家园重建的努力,放弃个体反抗现实的平庸的责任,完全忘却历史,回避自己的责任承担并进而放弃文学对现实的反抗精神,这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恶的视而不见,并任由这种平庸的恶蔓延。“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们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们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实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在日常的恶中生存就是崩溃。”㉗在恶中生存却对恶视而不见,放弃自己的责任承担,当我们的研究与创作都处在这种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文学以及对文学的研究,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从而让我们为自己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而寻找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对这种充满道德正义光芒的宣称我们要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与怀疑,正如卡夫卡《城堡》中的一个人物对K说,他的一切行动只能从一个十分不同的、远非有利的角度进行解释时,K回答道:“倒不是你的话有什么错,只是这些话不怀好意。”㉘“知识考古学”所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充满道德正义的光芒的宣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种宣称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目的,以及这目的背后的真正的潜意义所在。
【注释】
①《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钟山》1990年第4期。
②胡晓明、袁进:《现代化=俗化?》,《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30日。
③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98年第2期。
④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⑤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页。
⑥[意]安东尼奥·葛兰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收入《文化与社会》,J.C.Alexander and S.Seidm 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 47 页。
⑦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⑧《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⑨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98年第2期。
⑩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⑪范小青语,见《新写实作家、批评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⑫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页。
⑬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 年第 2 期。
⑭[德]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89页。
⑮[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⑯[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⑰[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⑱[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257页。
⑲陈晓明:《剩余的想象——90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⑳赵联成:《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文史哲》2005年第4期。
㉑陈思和:《关于九十年代小说的一些想法》,《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㉒赵长天:《走出梦境》,《中篇小说选刊》1990 年第 5 期。
㉓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98 年第 2 期。
㉔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㉕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页。
㉖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页。
㉗格伦茨曼语,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3页。
㉘[奥]弗兰茨·卡夫卡:《城堡》,赵蓉恒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