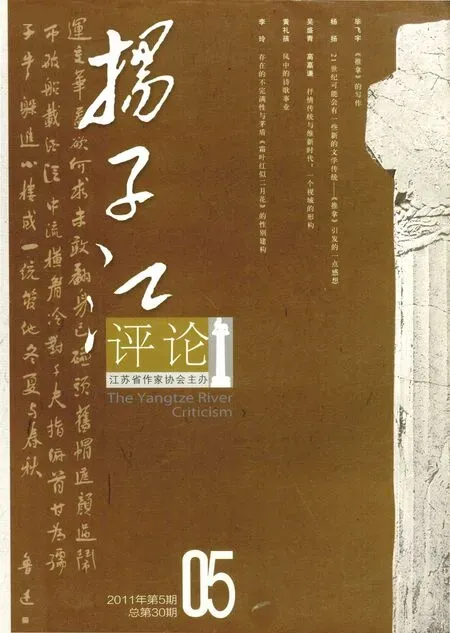救赎如何可能——“女知青回城”题材的书写景象
臧 晴
一
在新时期文学的书写脉络中,十年“文革”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知青题材不仅涉及以“五七作家群”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的身份认同与个体经历,更触及“青年”这一书写母题,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大书写景观。
及至“文革”后期,当年热烈响应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①的一大批下乡知青已被残酷的现实和渺茫的前途惊醒,满腔热血化作昂首盼回城的煎熬与苦涩。于是,围绕着“知青回城”展现了几个书写方向。有的着力表现等待回城的辛酸与无奈,营造出为时代民族牺牲青春的自我崇高感,80年代的文本如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和叶辛的《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的则剥去知青的华丽外衣,揭露了他们为回城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丑陋面目,90年代的文本如王明皓的《快刀》和刘醒龙的《大树还小》;还有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以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姿态书写了手无缚鸡之力、家无半点关系的女知青为回城而被迫“献身”的苦难故事,其中,竹林创作于1979年的《生活的路》②可谓代表之作。
小说中的女知青娟娟在大队党支书崔海嬴的威逼利诱下,背叛了善良正直的老支书,卷入了偷换公有财产的阴谋中,并进而为回城而委身于崔海嬴。故事的最后,以身体换来招生登记表的娟娟因怀孕而丧失了回城机会,在重重打击下走上了绝路。展现女性无奈辛酸的心路历程,刻画胁迫方道貌岸然嘴脸下的险恶用心……《生活的路》从故事情节到思想内涵都代表了当时这一题材普遍的书写模式与思考深度。
突出男性的伪善与胁迫,渲染女性的幼稚与软弱是这一类文本普遍采用的书写策略。正如当时一篇对《生活的路》的代表性研究论文所指出的,“娟娟的年青而短促的一生是一场悲剧。不用讳言,她是一个被邪恶势力迫害致死的悲剧人物。”而悲剧原因在于“娟娟那么年青,纯真,缺乏生活经验和斗争阅历,很缺乏对付这种邪恶势力的防御能力和清醒头脑”以及崔海嬴这个“戴着伪善的面具的两面派”、“革命队伍里的蛀虫”。③这种采用两相对比,以男性之恶与强反衬女性之善与弱的“脸谱化”书写方法实则仍是“样板戏”文艺思路的延续,虽能以字字血泪、凄惨悲怆的力量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但也不出意料地落入“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④的窠臼。
这一自1942年《讲话》奠定的延安文艺模式延续至“女知青回城”书写,已逐步走向极端。反面人物往往甫一出场,其丑恶本性就已昭然若揭。如在《飞天》⑤中,谢政委初遇飞天就“边说边打量飞天”,“两眼还是盯着飞天,又问出了什么事”,并忙不迭地伸出魔爪,表示“要是回家确实有困难,可以到部队当兵嘛”。而正面人物则愈发孱弱无力、渺小可怜,个人的有限性和无奈感被渲染得无以复加。如在《生活的路》中,娟娟对崔海嬴的屈从不单是因为“招生登记表还在崔海嬴的手里,怎么能就这样得罪了他啊”,而且“生活教会了她,使她认识到,无论是谁,纵有天大的本事,就是想在这偏僻的小山沟里,掀起一个浪头的话,不借助社会上的风,也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女知青何以回不了城?为回城而献身的逻辑从何而来?如果说,这种权色交易确是通往回城的有效路径,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青年们又如何体认乃至认同这一逻辑的存在?以《生活的路》为代表的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都没有作出进一步思考与探寻。
这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不但都外表猥琐、无耻狡诈,他们往往还有另一重共同身份——“干部”。无论是《飞天》中的“政委”、《生活的路》中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是《天浴》中的“场部的人”、《岗上的世纪》中的“小队长”,男主人公都纷纷利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赋予自己的官方身份(及所代表的特权),在知青返城的浪潮中换取垂涎已久的女性身体,满足以肉欲为旨归的男权需求。
在这一场场权色交易中,男权话语体系如何与主流话语体系合谋并攫取利益?而女性又如何对此产生认同?作者们往往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似乎这一逻辑是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拷问与探寻,将这一题材置于“少数坏人迫害好人”的道德二元对立逻辑下,以突出个人道德善恶的策略掩盖其背后深重的政治话语乃至社会现实问题。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尽管“伤痕文学”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使人读之潸然泪下,但也仅能止步于此。这种停留在对“革命队伍”中的“个别坏分子”作出控诉与批判的思维使作者往往囿于对具体个人的道德审判,落脚在一己的情感宣泄上,因此缺乏对“人”的深层反思,遑论女性视角的开拓与挖掘、对社会政治的反思与质疑。如果说,这些文本以切肤之痛所揭示出的女知青凄惨遭遇多少触到了五四“发现人”、“尊重人”的“人的文学”的精神传统,那么,其反思力量与问题意识的缺失也决定了其难以回到“五四”的起跑线上。于是,对于这些“失足女性”何去何从、她们的救赎如何可能,这些 “伤痕文学”作品也就往往给不出一个答案。若干年后,一些作品开始走出这一思维困境,尝试着作出探索与解答,典型代表即是严歌苓的《天浴》与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尽管二者的路径与指向截然不同。
二
因怀孕而回城无望的娟娟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她在心里大声责问:起伏的丘陵呀,绿色的青纱帐呀,我的路哪里呢?生活为什么这样的不公道呢?”并一步步走向了河流深处。从表面上看,女知青回城心切,在献身干部后仍夙愿难偿,继而自绝于世,《天浴》⑥中的文秀仿佛是草原上的另一个娟娟。然而,严歌苓摒弃了对女知青挣扎心路的渲染和对男干部以权相逼的批判,转而着眼于展现文秀对权色交易逻辑的认同过程,从而挣脱了对个人进行道德审判的枷锁,进入了对大时代背景的揭露与反思。
对于推动自己命运前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文秀经历了一个从蒙昧到认知乃至觉醒的过程。起初,她将这原因归结于老金个人——他对她的偶然选择,“文秀仍是仇恨老金,要不是老金捡上她,她就伙着几百知青留在奶粉加工厂了。”她一片赤诚地相信着场部对她的允诺,“六个月了嘛,说好六个月我就能回场部的!今天刚好一百八十天——我数到过的。”“你说他们今天会不会来接我回场部?”场部来接她的人久候不至,却等来了真相,“从半年前,军马场的知青就开始返城了”——她被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欺骗或遗忘了。
供销员的出现助推了文秀的“觉醒”,使她意识到自己被主流话语欺骗了的命运。然而,又岂止是场部对她的一个允诺,整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最大的欺骗。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原因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⑦。三天后,《人民日报》社论更将上山下乡运动升格为重大政治思想问题,“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⑧几十年后,当年那一大批“甘用热血洒青春”的知青们却发现,原来十余载光阴的人生沉浮始于一场彻头彻尾的连环骗局。他们用整个青春乃至生命去实践、奉献的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平息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以至难以收场的红卫兵运动,并借此分散社会对城市青年失业问题的注意力。⑨
当然,对这一事实的认知与反思并不在严歌苓的书写范围内,但《天浴》至少已经跳出了对供销员、场部干部的个人道德审判。意识到被主流意识形态欺骗、遗忘的文秀开始奋起反抗她逐步滑向边缘的命运。“逛过天下”的转业军人带来了真相(尽管这真相同样值得怀疑),“先走的是家里有靠山的,后走的是在场部人缘好的,女知青走得差不多了,女知青们个个都有个好人缘在场部。”文秀自知“娘老子帮不上她”,所以“只有靠她自己打门路”。在这个“关系”社会里,没有天然的家庭关系,则唯有靠创造肉体关系——身体是唯一的资本。至此,文本逻辑被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这是一场以男权话语的牺牲品换取主流意识形态关注与垂青的权色交易。
与大量伤痕文学作品反复渲染女知青献身时踟蹰、苦痛的心理不同,《天浴》中的文秀对“靠身体回城”这一潜规则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抵触情绪。对于性,她似乎有着天然的淡化态度,持有一种十分奇特的“还原”思维。
到马场没多久,几个人在她身上摸过,都是学上马下马的时候。过后文秀自己也悄悄摸一下,好像自己这一来,东西便还了原。
这种“还原”思维一直延伸到她进入权色交易之后。在主流话语的背叛和无情现实的挤压之下,她几乎是逆来顺受甚或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在第一次被供销员引诱后,她的反应是掏出获赠的苹果,“笑一下。开始‘咔擦咔擦’啃那只苹果”,进而感叹“‘我太晚了——那些女知青几年前就这样在场部打开门路,现在她们在成都工作都找到了,想想嘛,一个女娃儿,莫得钱,莫得势,还不就剩这点老本?’她说着两只眼皮往上一撩,天经地义得很。”文秀的特殊之处只在于她坚持“洗”,从第一次被玷污后“她不洗过不得,尤其今天”,并“走得很远,把那盆水泼出去”,到最后遗体被老金放进水池中,“她合着眼,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研究者普遍认为,“水”被严歌苓赋予了荡涤罪恶、漂洗灵魂的救赎意味。⑩确实,于文秀而言,“洗”或“水”是另一种“还原”的方式,她相信水能使自己的身体乃至灵魂从肮脏的权色交易中“还原”。
然而,与其说作者试图以“水”为救赎途径荡涤时代的罪恶,不如说,严歌苓将希望寄托在了以“水”为象征的自然力量上。这自然不但蕴含了“水”所象征的原始、纯粹与生生不息的坚韧,更直接以游牧文明为具体指向。
在已有的研究论述中,老金往往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物。其实,不论是在文本的着墨篇幅,还是在推进故事逻辑的前进力量中,老金都是一个与文秀不分伯仲的重要存在。他的善良、敦厚、粗犷、纯真反衬了现实政治世界的丑恶、污浊、矫饰、龌龊,表现了作者对游牧文明的向往与寄托。小说中,文秀虽然痛恨老金,但却很爱他的歌声。
有时她恨起来:恨跟老金同放马,同住一个帐篷,她就巴望老金死,歌别死。实在不死,她就走;老金别跟她走,光歌跟她走。
这个大草原上“有时像马哭,有时像羊笑”的声音浑然天成、发乎真心地“唱他自己的心事和梦”,文秀觉得这没有丝毫目的性的歌唱远甚于锣鼓喧天的政治话语宣传,“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从千方百计、不辞辛苦地从远方为文秀弄水洗澡,到最后在文秀的要求下开枪打死了她,老金始终以“文秀的帮助者”这一身份存在,作者企图依赖他所代表的的游牧文明,以其纯净、本真的原始力量为浊世中的文秀们寻找一条救赎之路。
只不过,如同老金被阉割的身体所隐喻的,作者自己都已意识到,她所向往的游牧文明早已是一个失根的时代,它于丑陋肮脏的时代环境中早已回天乏术。文秀的“还原”法很快就不管用了,断水数天后,“老金见她两眼红艳艳的,眼珠上是血团网。他还嗅到她身上一股不可思议的气味。如此的断水使她没了最后的尊严和理性。”
事实上,以“水”、“歌声”所代表的游牧文明为救赎途径非但注定是无效的,其对“尊严”、“理性”这些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价值(虽则在那个年代早已被压抑为无声的存在)的救赎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悖谬。严歌苓在对山林草原的想象中构筑起一个文字的乌托邦,企图凭借原始之力荡涤现代文明的罪恶,同时保留其所倡导的“理性”、“尊严”等“进步”价值观念,这样的愿景显然只是一场痴人说梦。
意识到此路不通的作者进退维谷,只能重回道德审判的旧地。在文本之初的文秀看来,老金不过是一头牲畜,他会“低低地吼”,“还有种牲畜般的温存”。很快,这一根据文明程度区分“牲畜”与“人”的标准随着文秀的献身而急转直下,“文秀‘忽’地一下蹲到他面前,大衣下摆被架空,能露不能露的都露出来。似乎在牲口面前,人没什么不能露的,人的廉耻是多余的。”“廉耻”成为了新的判断标准,因主动献身而失去廉耻的文秀才更像是一头牲畜。在文本结束的高潮部分,开枪打死文秀的老金将脱净了的文秀放进水池,然后选择了自尽。此时,他“仔细看一眼不齐全的自己,又看看安静的文秀”,“老金感到自己是齐全的。”通过救赎文秀、坚守人性美而在自己不齐全的身体中感到了齐全的老金进一步将作者的道德判断立场揭示得淋漓尽致。
对于文秀与老金的双双死去,现有对《天浴》的解读基本将其视为“在死亡中获得重生与超越”⑪。其实,与其说寻找不到出路的文秀选择了死亡,不如说,找不到救赎力量的严歌苓只能让这一切走向毁灭。这一场无出路救赎的毁灭看似悲壮而唯美,实则隐含了作者给不出答案的无奈,落入了在道德控诉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虚无之中。至此,曾想以展现权色交易逻辑、将救赎之路寄希望于游牧文明的严歌苓不但重回道德评判的泥地,更使整个文本落入了虚无之中,尽管这比控诉个人道德败坏的“伤痕文学”作品已高明不少。
三
同样是重生,严歌苓借“旧皮褪去,新肉长出”反讽了文秀“由人转向牲畜”的堕落;而在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⑫中,同为为回城而献身的女知青李小琴则获得了“创世纪”般的真正新生。
《天浴》中的文秀对造成自己“有城回不得”的原因有一个由懵懂逐渐清醒的过程,李小琴则是自文本伊始就意识到自己正被主流意识形态逐步边缘化的境地。第一次招工挨不上她,眼见着第二次招工依然很可能又没有自己的份,在此情形下,尽管“李小琴有些着急”,但她自始至终都不曾相信过主流意识形态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即便她劳动好,“做什么事都有个利索劲”,比姓杨的学生更得全村乡亲们的赏识,但她深知这并不能成为赢得招工名额的理由,要想回城,只能另辟蹊径。她想,“她没有姓王的后台和能量,也没有姓杨的权宜之计,可是她想:我比她俩长得都好。这使她很骄傲。”既然没有后台,也想不出别人的权宜之计,那只有靠自己的身体。李小琴对权色交易逻辑的体认与认同一览无遗。
相较于文秀的“还原”思维,李小琴对“性”的淡化态度则更为彻底,大有颠覆“伤痕文学”女主人公的态势。于她而言,性就是回城的筹码,且现实情况愈是紧迫,她对自己身体的利用意图就愈发强烈。权色交易的逻辑在招工日期的日益逼近下被逐渐强化。在她最初与杨绪国你来我往的调情挑逗中,目的性已十分明确,“李小琴想:可别弄巧成拙了。”“不料杨绪国心里也在想同样的话,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叫作:可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一个想得到回城的“巧”,一个不想惹付出代价的“膻”,两人虚虚实实、你进我退地展开了一场围绕回城和情欲的拉锯战。她很明确,这个小乡村“再好我也不稀罕”,于是,被几番挑逗后仍按兵不动的杨绪国使得“她心里十分发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该做的她都已经做到,如今已黔驴技穷了”。在某日回城探亲时,“李小琴看见城里一片热腾腾的气象,又敏感地发现城里女孩的穿戴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心里窝了一团火似的,很焦急又很兴奋。”联想到即将与杨绪国一起返回大杨庄,“她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又很难得的机会,如果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而当她终于成功献身后,面对杨绪国闪烁其词的“我们研究研究”,“李小琴心想,‘不能叫他那么便宜了!’”。王安忆将性与回城等价交换的过程交代得清晰明朗。
对于权色交易中的李小琴,王安忆不但不渲染、暗示其所受的身心巨创,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一个在努力利用身体中享受此过程,甚至欢乐得将这“身体经济学”抛诸脑后的“异类”女性。李小琴与杨绪国抱着互相利用的功利目的走到了一起,却在性与回城的较量中升华出一个美丽新世界。在两人逐步深入的性关系中,王安忆渐渐抹去了“小队长”、“学生”的称呼,而只以“男人”、“女人”代之。作者不仅以两人纯粹的性爱洗去了权色交易的肮脏丑陋,回击了对其作出道德判断的文本策略⑬,更将其作为一条救赎道路,指向了对个体人生自我意义的追寻和发现。当娟娟们还在思索、犹疑这样的付出是否正确时,李小琴反复思考着的却是“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一终极问题。
第一次思考发生在她得知招工快要开始之时,想到自己对杨绪国的征服尚未成功,“她心里如一团乱麻似的,无头无绪地站在桥头。日头斜斜地照了桥下,金黄金黄的一条干河,车马在金光里游动,她不由颓唐地想道: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彼时的她认为,招工、回城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即使以身体交换,她也在所不惜。然而最终还是“弄巧成拙”了的她既没有将错就错地就此利用为回城的机会,也没有进入道德层面的悔恨与反思。而是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在偏远贫穷的小岗上重新思考起人生的意义。
她直愣愣地望着井底下的自己,又想哭,又想笑。她对自己说“喂”,声音就轻轻地在井壁上碰出回声。“你这是在哪呀?”她心里问道,就好像有回声从井下传上来:“你这是在哪呀!”她静静地望了半天,才叹了口气,直起身子,满满的将一挑水挑了回去。
等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屋里已经黑了,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慢慢地流下,她想:我从此就在这地方了。心里静静地,却没有半点悲哀。她又想:人活着,算个什么事呢?……她忘了那小孩的腮帮一鼓一鼓,断然想道:人活着,是没有一点意思的。
她的反思以无所谓回城、无所谓道德的姿态越过了对权色交易道德与否的无止境纠葛,直抵“性”所指向的个体存在意义。通过性,她摸索到了真实存在的自我,找到了救赎的不二法门。
1989年的王安忆通过李小琴反问人生的意义,李小琴的迷茫使人联想到始于9年前的“潘晓来信”事件。时维1980年,《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⑭这封诉说人生苦难、无路可走的来信引发了对“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全国性大讨论。有的人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的人主张“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作者之一的黄晓菊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中国青年》编辑部匆匆偃旗息鼓,以“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人应该在实现整体中去实现个体”⑮宣布讨论就此结束。王安忆笔下的李小琴却选择了背道而驰的道路,她在潘晓认为走不出的死胡同——“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里发现了出口。她对身体的体认和感觉是如此真切而强烈,以至于甩开了“回城”、“前途”等政治包袱,在自我放逐中走向了自我放纵,寻找到了“人活着的意思”。
她是那么无忧无虑,似乎从来不曾发生过什么,将来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她的生命变成了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一个瞬间。……她心里没有爱也没有恨,恨和爱变得那样的无聊,早被她远远地抛掷一边。
同样走出“性关系捆绑权力关系”的杨绪国也重获了新生。
她就像他的活命草似的,和她经历了那么些个夜晚以后,他的肋骨间竟然滋长了新肉,他的焦枯的皮肤有了润滑的光泽,他的坏血牙龈渐渐转成了健康的肉色,甚至他嘴里那股腐臭也逐渐地消失了。他觉得自己重新地活了一次人似的。
他的身体在刹那间“滋滋”地长出了坚韧的肌肉,肌肉在皮肤底下轰隆隆地雷声般地滚动。他的皮肤渐渐明亮,茁壮的汗珠闪烁着纯洁的光芒。
他们逃离了性关系与权力关系捆绑的羁绊,通过性的救赎道路发现了自我个体的生命本真,生命只存在于自我体认的那一“瞬间”,“这快乐抵过了一切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畏惧”,“在那涌澎湃的一刹那间,他们开创了一个极乐的世纪。”
李小琴与杨绪国开创的七天七夜不但戏仿了《圣经》中的“创世纪”,更以一种看似情何以堪的方式找到了双方获得救赎的有效途径。同为七天七夜的极致欢乐,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⑯以个体“人”的发现颠覆了“集体”话语的规训,以性关系的反讽解构了看似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系。王安忆则打破了“性权力常常是政治权力的隐喻”⑰的惯例,从根本上放弃了性关系与权力关系相连的预设,在性关系中发现自我,凸现了大写的“人”的存在。至于李小琴何去何从,这场不成功的交易如何收场,王安忆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也早已不需要答案。李小琴已然找到了“自我”这个新天地,这也就是王安忆的书写目的所在。正如周介人对王安忆的评价,“她对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或许还无力去把握,然而,她不遗余力地控求着人的价值、人的追求、人的心灵美等一些为当代青年所共同关心的问题。”⑱
四
同为女知青回城,竹林选择了评判个人道德的立足点,以涕泪俱下的方式使读者为之动容。严歌苓在游牧文明价值取向的失败后,重新回到了道德评判的领域,如她本人坦言,写作《天浴》的时候“仍有控诉的力量”⑲。王安忆选择了关注个体存在意义与审美生存方式,关注曾经“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的具有艺术特质的“形式”,⑳进入纯粹的自我世界。
尽管,“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㉑但竹林、严歌苓、王安忆在“女知青回城”题材上所呈现出的不同书写景观还是让人联想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中“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
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审判,没完没了地审判,对所有人全都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径渭分明的。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的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㉒
这种乐于审判的毛病在涉及“文革”题材的作品中流毒甚广。无论是为了赞颂还是批判,作者们居高临下的“法官”姿态总是不改本色。相较于竹林与严歌苓,王安忆似乎能发掘出一个更有意义的层面。
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那里,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谋总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㉓
王安忆曾在1982年创作了属于“少女雯雯系列”的《广阔天地的一角》㉔,小说中天真的雯雯在权色交易面前茫然失措,而另一位被村支书逼迫献身的女知青朱敏更可被视作文秀的翻版。七年后的王安忆以另类的李小琴走进了“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寻找到了一个更审美化生存的意义空间,也为“女知青回城”的书写开垦到了另一番可资借鉴的新天地。
【注释】
①《人民日报》社论,1968年12月22日。
②竹林:《生活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王云缦:《知识青年问题应该得到真实反映——读〈生活的路〉》,《读书》1980年第1期,第81-83页。
④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8页。
⑤刘克:《飞天》,《十月》1979年第3期。
⑥严歌苓:《天浴》。
⑦《人民日报》社论,1968年12月22日。
⑧《人民日报》社论,1968年12月25日。
⑨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91页。
⑩胡辙:《撕裂与重构——严歌苓〈天浴〉解析》,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⑪王君:《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生命创伤主题》,2007年扬州大学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⑫王安忆:《岗上的世纪》,《钟山》1989 年第 1 期。
⑬张雅秋:《都市时代的乡村记忆——从王安忆仅作再看知青文学》,《小说评论》1999年第6期。
⑭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⑮《六万颗心的回响》,《中国青年》1980 年第 12 期。
⑯阎连科:《为人民服务》,《花城》2005 年第 1 期。
⑰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⑱周介人:《失落与追寻——读王安忆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札记》,《文艺报》1982年第6期。
⑲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新京报》2006年4月29日。
⑳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 年第 5 期。
㉑张爱玲:《论写作》,《流言·张爱玲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㉒[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㉓[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㉔王安忆:《广阔天地的一角》,《收获》1980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