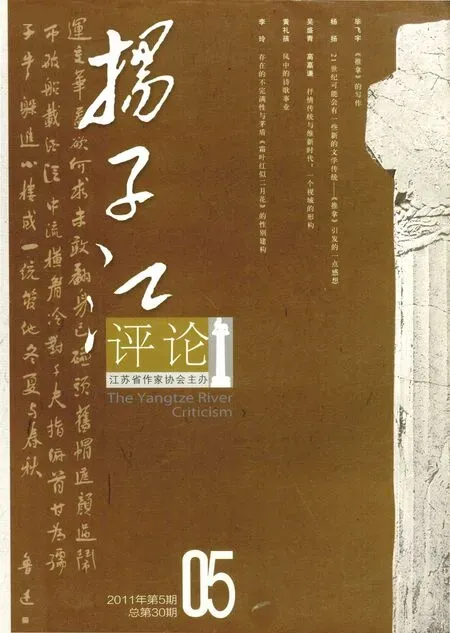视觉时代的不可承受之“轻”——毕飞宇及其小说《推拿》
王文仁
一、前言
相较于苏童、莫言、王安忆等大陆名家在台湾的高知名度,被誉为中国1990年代以来最具个人风格的汉语小说家毕飞宇(1964-)①,似乎才是刚要崛起的新星。实际上早在1994年,他的作品《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被改编成电影②,而当2001年长篇小说《玉米》诞生后,大陆的文学界更掀起一阵“玉米热”。继之,中篇小说《青衣》被改编成电视剧③,2003、2004年以短篇小说《青衣》、《玉米》拿下中国小说学会奖、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9年以《推拿》拿下《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与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和小说双年奖。毕飞宇在中国的迅速蹿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当代中国小说不可忽略的现象,即在不引经据典、不挪用理论的写实架构中,一套令人动容的说故事方法(story-telling approach),让文学性与市场性得到了有力地结合与平衡。
探究此一现象的形成,部分来自于1980年代后期新写实主义(new realism)的推波助澜,更大的促因,则是1990年代后视觉文化语境所造就的影响。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里小说原不乏写实的意识和技巧,但要正式成为一种流派,占据文学发展的中心,则要等到20世纪初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全面引进。对彼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写实”(real)本身就蕴含着解放与启蒙的意涵。而稍后,写实主义(realism)在左翼论述中被正名为“现实主义”,“一种迫切的时间感与意识型态召唤更呼之欲出”,“写实”因此不只是对生命百态的模拟观照,而是包拢进文学典律(canon)的转换,文化场域(culture champs)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乃至于真实与虚构论辩的庞大课题④。撇开幸与不幸的争论,“写实”之演化而为各种相衍、相近的形式,主导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主潮,既是事实也有着历史发展必然与偶然的促因⑤。然而时序一迈入1980年代,先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美学展开剧烈的冲击⑥,继之新写实主义的诞生几乎扭转了长久以来写实小说的样态。
“新写实”概念的诞生与定名,始于1988年。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首先注意到一种新的小说类别与文学现象正在兴起,这些作品的格调并不统一,但在把握现实的内在精神,以及直视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本相上,与过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截然的不同。⑦来年5月,文评家张韧正式替这类小说定名为“新写实小说”,强调其与传统现实主义有了根本意义上的区别。⑧江苏《钟山》杂志,继而在1989年第三期开始设立“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在卷首语中强调,新写实之所以为“新”,乃在于“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换言之,其更新了传统真实再现(reappear)环境中典型性格的概念,破除现实主义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特征,在作品中直显地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⑨表面上,“新写实”似乎是回到了传统和现实主义,其实质却是要与过去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现实主义”针锋相对,而其展示生存本相的勇气,与现代主义也是一脉相通的。⑩这一类的作品写的多半是普通人的庸常生活,用的是自然而不矫揉造作的语言,它们不再刻意去追问生活的本质意义,而是让生存与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平庸的人性内容——即凡俗性(profane)——成为小说真实描绘的核心。符应于新时代的客观需要,这种“新写实”的观念很快就在大陆文坛上传衍开来,成为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界里一股主要的趋势。
另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因素,来自于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语境对小说书写的挑战。早在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就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机械复制时代”,一切的艺术品可以透过复制的方式广泛传播,“电影”也将扮演一种扫荡文化传统的角色,带来富建设性的意义。⑪到了1970年代,美国当代批评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又明确告诉我们:“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在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⑫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所指出的,我们正在从一种抽象的书籍文化进入一种高度感性、造型和画像的视觉文化时代⑬。在这个时代,以影像为主的传播媒介广泛、深远地主导着我们的文化发展,以文字媒介为书写形态的文学自然受到了挑战与挤压。最终,以文学为业的创作者们不得不思考,允让视觉文化的元素进入自己的创作,或者干脆就维持一种有意的距离。所以,打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也就有这么一批小说家,因为作品与影视(诸如电影、电视剧)有了结合,迅速蹿红为“偶像级”作家⑭。
毕飞宇的崛起,与其作品的凡俗性,以及不断被改编成为电影与电视剧,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如郝誉翔所言,毕氏的小说“非常好读,情节紧凑,充满了戏剧的高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人物鲜活又分明”⑮。这样的作品不仅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且往往在琐碎与平凡中,见证凡俗里的真实性(reality)。但毕飞宇确实是富反思性(ref lective)的作家,在十多年的创作旅途中,既衍生出独到的小说美学,且在对现实生活的细密演绎中,充满个人风味与和流俗抵抗的对话及角力。本文在论析其小说艺术时,将以近期作品《推拿》(2009)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样的选取,不仅在于《推拿》一举拿下当代中国六个文学大奖⑯,也在于毕飞宇在此书中,打破过往专注于书写女性、历史、伤痕的小说惯习,挑战一个黑暗而富诗意的盲人世界,其所创造出描摩人性与想象世界的方式,之于个人乃之于当代的华语小说,都是值得记述的里程碑。
二、“轻”与“重”的小说艺术
要理解毕飞宇的小说艺术,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是个不可或缺的引子。在这部小说的首章,昆德拉用了数万字谈述一个对立而又辩证的观念:“轻与重”。他引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永 劫 回 归 ”(eternal return)的观念,并且做出了这样的陈述:“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但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⑰在昆德拉的笔下,“轻”和“重”是神秘的对立与模棱的两难。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永劫回归”之为不可能,就像人的生命与历史都只有一次性,如此之“轻”却也无比之“重”。毕飞宇深谙此理,且很早就有了自己独到的解释:
我轻。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知道我有多轻……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从昆德拉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感受,他使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词:不能承受。我为此感动了很久。
轻的人却又是勇敢的,具体的表现是他从来不惧怕重量。这有点矛盾了。这不矛盾。中国的老百姓用极度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的人生哲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⑱
“不能承受”代表已是明白,但无法或无以承认,因而只能不断回旋:用轻盈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用轻松的文体开掘沉重的主题。这让人直截联想到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4-1985)在《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中,同样在第一讲里谈到“轻”与“重”的对立。卡尔维诺举了不少的神话的例子,但也引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做出这样的阐述:
我们所选择并且珍视的生命中的每一样轻盈事物,不久就会显现出它真实的重量,令人无法承受。或许,只有智慧的活泼灵动,才得以躲避这种判决——那本小说就是以这样的特质写成;这些特质属于一个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相当不同的世界。⑲
在卡尔维诺眼中,轻与重的对立及辩证是生命中无以闪躲的本质,也是小说创作者始终需面对的晦暗鸿沟。对睿智的书写者而言,小说创作实际上是在改变策略,以不同的角度、逻辑与认知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洞见者(Voyant),在苦涩地承认“生命中不可逃脱之重”后,将自己扬举于世界重力之上。于是,轻盈的秘诀成了所有小说家不传的密法:他们贴近真实,直视生命的沉重,却不断抛弃、化除故事结构与语言中的沉重感,让文字抵达生命缠绕与矛盾的根部。
笔者以为,毕飞宇开始深刻理解此点,是在完成《玉米》(2001)之后。推究他的创作生涯,始于1980年代初期。一开始故意写得怪又难懂,“仿佛不是我毕飞宇写的,是德语、法语让我给翻译过来的。”在摸索中,他书写乡村、书写女性、书写权力,却经常求好心切用力过猛。直到完成《玉米》才“找到了自己说话的方式”⑳。作为创作历程上重要的转折,短篇小说《玉米》的写就对作家而言有两个层次上的意义:一是,确切蹈践他“写作的萌芽是从‘过日子’中来”的想法,且在里头文字表达出来的“是‘生’的,是‘动’的,生动,活生生的动态”㉑。表现而出的,便是轻者的不惧怕重量与切近于现实。二是,把小说描绘的重心直接贴紧在人物身上,去除过多的理论概念、背景描绘与历史纵深,以素朴、冷峻的眼光,让人性的勾心斗角、饥渴匮乏、复杂纠缠,细密显现在生存法则的小说舞台。这两点到了《推拿》,无疑有着更进一步的演绎。
《推拿》的主题是“盲”,写的是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的盲人。1964年出生于江苏兴化的毕飞宇,1987年自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曾经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教过五年书,加上长期伏案写作,经常在家中附近的推拿中心放松。写这部小说既是对盲人朋友们的承诺,也是心中久藏种子的触发。当然,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一,中国处在一个经济腾飞的时期,这很好,但是,没有人再在意做人的尊严了。我注意到盲人的尊严是有力的,坚固的,所以,我要写出盲人的尊严,这对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好处的。二,就我们的文学史来看,我们没有一部关于盲人的小说。以往的作品中,有过盲人的形象,但是,他们大多是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的。我不希望我的盲人形象是象征的,我希望写出他们的日常。㉒
从这样的自陈不难发现,这部小说打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一来,它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专写盲人之作。一如徐士金(Patrick Süskind,1949-)透过《香水》将书写的焦点置于嗅觉,以气味重构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毕飞宇对盲人世界的悉心关注,拭亮了一个以往只能以象征方式存在的盲人世界。这对整体华语文学的发展,确实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二来,毕氏也坦承,这部作品更进一步要表述的,其实是全人类的盲。将这样的意图放在视觉文化时代,更蕴含见与不见的强大反差。
一如论者所言,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能力,一个成年人从外界接受的信息有90%以上仰赖于视觉。每只眼睛的视神经纤维多达120万条,远超过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神经纤维的总和,人类视觉过程的复杂程度因而也就远超过其它的感官知觉。㉓现象学大师黑格尔(Georg Wilhelm Fiedrich Hegel,1770-1831)曾经说过:
视觉(还包括听觉)不同于其它感官。属于认识性的感官,所谓认识性的感官,意指透过视觉人们可以自由地把握世界及其规律,所以,较之于片面局限的嗅觉、味觉或触觉,视觉是自由的和认知性的。㉔
视觉的全面与自由,显现在它既是人类观看外在世界最基本的能力,也显现在此一观看过程的主动与能动性。视觉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中透过影像接受各式讯息,便利地与他人沟通,进而掌握并理解这个世界,人类的文明进步基本上也是建构在这样的观看与理解上。因此,当视觉遭到障蔽,其在生活适应上所造成的困难,往往远甚于其它感官上的缺陷,甚至造成与明眼社会间的隔阂。这样一个视觉时代不可承受之轻的黑暗世界,到了毕飞宇的笔下,乃有了鲜活、立体且爱恨交加的光明面貌。
三、人物心理与生存境遇的生动刻划
严格说来,《推拿》并不是一部情节繁复的小说,部分章节甚至几乎没有情节推动,作者更大的力气实际上是放在以小说人物为中心的生存际遇的描绘上。换言之,这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这一点,清楚显现在各章节的名称,除了首章的《定义》与最终的《夜宴》外,作者都直截用了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透过他们的视角来进行叙述。从叙述学(narratology)的观点来看,小说中的人物可以简单区分为“功能性”与“心理性”两种。前者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者惯常运用这样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分析。主张后者,强调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在小说中,我们理应关注的并非只有人物的心理、动机或性格,也该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类型、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这种人物观,主要被用在19世纪小说和现代心理小说,分析具有丰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人物㉕。
读毕飞宇的小说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㉖《推拿》既在书写盲人的“日常”,人物的立体及其鲜活性也必然的要冲破仅仅作为“象征”与“行动素”的扁平设置,以富个性及生命境遇的型态出现。但这并不意味小说中的人物必须与真实人物画上等号。佛斯特(E.M.Forster,1879-1970)在其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中提出过“真实人物”(homo sapiens)与“虚拟人物”(homo fictus)的区别。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虚拟人物”)是在作者的召唤下出来的,他们与真实人物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其区别是:只要作者愿意,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可以为读者所知,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真正相互了解。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充满著作者的想象与安排,这样的作品在小说世界里是活生生的,却可能在现实世界付之阙如。㉗
毕飞宇在写作《推拿》时,确实尊奉这样的法则,他说:“我在《推拿》里并没有写我朋友的事,‘真人真事’我都没有写,作为一个小说家,想象是我的基本能力,在了解的基础上,我拥有想象的逻辑。”㉘与人物“心贴心”而非“面对面”的想象逻辑㉙,让人物在小说的世界里头生动,并且拥有自己的身世与生命。打从一开头的《引言 定义》,作者就迅速带出这部小说的重要人物,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复明。但是在这里,沙复明的出现其实是被借来阐述“推拿”的意义㉚。真正作为鲜活人物首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反倒是第一章里的王大夫。
盲人在推拿房里多以“大夫”相称,但整部小说中只有王大夫始终被叙述者(narrator)如此称呼,其他人物都有自己的名字,加上王大夫在整部小说章节的安排中出现的次数最多㉛,我们可以将他视为是这部小说推衍盲人生存境遇时,最为核心的人物。王大夫在首章的出现,直接把小说的背景带到了千禧年前后。香港回归替深圳的推拿业带来了庞大商机,香港人、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国际化的金钱市场疯狂地来到这里。在这个呼天喊地改变着中国的大时代,王大夫先是赚足了钱,却又被泄了气的股市一路套住。最后,他不得不带着小孔到南京投靠老同学沙复明,以沙宗琪推拿中心为核心的故事于焉展开。
作为小说核心的王大夫,一开场便是以魁梧的形象出现。他的“指头粗、巴掌厚、力量足,两只手虎虎的,穴位搭得又非常准”(第21页),是一个标准推拿能手的样态。王大夫是天生的盲人,在小说中他有一个非常不成才的弟弟,这个弟弟原是父母为了弥补他的残缺而生,却让全家陷入了愁云惨淡。王大夫弟弟这类人,在小说里头被叙述者称之为:“活老鬼”。他们实际上是一胎化的中国,所创造出来无责任感的新人类,这些人的口头禅是“烦不了那么多”、“多大事”,天塌下来总以为有人顶着。这种人生命态度如此之“轻”,实际上是面对沉重的不断逃避。为此,王大夫确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说第十六章,他为了弟弟的债自剐,缝了一百一十六针。实际上他要保护的不是钱,而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尊严。人物的尊严在小说里头,是不断被强调的要点。
与王大夫毗邻出现的,是他的老同学,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复明。和前者在就学时代勤于锻炼身体相比,沙复明是靠着自己的头脑走出生存之路的。他精于谋略、迷恋管理,且有自己坚信的一套哲学:“‘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的,无论是当了教师还是做了官员,他们永远都会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好极了。……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剽悍的马力。”(第39-40页)沙复明的理论,一举戳破社会刻板看待盲人的想法。小说的第四章,作者安排他讲了一番相当醒人的话:“盲人凭什么要比健全人背负过多的尊严?许多东西,其实是盲人自己强加的。这世上只有人类的尊严,从来就没有盲人的尊严。”(第77页)事实上是,为了证明自己不输给明眼人,沙复明拼命读书、努力存本,最后把身体给弄坏了,埋下《夜宴》中吐血的情节。
被描绘为帅哥的小马,是王大夫宿舍里的下铺,他的盲是九岁时一场车祸造成的。跟中心里其他人相比,小马的困窘在于表面上看来和明眼人没什么区别,他的眼珠子还会经常地转动,因而造成明眼人的误解,有一次就这样硬生生被从公交车上赶下来。小马在第三章的出现,首先是为了透过他的生存境遇,勾勒出先天盲人与后天盲人,在心态与沉默上的区别:
后天的盲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连结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越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它是狂燥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在记忆的身处,他并没有失去他原来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为了应付,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第 52页)
小马是这样一种形象(image):他以残酷的手段在自己的颈上留下一道骇人的疤,他在内心杀死自己而后重塑(remoulding),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静默存活下来。在第八章中,作者特地花了一整章描写小马如何熟习于将时间当成可以无限切割、组合的玩具,并用他的话语道出:“看不见是一种局限。看得见同样是一种局限”,“健全人其实都受控于他们的眼睛,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与时间如影随形。”(第137页)这里头实际上有着中国传统道家“见与不见”的哲学意味㉜,亦蕴含对人类之盲的一种省思。
与小马一同出现在第三章的,是另一位后天盲人张一光。张一光在三十五岁时因为矿坑意外被夺去双眼,但他又是一百一十四条人命中唯一的存活者。这该死而未死中有了庆幸与恐惧的成分,让张一光后来事事都过了火。为了带出他的生存境遇跟解决之道,作者在第十四章(这一章刚巧是除了《引言》外最短的一章)用了七页半的篇幅,描摹张一光如何在后怕的恐惧中挣扎。他离开自己的家来到这家推拿中心,作为一具活着的“尸首”,他在黑暗的世界里茁壮成长,最终靠着不断的“嫖”——性的发泄与对女性的驾驭——来转移自己内心的恐惧,并且获得属于自己扭曲的尊严。
在第六章里,以半个章名(《金嫣与徐泰来》)方式出现的徐泰来,有着一口浓重的苏北口音。这口音(乡下人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卑,极度的自卑令他打了人,被其他盲人冷落。可又是因为这口音,他吊诡地获得了爱情。最后一位男性角色,是推拿中心的老板之二张宗琪,他一直到小说中段(第十三章)才以章名的方式出现。与沙复明的外显对比,张宗琪显得非常的内缩、深沉。这种严重的内在盲态,来自小时候对后母下毒的一种恐惧。这样的情绪阴影让他从此对吃食与言语极度恐惧,甚至因为无法克服亲吻女友的嘴唇,失去爱情。这样的人物在小说里头,他的每一天实际上都是在和死亡与恐惧拔河,他的生存意义(survival signififance)到头来就变成“活着”本身,这之中实际上又蕴含了“轻”与“重”的深刻辩证。
有别于过去在小说中大幅抬升女性角色的地位,毕飞宇在《推拿》里头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描摹男性盲人的角色,女性反倒落居了次位。最先以章名方式出现的是都红(第四章)。她一出场,就抛出了两个震撼弹。一是:明眼人的爱心行动是什么?是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康的人感动。例子是,都红用音乐克服了身上的残缺,她的表演却在慈善晚会上被形塑成对全社会的一种“报答”。实际上,在多数人眼中,盲人眼睛的残缺本身就是一种伤痕,残缺的意识根深蒂固地藏诸于我们的社会,成为一种难以动摇固着的意识型态㉝。这种弱者的逻辑使残障者难以在社会中翻身,也让都红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转向推拿。二是:都红的美引发了推拿中心一阵的骚动。这个美,先是上门的男客络绎不绝,接着是电视剧组人员看到后惊为天人。可对盲人来说,什么是美?这个问题困惑了凡事讲究理论的沙复明,最后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第五与第六章接连出现的小孔跟金嫣,一个内敛、一个外放,但他们在小说中有着相同的目的与方向,即对爱情的向往与跟随(前者为王大夫,后者为徐泰来)。这部分牵扯到整部小说关键性的对爱情的描述,下节会有进一步的析论。小说里唯一以明眼人角色出现在章名中的,是中心的前台高唯。高唯的存在,实际上是作为中心五个明眼人与盲人间的一种联系,两个世界的连结:她带出几个健全人间(不合)的关系,又透过与都红的友好,将沙复明的单相思化为自己生存的一种利器。最终透过高唯与金大姊、杜莉的摊牌,作者将推拿中心里复杂的矛盾与纠结一举引爆。
在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登场,聚首在沙宗琪推拿中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尊严与生存,这些盲人几乎每个都有跟正常人社会抵抗的艰辛过程。他们的日常交织在命运隐伏的悲剧中:王大夫的自剐,小马的逃离,都红的断指,沙宗琪的呕血……他们击不倒外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只能在一个接一个涌来的困顿中战胜或扭曲自己。在生命忐忑的缓步中,他们哭、他们笑、他们坚决的沉默,而又逐渐发现“爱情”——那生命的美好。
四、作为主题的爱情及其救赎性
读者多半会注意到,在《推拿》里头,人性的倾轧与斗争实际上不是作者意欲描写的重点。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眼人间的角力,沙复明与张宗琪在管理上的矛盾,但那多只是平静波澜中的一点小涟漪,谈不上什么大奸大恶。在整部小说里,作者花更多力气去经营的,反倒是盲人间的爱恋与情欲。这些盲人们在黑暗中摸索,渐次建立自己的信心与尊严,他们安全感的极大来源正在于对感情的信赖。回归到生活的原貌,盲人与正常人并无差异,他们踏实工作、追逐梦想,但因为先天与后天的匮乏,他们更需要情感上的依赖与互助,爱情成了这世界最重要的美好,一道照亮黑暗世界的窗扉。
在作者的安排下,《推拿》里头主要的人物不管成或不成,在情感上几乎都被抓成了对。情侣者,有王大夫与小孔、徐泰来与金嫣;单相思者,有小孔之于小马、都红之于沙复明。他们的爱恋与情欲,成为牵动整部小说发展的主轴。小说的一开头,就是从新世纪王大夫与小孔的相恋起始。在来到沙复明推拿中心之前,王大夫与小孔已经是一对恋人,在新世纪到来的那天,他们吻,“他们的身体往对方的身上靠,几乎是黏在了一起。”(第19页)这种身体的“吻”,让彼此都有了依靠。从此,王大夫的生命有了目标:回家开店,早点让心爱的小孔当老板娘。就因为恋爱,因为心疼小孔,被描写成憨实的他将钱丢入明眼人都看不清的股市,最终被迫到老同学的店里工作。在这段情感的经营上,小孔流露出更多的积极以及对安全感的渴求。她背着双亲的企盼,跟随王大夫私奔到了南京,甚至在性的渴求上经常也发挥主动性。“她需要的是他的重量。她希望他的体重‘镇’在自己身上。”(第35页)做爱时,她要王大夫“永远记住,我们是一个人。你想什么,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们是一个人,就像现在这样,你就在我里面。我们是一个人”。(第34页)情欲的缠绕在两人身上燃烧,让小孔惊天动地地要把自己“嫁出去”。这过程里头当然横生枝节,一如文中所言:“情欲是一条四通八达的路,表面上是一条线,骨子里却连结着无限纷杂和无限曲折的折杈。”(第83页)小马的出现成了王大夫与小孔爱情中奇妙的插曲。
小马的情欲,起于小孔身上散发的气味。在第三章中小孔来到男生宿舍,挨坐在下铺的小马身旁,气味与身体莫名的接触,让“小马顿时就回到了九岁。这种感觉惊奇了。稍纵即逝。有一种幼稚的、蓬勃的力量。小马僵住了,再不敢动”。(第59页)小孔的出现之于小马,实际上是一种召唤(recall),一种幸福感的重塑、情欲的启发。对原本着迷于关注时间、魔幻地耍弄时间方块的小马,小孔的气味连结的是童年时代的场景:“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有蓝天,有白云。还有金色的阳光。”(第137页)这样的描绘,很容易让人连结到徐士金《香水》对嗅觉的描绘。在这个由情欲所连结的空间(space),小马的白日梦无休无止地延续,幸福感取代了因为失明造就的悲惨与沉默。但是当他进一步想拥有小孔,落实对想象的捕捉,却只能立即的被打回原形,最后由张一光牵引着他走向了以性欲(lust)代替情感的不归路。
推拿中心里头具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徐泰来与金嫣身上。徐泰来是这样一个畏缩的人,但他自卑的软肋碰上了喜欢他说话的小梅,自信于是建立起来。这段不到十个月的爱情成了徐泰来生命中的救赎,但两人在发生关系后,小梅被父亲召回,嫁给一个智障。戏剧性的转折,促成爱情必然的诱因:徐泰来开始不吃不喝只是唱,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串联到二十一世纪初,什么风格都有、什么唱法都有,甚至把原本说不清楚的普通话唱得淋漓尽致。悲剧的爱情故事透过不断加工与传播,传到两千公里外的金嫣耳里,叙事(narrative)的迷人特质塑造出情欲的魔力。金嫣就这么横跨两千公里,追索一个命运带来的笑声。她的爱是狂放的、不羁的,比之于小孔更见其热烈与勇敢。她几乎是一开始就认定了懦弱的徐泰来,不要命的公开追求,把一切都做在了明处。但她也有自己的坚持:一个明证于爱的“仪式”(ceremony)。
但徐泰来是如此的破碎与卑微,以至于金嫣成了整部小说中,最大胆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他们的关系是在一场大哭,由金嫣说出“我爱你”后确定的。由于缺乏视觉,叙述者让徐泰来用了一个奇妙的词汇形容她的美:“比红烧肉还好看。”(第158页)味觉在这里代替了视觉,塑造一种爱情鞭辟入里的魔力。从此,这浪漫的女人无时无刻不在思想另一个仪式: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与婚纱。在金嫣的心中,“婚礼才是她的上帝”,“她可以一辈子效忠自己的婚姻,永不背叛,永远忠诚。”(第186页)但泰来并不想要隆重的婚礼,交杂其中的冲突、无奈,在第十五章中作者借两对情侣的倾诉,有着细腻的勾勒与对话,在最后的《夜宴》也借王大夫错抱了金嫣,抛出一个看似完满的结局。
相较于小马因为气味迷恋上小孔,沙复明对都红的爱恋,起于更无边无际的“美”。实际上,在中学时沙复明曾经经历过一次,只维持两小时与明眼人的恋情,这恋情对他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一定要得到一份长眼睛的爱情。只有眼睛才能帮他进入主流社会。”(第129页)这里头存在着盲人对主流社会价值的趋附与认同,但沙复明最终却是被更虚妄的明眼人眼中的“美”给迷惑了。在小说的第七章,他枯坐在休息厅里,努力用他的方式思索什么是“美”:
书上说,美是崇高。什么是崇高?
书上说,美是阴柔。什么是阴柔?
书上说,美是和谐。什么是和谐?
什么是高贵的单纯?什么是静穆的伟大?什么是雄伟?什么是壮丽?什么是浩瀚?什么是庄严?什么是晶莹?什么是清新?什么是精巧?什么是玄妙?……(第118-119页)
沙复明从记忆中抽取了无数的语词,但语言对盲人而言从来就不是语言,而是声音(sound)与无数小点排列出的触摸感。“美”在这里具有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它无比宏大抽象,又代表着主流社会赞叹的认同。更玄妙的是,连当事人都红都无法说清楚自己的美是怎样一回事。结果,对“美”的迷恋成了流沙,而沙复明深陷其中㉞。实际上,作为小说角色的沙复明自己也清楚:“盲人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评头论足里”,“就在‘别人’的评头论足里,盲人拥有了盲人的一见钟情,盲人拥有了盲人的惊鸿一瞥或惊艳一绝。”(第122页)但他并未能挣脱于此,几经挣扎后向都红求爱遭拒。实际上,都红也曾恋上小马俊俏的外表,这完全也是明眼人的主流价值作祟,只是这个部分作者并未有太多的着墨,都红断指的悲剧随即衍生。
文学评论家大抵认同,一部小说的关键,往往就在作者没有来由的关注上。毕飞宇在这部小说中如此精道的描写爱情,或许有向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借镜之意,然而摸索中的爱情确实比之正常人要更加的诚挚、珍贵且打动人心。盲人看不见对方的表情,加上爱情难以获得,表现出来身体的接触与言语,也就加倍的深刻与强烈。是以,守本分的王大夫会在犹豫要不要离开小孔几天回深圳一趟时说出:“我一天也不想离开你。你一走,我等于又瞎了一回。”(第25页)徐泰来在金嫣逼着说话的当下,憋着半天,才开口:“金嫣,我配不上你。”(第154页)盲人世界里的爱情,轻盈得似乎要抓不住,却在只字词组中,又显现出其沉甸甸的生命重量。掌握这样的特点,《推拿》一出手就具有了极度的可看性。爱情作为盲人光明世界里少有的美好,实际上也让他们的生命更为立体,更贴近了凡俗性。
五、盲人书写的挑战与反思
这个长篇小说和其它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小说的修辞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㉟
在文学的世界里头经常吊诡的是:一部没有巨大文学野心的作品,反而达成一波艺术创作的高峰。这之中蕴含的道理是:文学野心的缺如让作家能够回归朴素,从最基本可听、可见、可解的生命原点出发,热爱与拥抱生命中的冲突与矛盾。这里头当然有个人的取舍,也须考虑所面对的题材与书写意图。当写作纯然成为一种跟内在与外在世界的对话,或许更能够放弃意识形态、美学目的、小说修辞,成为生命真切的记录者。但没有野心可不可能是另外一种野心?笔者以为,毕飞宇在这部视角不断流转的盲人小说中,最起码有几个冀望是意欲达成的:一、打破过往盲人书写的偏狭型态,完整切进与描摹这个黑暗而错位的世界;二、阐述盲人乃至于一般人的生存意识与局限;三、让中国文学以“热”的方式走向全世界。
过往,在盲人的书写上,大抵很难离脱“伤痕文学”的书写风格:若非将盲人拿来作为正常人的一面镜子,就是将其做一个象征反映社会问题或哲学思考的象征,还有部分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包含残疾人的自我书写)是以励志文学的型态出现。上述几类残疾人的文学作品,表面上可以满足市场上的需求、政治上的目的与精神上的自我治疗,但实际上反而导致残疾者的被标签化,让他们受到更不公平的对待。㊱《推拿》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破除这样的偏狭意识,回归到作为人的方式来看待盲人的生活。是以,我们会看到王大夫面对恶势力时耍出自剐的流氓行径,张一光每每跑进洗头房里就不断对小姐大喊“爱妃、爱妃”,沙复明对美有近乎疯狂的坚持与迷恋。当作者决意将盲人当成正常人书写,就不可能不涉及人性,不可能不涉及盲人身上丑陋、畸形那一面。这当然会让部分强调社会价值的论者失望,因为读完整部小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象征意义,或者正面、积极、向上的力量。实际上,毕飞宇过往的小说作品(尤其是《玉米》与《平原》),相当强调社会意识的批判,许多人物的命运是被社会、历史与意识型态所牵引。但在《推拿》里头这些通通被加以弃舍,他让残疾者回归到就只是个人,走入日常的画面,人物的形象及其与外在世界的干隔与抵抗,因而更加的鲜明动人。
回归于人,人的生存意识及其局限必然是这部小说刻画的重点。生存意识的部分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局限是什么?就是人时时刻刻活在自己的盲区,活在自己生命的局限。这种盲区与局限又是什么?就是“固着”。具体的显现有两点:一是过度相信或倚仗主流社会的“见”;二是对自己欲望无以名状地执着。针对第一点,小说中有一幕沙复明与张宗琪在讨论拆伙的事,作者恰恰借叙述者的口吻道出他的想法:
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独立的、区别于健全人世界的盲人世界。盲人的世界里始终闪烁着健全人浩瀚的眼光。这目光锐利,坚硬,无所不在,诡异而又妖魅。当盲人浩浩荡荡向“主流社会”的时候,他们脚下永远有两块石头,一块是自己的“心眼”,一块是别人的“眼睛”。(第 255页)
这别人的眼睛,指的就是社会主流的价值。由于盲人是弱势,对自己的那一套总没有自信,所以一旦和健全的人相处,就会本能地利用健全人的“另一套”来替代自己的“那一套”,也就是借助“眼睛”来判断、来行事,这当然会过度倚仗主流社会的价值,要求主流社会认同他们。但明眼人呢,是不是因为看得见所以能摆脱社会强加的意识形态?毕飞宇显然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通过眼睛交流,我们凝视的目光有的时候是桥梁,有的时候是高墙和阻隔。”㊲这种墙是偏见、是意识形态、是猜测所成,每个人其实都带着自己的一副眼光在看世界,过度相信自己所“见”,就是掉入更大的盲点与漩涡。就像小说最后《夜宴》里头说的:“他们一直以为彼此都很了解,实际上,他们彼此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口独立的井,井水不犯河水永远都是他们最为直接的写照。”(第315页)
针对第二点,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自己欲念的坚持。对王大夫来说,那是钱与爱。对沙复明而言,是权力与美的获得。之于小马,是气味、是抽象的幸福感。对小孔来说,是情欲、是忠诚。在金嫣身上,是一个浪漫完满的爱与婚礼。在小说里头,某些坚持的结果就是悲剧。拿小马来说,他迷恋于小孔而不能自拔,因而将买来的性当成是“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手到病除,他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第257页)结果陷入性成瘾的恶性循环,被迫离开推拿中心。沙复明是另一个血淋淋的例子,他一心想要有间属于自己的推拿中心,又因明眼人的社会价值耽溺于美的想象不能自拔,最后生死未卜。说穿了,欲念的坚持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金嫣与小孔以此获得爱情,但不要命的被欲念牵着鼻子走,到头来就成了悲剧。这实际上也是人类普遍之“盲”。
毕飞宇在小说的书写上——尤其是《推拿》——还有一个隐伏的企盼,就是希望中国文学能够更加地走向世界文坛。在一次“回顾与展示——拥抱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交流会上,他谈到现在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幸运而又极度不幸的阶段。幸运之处,在于中国的经济发达让很多作家能够走向全世界;不幸的是,因特网的发达让全世界的文学阅读相对地走向了萧条。而西方在看待中国文学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削弱中国文学的文学质量与魅力。因此,尽管汉语成为世界的显学,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相当感兴趣,但是“‘冷’在出版社——很简单,中国的文学作品还不能给西方带来巨大的利润”㊳。
毕飞宇的观察,揭示了中国文学发展在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撇开因特网涉入对文学场域的排挤,他更重视文学性的创新及其与市场性的结合。在摆脱政治力影响之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必须创造出属于自我说故事的方式,在文学性与市场性折冲下登临世界文坛,成为华文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无可替代的一环。《推拿》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蹈践了此点,这本专写盲人生存境遇的小说不仅让他拿下六个文学大奖,毕氏也在2009年7月应邀为香港书展的贵宾,英国的安德鲁纳伯格代理公司则买了这本书的全球版权,准备向世界推出各种版本。由此,毕氏让自己走了出去,让自己成为我们研析21世纪中国新文学时,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六、结语
《推拿》是毕飞宇年过四十之后(43岁)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作家而言,那刚巧是一道有趣的书写界线:从紧张到放松,从尖锐到温和,从大叙事到小言说。但《推拿》到底不是部读来可以轻松的小说,当作者将关注的焦点落在社会边缘、人性黑暗、生命尊严且松弛有致地道来,潜伏其中的沉重也就牵引着读者坠入更深层的沉默与反思。留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毕氏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是专注地书写盲人不写外面的世界,不谈外在世界如何对盲人造成波动,或者带来悲剧性的影响。这种专注性,表面上让整篇小说的视野过于狭隘,缺乏与外在世界更进一步的连结,实际上这正是新写实小说的一种特色,也是毕氏有意让主流社会在其中“缺席”(absence)。
必须理解的是,新写实小说的凡俗性恰恰是一种对传统写实有意的颠覆,当关注的视野有意被置放于琐碎的间隙(gap),非主流于是跃上台面,成为反复论述与观看的焦点。是以,毕氏在《推拿》中所营造最大的悲剧,不在于王大夫的自剐、都红的断指,也不在于沙复明的咳血、小马的自裁,而在明眼的主流社会对这个黑暗世界的“视而不见”。因为“不见”,所以“黑暗”更加“黑暗”,没有得到同理心的理解与协助,让盲人更容易走向自我性格与命运的悲剧。小说的结尾,作者让盲人之间终于能够相互牵起手来(沟通与信任),感觉上结局是圆满的。实际上,从小说整体的诉说来看,明眼人与盲人社会的隔阂与矛盾,在毕氏看来显然有着巨大鸿沟而难以调和。视觉时代的不可承受之“轻”,也在此处清楚地显现。所幸,黑暗的世界中也有温暖,悲怆的生活里也有快乐。他用爱情照亮了这个疏离于你我之间的世界,也以轻盈的姿态,为我们展现视觉时代最沉重的生命哲思。
【注释】
①中国当代文学院学院讲评委员会:《〈推拿〉授奖词》,《推拿》,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导演张艺谋,编剧毕飞宇,巩俐、李保田主演。
③《青衣》被改编成20集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编剧陈枰,徐帆、傅彪、潘虹主演。
④王德威:《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⑤有关现实主义主导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促因及其详细辨析,参见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1980年代是中国第二次接受西方文化的高潮(首次自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从19世纪末的早期象征主义,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各种流派,都在迅速的引介中为中国文坛所知。这些接踵传来的西方文学观念,对1980年代后中国的文艺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举凡小说、新诗、散文、戏剧等文体,相继产出的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新的美学原则,显现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抗争,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追求。翻转了过往写实的书写样态,也为读者带来了新颖而强烈的阅读感受。
⑦雷达:《探究生存本相 展示原色魄力——论近期一些小说审美意识的新变》,《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
⑧张韧:《生存本相的勘探与失落——新写实小说得失论》,《文艺报》1989年5月27日。
⑨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9页。
⑩唐翼明:《大陆〈新写实小说〉》,台北:东大图书1996年版,第18-26页。
⑪[德]瓦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⑫[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56 页。
⑬[美]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
⑭徐巍:《视觉时代的小说空间——视觉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演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3页。
⑮郝誉翔:《以肉体殉祭——读毕飞宇的〈玉米〉》,《玉米》,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⑯其中,由《南方都市报》所举办的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毕飞宇以《推拿》获得“年度小说奖”。但他却以“个人原因”拒绝出席领奖,引发文坛上的一阵哗然。
⑰[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页。
⑱毕飞宇:《自序》,《毕飞宇作品集1玉米》,上海绵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⑲[意]伊塔罗·卡尔维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吴潜诚校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⑳编者:《江南才子毕飞宇是“得奖专户”》,《玉米》,台北:九歌出版社 2005 年版,第6页。
㉑编者:《生活就是要对得起每一天——郑重推荐毕飞宇以及〈推拿〉》,《推拿》,第7页。
㉒同上注,第 4 页。
㉓徐巍:《视觉时代的小说空间——视觉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演变研究》,第2页。
㉔[德]黑格尔:《美学》第 3 卷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31 页。
㉕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8页。
㉖李敬泽:《序》,《毕飞宇作品集 1 玉米》,第 4 页。
㉗[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李文彬译,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7-55页。
㉘编者:《生活就是要对得起每一天——郑重推荐毕飞宇以及〈推拿〉》,《推拿》,第6页。
㉙胡玉萍:《毕飞宇:与小说中人物心贴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2月18日。
㉚毕飞宇在首章之所以特意描述“按摩”与“推拿”的区别,是因为“按摩”在大陆改革开放后,有了异性按摩的色情与暧昧成份,而“推拿”是一个中医的老概念,更有文化价值与生命意义在里头。所以,作为小说关键人物之一的沙复明要强调:“我们这个不叫按摩。我们这个叫推拿。不一样的。”(第14页)
㉛扣除“引言”与“尾声”小说共计 21 章,其中有四章(1、10、16、21)直接以“王大夫”为名,另外第十五章“金嫣、小孔、泰来、王大夫”中,也把王大夫含括了进去,在比例上位居小说中所有人物之冠。
㉜如《老子》第12章中谈及,“五色令人目盲”。意思是说,过份追求视觉的享受,最后必弄得视觉迟钝,视而不见。进一步延伸而言,即人类若过度依赖眼睛所见之一切,往往无法洞悉表面背后的真理,而为表象所蒙蔽。换句话说,表面之“见”往往非真理之“见”。
㉝周掌宇:《盲人的问题与梅洛庞蒂的解决方案》,桃园:中央大学哲学所硕士论文,2000年,第66页。
㉞有关于“美”,以及审美感情所引起的感受,卢纳察尔斯基有着这样的观察:“有一派美学家认为,美能够起安抚作用,它降低我们的生命力,麻痹我们的意愿和欲望,使我们陶醉于和平安宁的瞬间。另一派美学家宣称,美就是‘Prom esse du bonheur’——幸福的许诺,它唤起对理想的怀念,犹如对遥远的、可爱美妙故乡的模糊回忆,正是对幸福的渴望抓住了我们,使我们的欢乐在审美享受的最高层面上带有一种哀惋之情。”就小说中的描述而言,沙复明对“美”的追寻显然兼及两种。参见卢纳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㉟张英发:《毕飞宇: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盲区里》,《南方周末》2009年5月8日。
㊱周掌宇:《伤痕与悲情》,收入《为梦前行——你我并无不同》,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38-44页。
㊲张英发:《毕飞宇: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盲区里》,《南方周末》2009年5月8日。
㊳朱玲:《作家毕飞宇:中国文学走出去“冷”在西方出版社》,《北京青年日报》201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