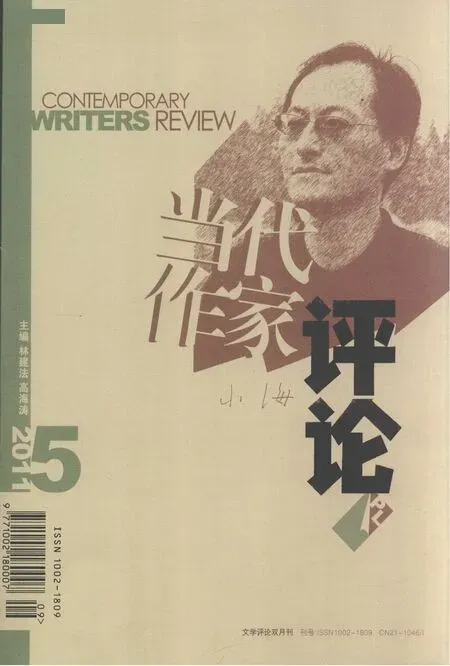写作,寻找生活与文本的“纯粹”——读王手的短篇小说
张学昕
一
在读过王手几乎所有的短篇小说之后,我感觉王手是一位踏实、虔诚又令人信服的“叙事者”。至少,王手的小说里已经充分地体现出他对写作的极度用心,对文学的满怀诚挚,而且,他对于短篇小说的敬畏,更是表现出一个作家最需要的“纯粹”。这种“纯粹”,不仅仅在于写作的态度上,还在于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用心。倘若一个作家,能以对生活的用心来实现并完成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用心,就一定会在文本中建立自己的这种“纯粹”。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文学是多么需要精神和艺术的双重纯粹。因为,文学写作在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承载,也受到了太多的困扰、扑面而来的冲击和难以挣脱的诱惑。实在说,在今天,做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是异常艰难的,尤其做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作者。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专事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就一定比其他作家更崇高,这也没什么可夸耀的,但他一定是在艺术的层面更忘我、更执著、更忠实的写作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所依靠和凭借的主要是对艺术的某种信仰。信仰或信念,才是一个作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作家或好作家的理由。我相信王手对短篇小说的表述:“我写短篇的负荷还是挺重的,是的,这也是我写得比较艰难、写得不多的原因。那是一个犹如生病的病理现象,它不一定天天纠缠着你,但你一定要坚持吃药,一旦病状发作,你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病生在你的身上,你一点办法也没有。”①本文所引用的王手的文字,都引自王手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西门之死》自序。这种几近病态的艺术追求,俨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内容而显得难能可贵,这可能也是小说这种文体样式尚能存留、保持活力的根本缘由。这种写作,当然应该算是“纯粹的写作”。
在这里,我愿意提到苏童,他对短篇小说也有着几乎病态的喜爱。他的短篇小说以及对短篇的理解,都显示出其极好的艺术感觉和天分。在谈到中外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时,苏童所钦佩的,不仅仅是霍桑在叙事中对道德、良心在人心中存在相互距离的考察;辛格在人物上不惜气力进行描摹的朴拙的小说观;而且,他还特别激赏博尔赫斯在作品中通过捕捉人类生活的重要细节呈现人类的巨大困境;同时,苏童还尤其喜爱雷蒙德·卡佛对待普通人生活的洞察力、毫不矫饰的文风。他将这些归结为“短篇小说,一些元素”①苏童:《短篇小说,一些元素》,《苏童散文》,第23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而苏童自己的短篇小说写作,更像是一次次愉快的旅程,在这些旅程当中,他凭借出色的想象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整合种种文学“元素”,再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小说元素,精神的、技术的,以此接近艺术宿命般的纯粹,从而,在短篇小说的有限时空里聚焦人性和生命的律动,蕴藉既属于个人又引证时代的种种现实。
王手崇拜苏童短篇小说叙述的宽广和从容,因为这的确是短篇小说最为难得的品质,他在这种镜像之中发现了自身的局限,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写作的出发点和前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位作家的时候,也不难从这位作家面对另一位作家的目光里,发现他自己的内心和诗学踪迹。因为真正的作家,都走在共同开掘小说新的可能性的途中,他们都有着以小说抵达现实和心灵的梦想,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小说长久以来的美学抱负。我相信,小说的基本元素之外,仍然有远未达到顶点的小说叙事的结构,还有安睡着的想象力没有被作家的创造性所唤醒。而每一位作家内心的“纠结”,都在于渴望能够以自己独有的写作炼金术,企及小说艺术绝妙的高度。当然,这里除了需要光芒四射的智慧,主要是需要一个作家坚持的纯粹的信仰,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从事写作。如今,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写作伦理或底线,在许多写作者那里已经变得格外地奢侈。
现在,我们大致厘清了王手的虔诚的写作姿态和方向之后,还无法猜测王手为何如此病态般地迷恋、醉心于短篇小说写作的理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王手短篇小说的叙事力量来自何处?纯粹属于王手的独一无二的文学元素都有哪些?王手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在哪里?可以说,王手是一位自觉的短篇小说的叙事者,那么,他究竟如何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来处理现实生活或存在世界,他在短篇小说中发现了什么,或者说,他发现了有关短篇小说的什么堂奥?像王手这样诚恳而有痛感的写作,对于王手本身和短篇小说的文本意义何在?王手在小说中将自己置于一个怎样的世界里?王手的坚执与纯粹,他的自我认同和“野心”之间还有多大的距离?除此,我更感兴趣的,还有王手在他的短篇情结中所遭遇的无奈、妥协、挫折,或者他的得意、喜悦、胜利,这些都肯定藏在了纸面语言的背后。但无论他能否意识到自己文本的表层或深层意义,对一个执著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写作的过程已然不是炫耀的过程,而是内心试图把握生命、寻找诗意、努力发现的过程,想刻意承担些什么的过程。当然,也可能是精神焦虑、无助而苦楚的过程。
我这样想象的时候,也就是在不断地预设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试图用心而冷静地考虑:一个作家,无论是否富有经验,无论能否将现实的和艺术的困难重重的环节抛弃掉,他一定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精神的自由、自立和艺术的独特,尽管对于写作而言,这里布满了可能永远也参悟不透的命运玄机。王手说:“我的短篇很少有虚构的故事,都是些真实生活的反映,以我对生活的用心来完成对短篇的用心,生活的纯粹加上文本的纯粹,我以为短篇就是要纯粹,就是要品与质兼优。”也许,纯粹真正的就是一种宿命,正如写作也是某种宿命一样,写作的初衷和文本之间可能出现的“断裂”,常常不具有通约性。可是无论怎样讲,写作中保持朴素、老实、厚道的姿态,可能会忽视或漏掉存在世界的许多“精彩”,但对于小说而言,叙述的“盲点”和“空白”处,一定埋藏着无尽的隐秘。这也许就是王手以短篇小说进入现实的另一种“纯粹”。
二
我对王手短篇的解读,想从他的叙述方式或手段开始,同时,努力去考量王手在调动、整饬小说元素时所获得的意外叙事效益。人性的较量与纠结、死结,命运、宿命的传奇,不可知的力量所导致的悲剧,琐碎而热闹的生活,都在王手实实在在的短篇独幕剧里率性而轰轰烈烈地上演。王手对短篇小说写作有着自己的看法:“短篇不一定都有一个大的起势,但一定得找到一个好的入口,这个入口可以很小,但进去之后一定要有绮丽的风光。这个风光就是一些短篇的元素。”在这里,王手的短篇小说最为用心的是叙事的“入口”。所谓“入口”,我理解为就是小说的视角选择或方位,还包括视角展开后牵动叙事的逶迤的通道。有了好的、恰当的“入口”,才会使后面的叙述趋于和谐或平衡。王手的与众不同在于,他老实而略显笨拙的布局,看不出有任何手段的手段,也没有匪夷所思的情景安置,但让人备感踏实、稳健。他所依赖的是,在充分的、流畅的、在人物困顿尴尬的人性夹缝里,进行种种点滴的、持续的、跌宕的故事讲述。我感觉到,这些文本本身,也是从作者对生存现实的思考缝隙中诞生的,它带着那种生存现实的感慨和沉重,因此,王手的许多短篇小说都蕴含着人性深处悲凉的况味。
我感觉,《英雄穷途末路》和《柯一娜一个人》是王手写得最沉重的两个短篇,但也是王手蕴蓄了很大力量和心劲的作品。仿佛是憋足了一股劲,小说小心翼翼地先开了一个很小的“入口”,慢慢地让水流静静地流淌进来,接下来的空间就开始阔大起来。首先说人物。正是人物内在的精神、心理渐变或骤变,并且让他们在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变化中,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纷繁、漂浮、欲望纠结的存在现场里,生发出令人震惊和骇异的状态。这两个短篇里,王手没有让人物的意识、思想、渴望和欲望只停留在心理阶段,他们必定要表现出来,化为实际的行动。《英雄穷途末路》中的阿诺德和《柯一娜一个人》中的柯一娜,都是有着各自力量的人物,在现实的挤压下,他们的行动感异常强烈,似乎要不断地胀破小说叙事的固有空间。这些行动浸透着或饱含着冲动,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心理的、现实的、理性的、非理智的冲突都纠缠在一起,他们带着自己的意志力从容不迫地登场,呈现出鲜见的人性的图景。阿诺德的力量和一系列“动作”,源自生命本身的内在压抑感和与精神无关的物质欲望。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向现实发起冲击,试图凭借身体或体魄创造“价值”。他和妻子阿香都沉浸在与现实博弈的快感里,生命的欲望和冲动与现代消费社会的怪影相纠缠,结果却被现实无情地解构。阿诺德身体的幻象,在一种强大的现实秩序中必然要成为泡影。王手轻松地发掘出主体能动性的荒谬性,在表现生命的惆怅、失败、挫败感的过程中,无意间将生理学、政治学与叙述学做了一次绝妙的联袂,这使他的叙事充满了反讽的快感或黑色幽默的效果。
与阿诺德相似,柯一娜的个人命运,更有些苍凉、残酷的味道。许多作品叙述的直接力量来自对人物的自我意识的不断揭示,发掘人物自我意识与现实处境的种种关联或纽结,而王手却在描述这个人物的外在行动中,一步步给她编织成一条无形的生命之索。似乎是一个人的命运被另一个人牵扯着,而自己放纵掉道德的底线成为风中芦苇之后,更无法把握自己,而且其行为自身,最终成了自己命运的否定者。这时,柯一娜不自觉地陷入到自虐、自贱、自卑的迷津里,生命在这里被王手演绎得灰暗、深刻,阴冷、透彻,构成这个短篇小说的黑色咏叹。这篇小说的“入口”依然很小,但整个叙述则直线推进,一个人的生死、命运就像一座堤坝的坍塌,在任由洪水数次拍击后的一瞬间訇然变成齑粉。在这里,我们强烈地体会到短篇小说不容忽视的独特的内暴力。我们曾阅读过很多相当优秀的作品,它同样能够深入到生活的纵深处,深入到事物的肌理表现生活,有作者不凡的洞察力和叙事技术,也能触及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但却难以对我们的内心形成强烈的冲击、震撼,王手想努力获得的便是这种能使人产生震撼的惊悸,这无疑是一种叙事的力量。
我还注意到这两个短篇情境设置的紧凑、抑郁,叙事节奏和时间的舒张、紧迫。两者不同的是,《英雄穷途末路》是先扬后抑,《柯一娜一个人》是“先擒后纵”。开阖的幅度也略有差异,但最后都令人感到无法忍耐的窒息。就小说的基本意义而言,它们都可以看成是对现代人存在状况和处境的忧虑,对人性中坚硬、柔软、错位、扭曲等质地的盘诘。
《软肋》和《夫妻》,也是王手短篇中的精品,它们同样体现了王手短篇叙事的基本策略:扎实地推进,举重若轻,在看似粗粝的对现实生活的复现中,洞烛探微,深入肌理。《软肋》中“外强中干”的人物龙海生,过着并不富裕甚至很“紧巴”的生活,但他凭借“江湖气”在单位里霸道行事,常常获得一些大大小小的利益。但作者捕捉到他性格中最复杂的那部分,他无论怎样“江湖”,任何环境或格局里面终究潜伏着秩序与规则,人的个性与欲望只有在相对的限度内才能发挥。所以,行走在生活的斜线里,龙海生的内心也必须把握应有的尺度。这样,人的“软肋”就变成坚硬冰冷生活的“溶栓剂”。《夫妻》描写小夫妻的一场“叫劲”、“呕气”,极平淡、极普通也极典型的一场波澜。王手给女主人陈节先系上一个“心结”,让丈夫天录惶惶不可终日,内心和行为都处于翻江倒海的“负疚”状态,接下来又在叙述的不经意间设置一个“拐点”,陡然中断一贯的节奏,反置陈节于被动的情势之中。这虽说只是男女主人公情感、心智、秉性多方位的一场并不离奇、没有阴谋的较量,但当代社会生活中家庭、婚姻巨大的情感隐忧被王手演绎得精微、别致、出其不意。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娇弱、微妙的心理和感受,人性中的浪漫、执拗、倔强、自尊的天性,毫发毕现。实际上,现代小说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奇迹性的发现,包括对问题、病患和病态的发现。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一篇有所发现的小说。在对那些日常性的、可把握的生活事物中,王手都没有将其转化为个人经验的事物加以呈现,而是在叙事切近生活“原生态”时,向着没有刺痛感的、客观冷静的日常性展开。这种趋向,应该说是王手短篇与众不同的叙事倾向。这些,是否也是王手所追求的一种“纯粹”的叙事诗学?
这里论及的这几篇小说的叙事起点,都是平缓展开的,格局也不算大,但叙事方面则格外精致和睿智。前面所说的“入口”和“收口”以及整体结构、布局,都是颇为下功夫的。叙事过程,也是人物的自我意识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时间和空间也绝少人为的刻意处置,讲究自然、规整、逻辑性。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确切地感受到一种温度,一种情感温度,正是作家在作品里设置了这个有高有低、又很神秘的温度,作品里才充满了氤氲,充满了叙事的魅力。很显然,这其中蕴藏的不仅是作家的独特感受,更有作家整理生活现场时所采取的属于自己的修辞方法。看来,这一定也是王手“别有用心”而“有意味的追求”。
三
我在这里,并不想将王手的小说做一种狭隘的叙事方法和策略上的简单理解或简化处理,也并不想探究小说叙事中作者是否自觉选择或者已经具有、坚持某种明晰的创作方法,而是想从王手的写作来思考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中所一贯坚执的文学观念、小说理念,与文本形态,与小说的虚构品质、想象关系之间的默契或错位,进一步思考一个作家是如何通过文本虚构来实现自己的想象,转化自己不安分的冲动的。那么,作家究竟是需要生活中的实感经验,还是要把握主体对叙述的控制呢?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是否一定要越出经验的边界,让叙事从文体的局限中溢涨出来?即使像王手这样踏实的叙述,也是裹挟着写作主体意识到的问题展开的,虽然没有通过精雕细刻、通过叙述来组织、抽象和阐释这些问题,没有让叙述成为隔在现实生活和人的心理、感受之间的夹层,谋求抵达真实和纯粹,但我想,王手最终还是获得了文学叙述的直接的品质。
叙述有时可能就仿佛一只粗糙的或者细腻的手,抚平、抚慰着生活中的褶皱、凸凹和沧桑。在叙事方面,王手不纠缠,不刻意,不矫情,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写真式”的呈现,之后,再用这只有力量的手,拧干毛巾里的所有水分,裸露出世道人心“原生态”的样貌。看似笨拙的表达,却直接抵达事物的核心地带。王手似乎也无意赋予现实任何一种形式、一种结构,也没有去强调心灵主体的“介入”。这多少显得有些“憨”或“拙”。实际上,“八十年代后期,写真式的写作已经陷入了少有人问津的尴尬窘境,加缪式的、卡夫卡式的、福克纳式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式的寓言写作已经开始变得深入人心。小说新观念的兴起与传播瓦解了以往作家对生活与所谓真实的理解,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小说的认识价值、表现对象、文本特征等等根本性诗学问题的理解”①张清华:《文学的减法》,第163-164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无疑,写真式写作在今天再次成为对短篇小说写法的一个挑战。显然,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对小说理念和作家个人智慧的重新审视。虽然,小说的力量并不只是暴露的力量,也不是依靠寓意和象征就能够深邃起来。坦然地揭示灵魂深处的隐秘,探察、揣摩人类不可摆脱的宿命才是最终的目标。那么,问题在于,面对有时很“粗鄙”的现实生活,一个作家如何下笔?尤其在当代,现实的问题已包裹起整个人类的精神形态,如何表现生活,实际上是作家面对的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种叙事姿态的选择。王手坦言:“生活中有很多残酷的东西,这是我一直在极力回避的,我以前告诫自己,要以温暖之心写身边的善良,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是的,温暖之心,会使叙述产生力量,会使王手的小说不断地让我们对他的故事产生信任感、亲近感,因此,他始终没有辜负我们的阅读。
《推销员为什么失踪》,极力状写商场如战场般激烈竞争中的残酷无情,但王手还是竭力地发掘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柔软、同情和自我失落。人被打得一败涂地之后,其内心燃烧起来的可能是极端的空洞、空虚感。它刹那间唤醒了我们的良知,使鼓胀的欲望之火一下子就冷却下来。《软肋》也是在淋漓尽致地呈现龙海生“霸道”一面之后,叙述了他的退让、收敛和羸弱,与此同时,开始张扬其他人的进攻、报复、得意。但两股力量对峙的结果却是难分胜负的平衡。我想,这个时候,王手一定没有按着自己的意志“控制”小说叙述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生活或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简单而朴素的短篇的本色和底色。可以这样讲,与其说短篇小说有技术,不如说作家对待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判断更需要定力和对技术的内敛。
王手笃定要追求一种“纯粹”,其实,“纯粹”也只是相对的一种写作状态或叙事境界,它不是作家一厢情愿的诉求,但一定是作家呈现生活时试图超越世俗、超越现实逻辑的内在追求。即使在叙事的激流中,作家也应该让生活中的可能性潜伏下来,哪怕是呈现给我们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就是叙事的可能性,也是生活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必须承认,所有人对世界的描述都是局部的描述,再完美的描述也有放射性的覆盖和无法抵达的盲区,这里面必定是隐藏着一种逻辑的动力,有着一种甚至是作者都难以把持的逻辑的动力,有时捉摸不定,难以驾驭又必须驾驭。一个短篇究竟能蕴含多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故事、情节,再借助语言的功能和魔力,传导出语言所暗示、隐喻和象征及其指涉的文本之外的“有意味”的世界,这不仅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限制有直接关系,更与作家赋予生活或经验以多大的想象力有关。也就是,与长篇小说不同,短篇小说叙事呈示出的只是一个生活片断、横切面、局部,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但它却必须通过其有限的叙述引申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可能性的或者充满迷局的、模糊性的世界。说到底,一个作家只能在叙事中呈示自己所意识到的,所能呈现的那一部分。
《飞翔的骡子》、《双莲桥》、《火药枪》所叙述的故事都格外引人入胜,它们将我们带进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每一篇小说的容量有限却仿佛都贯注着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来自人物,来自叙事的跌宕、冲击力量,当然,也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对生活的判断和选择的自信,因为这是小说的支配力量。而晚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则显示出了王手处心积虑般的成熟,叙述更加自信和从容,也更沉醉。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变成一个有“匠气”的写小说的“匠人”?那样的话,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纯粹小说家”了。
我渐渐感觉到,在王手的小说背后,隐隐出现的是一个中年人的身影。中年,是一个老成持重、思想日渐深邃但也愈发会变得世故的年龄,更是走向成熟的年龄。我相信,小说家的中年意味着成熟,甚或是真正写作的开始。在文本中,王手的目光总是略微低垂的,气质显然也不是“贵族”的,更不见什么“知识分子立场”,有的只是这个时代的作家身上已经很少有的英雄气概,任劳任怨的宽厚。虽然,我们看到王手小说中有许多无法掩饰的结构、语言上的“糙面”,甚至是令人惋惜的缺憾,这可能与他内心的尺度感有关,也可能是他贴着生活的“地面”很近的缘故,以致一时难以找到自己最确切的位置,造成了一种“深刻的惶惑”。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王手把追求写作的“纯粹”当作一种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视为自己精神和文本的最大“政治”。敬畏文学、潜心写作,成为他生活、生命的重要内容,有此,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