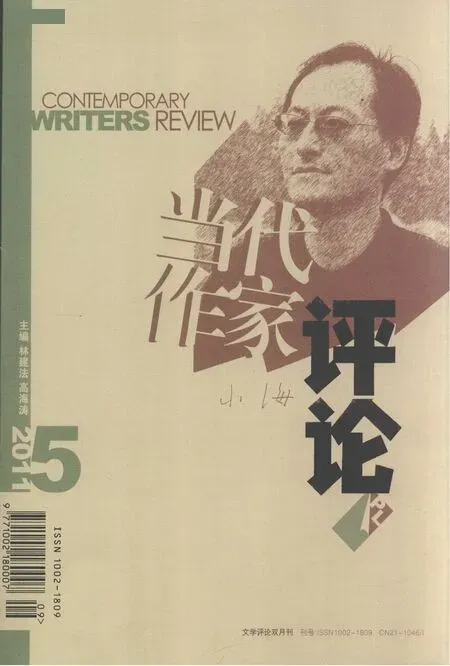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多”——对小海近期创作倾向的考察
何同彬
当诗歌想到它自己的自娱必须被看成是对一个充斥着不完美、痛苦和灾难的世界的某种蔑视,那么抒情诗那种活力和逍遥,它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品尝,它那快乐的张力等等,都将受到威胁。
——西默斯·希尼①〔爱尔兰〕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第241页,吴德安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分担诗人的痛苦
为一个成名已久的诗人写“新”的评论是艰难的,因为关于他们的研究和论述已经呈现出一种过度饱和的状态,弥漫着水果因为过分成熟而散发的那种甜腻又腐败的气息。所以如何接近一个诗人及其作品,对于如今的批评语境和批评者而言,将不得不采取或创造一种回避了虚与委蛇的更为尖锐、锋利的切入方式。既然布鲁姆认为每一种阅读总是一种误读,那我们就尽力去做一个“高明有力的读者”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第1页,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这种高明有力不是体现在某些“过度阐释”的文本细读或哲学联想那里,而是体现在布鲁姆所说的读者与作者之间如何确定“自己同真理的原始关系”、如何揭示和展露彼此的“痛苦”这样共有的困境之中。
在阅读小海近期诗歌作品的时候,我一直激励自己去做这样一个“有力”而未必“高明”的读者,尽管批评在哈特曼看来是“一种次要的流言蜚语”,但我仍旧希望我的莽撞但诚恳的流言蜚语能实现“读者是作者的幽灵”(巴什拉)这样一个“有力”的结果。在我梳理小海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早就有一位“高明有力的读者”如幽灵般地缠绕着他、逼视着他。从韩东一九八九年的《第二次背叛》②韩东:《第二次背叛》,《百家》1990第1期。一文和二○○五年他与杨黎、小海的对话③《小海·韩东·杨黎:关于小海》,《中国诗人》2005年12月6日。之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什么是文学上的“朋友”,什么样的批评方式才是“有力”的。那种“有力”不在于某些评价和判断的卓越的洞察力,而是“交谈”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愈来愈可贵的坦诚和“粗暴”。尤其在那篇“关于小海”的谈话中,韩东的咄咄逼人的提问和质疑,迫使一个温和的抒情诗人说出一些与他的抒情天分和诗性特质相悖的“追求”,一个天生的抒情者的脆弱在那一刻暴露无遗。也许如小海所说的,韩东是“他们”的“灵魂”人物。“这么一些年,我感到韩东对我的一种压力。”但小海无疑是“他们”中的异类,与其他人,尤其是韩东,在诗学旨趣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虽然韩东在《第二次背叛》中所忧虑的小海的“保守态度”和“现代思维环境中所处的不利位置”,在小海后来的创作中的确“应验”了,可应验的方式却不像韩东对小海九十年代诗歌“混乱”局面的尖刻评价那么简单。一个丢失家园的抒情诗人如何寻找家园,如何在失去返乡之路后构筑诗学的“家宅”,又如何在这个虚拟家宅的羸弱那里暴露自我的脆弱,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所有当代诗人甚至当代人的共同的抒情困境。
写作的途中充满了秘密,这些秘密都是“黑色”的。在特朗斯特罗姆的《途中的秘密》里: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的屋里——/一座蝴蝶博物馆。在小海的《屈从》中:一只鸽子落进黑土地/它也由此变成黑色,黑色的/尾羽,我见到无数的鸽子/不断落下/像刮起黑色的风暴。这黑色的“屈从”、这黑色的风暴是小海九十年代之后苦苦挣扎和探索的“足迹”,所有的黑色足迹形成一个抒情的漩涡,“像遭到串场河遗弃的漩涡/一个寒冷的漩涡,消失//一条狗,打扮一下,爬上岸”。这又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形成一种有趣的“互文”:如同深入梦境/返回房间时/无法记得曾经到过的地方/如同病危之际/往事化作几点光闪,视线内/一小片冰冷的漩涡(《足迹》)。小海九十年代的诗歌探索绵延至今,与他的近期创作一同结构为宏大的“黑色”背景下的“冰冷的旋涡”,或者“世界微缩成茅屋里的一豆灯光”(《题庞德晚年像》)。从小海当下诗歌中比比皆是的衰败和死亡的气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抒情诗人为了寻求灵魂在场的片刻宁静所付出的代价。想象力的“蝴蝶博物馆”可以营造语言的狂欢、抒情的自娱,却不能安顿抒情主体的焦虑和绝望,此时,越来越尖锐的提示频频发生:对于诗人而言,辨析并扬弃“自我”似乎是比品尝创造力更严峻、更紧迫也更无希望的时刻,虚构一种形式化或风格化的诗歌精神永远无法替代一个主体精神的建构需求。此时无论小海如何表达他的“自信”,如何通过他所谓的“反叛”、“自我怀疑”、“自我焦虑”来建构“国家”、“民族”、“古典”等诗学想象,都掩饰不住他在诗歌中无法控制的绝望,一个抒情诗人苦苦求索却又无处逃遁的绝望。韩东说小海九十年代的诗歌“混乱”,事实上新世纪以至当下才是小海诗歌创作最具多面性、也最混乱的时期。而晚近的《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是一次勇敢却“徒劳”的冲刺,一种结构的“企图”显现的却是一个解构了的世界的“荒芜”。也许一切如小海所说的,我们“在人世间陷得如此之深”,那个在《村庄组诗》的开篇埋怨“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少”的歌者,最终在顽固的日常生活面前不得不用诗歌“坦陈”:忠实于我的时刻越来越多!
以下的一种考察也许并不符合小海对批评的期待,或者恰恰带有小海所反对的那种“庸俗社会学批评”①小海:《回答沈方关于诗歌的二十七个问题》,《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的痕迹,但我不得已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小海认可的那种从文本入手的批评已经很多了,其中很多杰出的批评家对于小海诗歌的艺术面貌已经作了很精到的研究,我实在没有狗尾续貂的必要和能力;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面前,我既不信任诗歌,也不信任诗人,我更关心一个主体如何在冷酷又平庸的现实之中确认“自我”,喜欢发现并“分担诗人自己的痛苦”②“我希望,通过促进一种更加对立的批评,即诗人同诗人相对立的批评,来告诫读者:他也必须分担诗人自己的痛苦,如是读者同样可以从他自己的迟到中找到力量,而不是苦恼。”《误读图示》,第80页。,即便那也许仅仅是我延迟的误读的想象性“痛苦”。
抒情者的“疼痛”
小海因为对“村庄”和“田园”的书写,很早就被定义为一个抒情诗人,但人们在分析他的抒情诗的时候往往关注的都是那些围绕着乡村世界展开的作品,而小海在九十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大量的诗歌作品是和他始终无法割舍的乡土记忆没有本质关系的,这一方面是小海生活环境和体认世界方式的客观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诗人在成长和探索的过程中创造和尝试更多的抒情可能的一种不得不做的选择,有时候不是“好坏”、“成败”可以概括的。也许正如本雅明在分析波德莱尔的抒情诗的时候所说的,无论是抒情诗人还是“积极接受抒情诗”的那些读者,因为自身“经验结构的改变”,都在抒情需求那里谋求新的答案或新的途径,以面对陌生的环境③〔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第168页,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虽然小海对自己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非常自信,但从他不断尝试和改变诗风的“自我焦虑”、“自我怀疑”来看,他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新的抒情途径,仅仅是建构了很多用韩东的话说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譬如“国家的代表性诗人”,“诗歌民族化”、“承继着我国古往今来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独抒性灵的优秀抒情传统”、“中国的诗神”④小海:《面孔与方式——关于诗歌民族化问题的思考》,《人民日报》1999年11月6日,第7版。等等。这些诗歌远景的规划和小海的具体的诗歌创作无法构成有效的对应,似乎仅仅是他用来“辩护”的一些“说辞”,他事实上是比较绝望的,“我已经找不到你们/就像我找不到诗歌中抒情的力量/感悟的不能上升/飘忽的又如此颓废”(《错误》)。
也许小海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焦虑,他也不需要为自己设置那么多诗歌的“远景”,被“村庄和田园”抛弃了的小海的抒情质地仍旧如一只温柔的大手,一直在抚慰着他、“引诱”着他,只是这抚慰往往被小海误解为一种“新”的抒情需要,并试图为它找一个同样“新”的抒情形式。这只温柔而有力的手也许就是叶橹所说的:“它以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和回顾表现出一种智慧,在最平淡的事物中寄寓着内心的疼痛。”①叶橹:《心灵关注的朴实与诡异?——论小海的诗歌品质》,《中外诗歌研究》2000年第2期这种生命的“始终如一”的疼痛感和小海敏感的天性、平和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当他面对北凌河、面对村庄和田园的时候,那种抒情结构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无需雕饰的。小海对北凌河的回忆一如普鲁斯特对贡布雷镇的童年时光的回忆,这种形式的回忆被普鲁斯特称之为“非意愿记忆”②〔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第170页。或者“智性的记忆”。普鲁斯特进一步指出,“非意愿记忆”是一种特殊的过去,“在某个理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我们能否在有生之年遇上它们全仗一种机会”。对于小海和北凌河而言,他的抒情诗人的天才性赋予了他这种机会,当然,这种机会也不是永远驻存的。尽管小海认为自己的诗歌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什么“重要的分水岭”,但我却执拗地认为一九九六年的一首《北凌河》似乎在提示我们某种重要变化的发生:从“非意愿记忆”到“意愿记忆”,从“回忆”到“记忆”③“雷克写道:‘回忆功能是印象的保护者;记忆却会使它瓦解。回忆本质上是保存性的,而记忆是消解性的。’”《启迪:本雅明文选》,第172页。。在这首诗里诗歌情感的张力弱化了,一种缓慢而忧伤的抒情叙事凸显出来。更为剧烈的变化来自于那股中年式的感喟后面不断扩大的裂缝——横亘在小海和他的“故乡”之间。小海开始了正式的“返乡”,因为他离那里越来越远。他开始区别于北凌河里的鱼、海安上空的鸟和那些互掷桃核的情人们,他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北凌河》一诗不正是把自己从一个当局者变成了旁观者了吗?当小海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根”在村庄和田园、在海安、在那些日渐消淡的童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蜕变成了这一切的局外人了。在今后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中,小海的那种揣摩和观察世相的“对立”姿态已经非常明显,在新的生活和新的抒情需要那里,保存性的“回忆”没有了,而那些消解性的“记忆”纷至沓来,诗人只能被迫“反抗”,尽管最终只是反抗的内容、反抗的形式乃至反抗本身的瓦解。
“诗人倾尽一生的努力和心血,要用语言触及所有虚妄和现实的世界,去消除‘在语言和诗由以产生的情感之间总会有的紧张和对立’,建立起语言和命名对象天然的亲和力,获得词与物之间言辞意义上的和谐对应关系,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理想。比如我本人创作的《村庄》、《田园》、《北凌河》等系列组诗,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尝试。”④小海:《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访谈》,《广西文学》2009年第1-5期。在二○○九年的一次访谈中,小海自己认可的那种“天然的亲合力”、“和谐对应关系”的诗歌仍旧只能是那些“非意愿记忆”时代的作品,而那样的一个“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抒情经验的结构以及小海自身确立的与现实的那种暧昧的、“保守的”关系,决定了他晚近的作品的那种形式化、风格化的多元尝试的“混乱”局面。“就像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温热的泪水)/慢慢习惯,与残酷现实的联系/永别了,画境南方/再见吧,烟水江南/故乡,是雨水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铁钉”(《雨水是棺材上的最后一枚铁钉》)。故乡已经远去,在一种新的“混乱”的抒情格局中,它把主体推入绝望的“棺材”,“残酷现实”制造的疼痛把抒情诗人逼到死亡的绝境。那这一切是否是可以避免的呢?对于小海这样的抒情诗人来说恐怕很难,这事实上恰恰取决于他“与残酷现实的联系”,而并不在于他采取何种形式,以及试图建构何种风格。
小海晚近的诗歌尝试了很多形式和风格,长的、短的、宗教的、历史的、民族的、格言的、叙事的、怀古的、游历的、赠答的也发表了很多关于诗歌的观点和看法,这体现了一个抒情诗人持之以恒地寻找更“准确”的抒情方式的决绝,创造的狂喜或忧伤,会让自由更自由,也是诗人面对“残酷现实”所必需的“净化”方式。弗里德里希在评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时,这样评价“形式”的意义:“形式力量的意义远远超过修饰,远远超出适度的维护。它们是拯救的手段,是诗人在极度不安的精神状态下极力寻找的。诗人们历来就明白,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这便是通过将痛苦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而使痛苦净化(Katharsis)的识见。”①〔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第26页,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但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往往是非常艰难的,不会像小海表述的那么简单②“我希望达到的效果也是随心所欲而又不逾轨。或者更直接地说,我不希望我的诗中形式大于内容,我要求两者的有机统一。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应当在诗中看不到我的才能才好呢。因为才能常常会遮蔽掉许多东西。”《诗歌寂寞的力量——苏野专访诗人小海》,《华东旅游报》2006年1月5日。。要么形式压倒内容,要么内容压倒形式,在小海近期的创作中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它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表面的风格化背后的不可避免的混乱,以及苏珊·桑塔格在谈论“风格化”的时候所指出的,因风格化和题材之间的“距离”调整的不恰当而引发的艺术作品的“狭窄和重复”、“散了架”、“脱了节”③〔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23页,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等后果。韩东在二十多年前的《第二次背叛》中的提示似乎有着某种穿透历史的特殊洞察力,“小海仅凭个人天生的才能就把已有的形式发挥到极致”,因此“不需要创造属于个人的排他性极强的形式,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主题”。尽管小海有足够的理由采取新的形式,也有足够的生活的依据提供着必需的、新的题材,但这其中的“度”他控制得并不好,似乎过于“随心所欲”了。虽然抒情的疼痛在新的形式、新的题材中得到了延续,但这疼痛被一种铺张的“混乱”稀释了、耗散了,归根结蒂并不是新的探索的问题,而是小海与现实或历史的关系因为其性格和缺少戒备的态度,最终影响了抒情的“强度”、“力度”和疼痛的凝聚。
历史即现实
如今一种如此高密度的生活,对诗人而言实在是一场灾难,平庸的恶、赤裸裸的丑陋无处不在,一个诗人及其诗歌的力量被死死地压制着,此时一种悖谬的、无法化解的两难处境日益形成:坚决地抗争和彻底的逃匿都是毁灭,难道我们只能中庸甚至犬儒吗?不过,诗人或艺术家总是有一个永恒的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那就是对纯粹的诗和自由的追求,正如希尼所说的:“诗歌无论多么负责,总是有着一种自由无碍的因素。在灵感的内部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欢欣与逃避责任的东西。那种解放与丰富的感觉是与任何限制与丧失相关的。为了这个原因,抒情诗人从心理上感到在一个明显是限制与丧失的世界上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④〔爱尔兰〕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第229页,吴德安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但这种“辩护”必须要一个模糊却坚决的界限,人对现实感的过分逃离或过分沉溺对诗歌的威胁都是毁灭性的。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而言,艺术的理由一直在被滥用,结果是诗歌表征的繁荣与本质的腐败并存,但诗人往往缺乏足够的勇气,与这个浑浊的现实划清界限、表达对立,甚至采取冲突。这最终导致日常生活的暴政的肆虐,诗人没有未来感,只有一些空泛又密集的现实感,一些充满想象力却又贫弱的历史感。现实即历史,每一分钟的现实都在一分钟后成为空洞的历史。诗人对现实的屈从即是对历史的屈从,对历史的反叛却相反,成为对现实的逃离。
小海是一个温和而宽厚的人,他忠诚于写作,因此他对现实不满,但他对现实的要求不高,只需要更多的写作时间,需要一种“生活的稳定感”,所以他为了老婆、孩子、家庭不会辞职,他唯一的反叛是“写作”①《小海·韩东·杨黎:关于小海》,《中国诗人》2005年12月6日。。也许对于小海而言,并不十分需要一个外在的社会性的自由,他只要通过诗歌构筑一个巴什拉所谓的“圆形的内在空间”,一个抽象的家宅,“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并非只有思想和经验才能证明人的价值。有些代表人的内心深处的价值是属于梦想的。梦想甚至有一种自我增值的特权。它直接享受着它的存在”②〔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第4、5页,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但这种家宅会时时受到现实的“黑色风暴”的侵袭,维持一种强度极高的孤独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一个诗歌的抒情主体不能采取一种尖锐而锋利的方式面对强大的现实,那这个家宅的封闭性就是脆弱的,它庇佑的梦想也越来越缺乏有力量的情感和想象。小海晚近的诗歌有很多的“小疼痛”,都是与现实碰撞后留下的淡淡的伤痕,这些诗歌最晦涩的地方也即小海最孤独的地方,最孤独的地方也即他最疼痛的地方,但即便是最疼痛也是一些小小的疼痛:彷徨、游荡、忧伤、惆怅、无奈、绝望……这些诗歌是潮湿的,是梦想被过度饱和的水分浸泡后的软弱无力,它们尽管有足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力量,但却会让我们郁积更多的挫败感,会把小海和他的读者带向衰老和死亡。“窗外的葬礼/似乎将我压扁了/放倒在床上”(《窗》)。“从沙漠里的一具尸体,我认出了自己”(《从一开始》)。小海近期的诗歌越来越弥漫着这种苍老的氛围,他似乎没有勇气把那些小疼痛聚集成一种大疼痛,那样的大疼痛会逼迫他与这个黑色的现实“决裂”。但他也不甘于死在这种小疼痛之中,希望用一种诗歌形式的聚集来结构一个更大的家宅,以便更自由一些,更“稳定”一些。
《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是小海选择的疼痛的聚集方式,一种现实态度与历史意识的合谋、狂欢,最终疼痛不会聚集,而是裂变、分散,以至于消隐。至于小海采取的是“诗剧”、“史诗”还是“长诗”的形式,在我看来都不重要,用小海的话说,这不过是“游戏”。对于《大秦帝国》,我不太认同“英雄史诗”的评价,这倒不仅仅是文体界限的问题③我们对“史诗”的使用早就泛化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史诗”太多了,多到我们都无法确定一部达到一定长度和容量的作品“如何才不是史诗”。,关键是《大秦帝国》的那种强烈的后现代特征使得它更像是一部解构“史诗”的颠覆之作。正如江弱水在评价柏桦的《水绘仙侣》的时候所说的:“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发散式的‘稗史’(Les Petites histories)写作。其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暗含了作者对理性整合的现代秩序的反叛,而与后现代主义声气相通……中心被消解了,连续性和统一性被打破了,整体被解构为无数片断。柏桦用这样的抗拒一体化的尝试,把他反宏大叙事的‘养小’型思维发挥到极致。”④江弱水:《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读柏桦的〈水绘仙侣〉》,《读书》2008年第3期。小海的《大秦帝国》同《水绘仙侣》一样,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实际上是一些“养小”的思维,但这种“小”不会像江弱水认为的那样产生“思想的黄金”,与当下诗歌创作中越来越多的历史题材写作一样,只是思想贫弱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后现代的外壳,还是虚假的英雄浪漫主义外壳都有语言狂欢的一面,往往不过是无力面对现实之外的一种历史逃逸。
《影子之歌》同样有着明显的“历史”外观,而且与《大秦帝国》一样,对小海来说最重要的是“长度”和“跨度”,用长度和历史感培育一种新的“自信”,一个更大的家宅。但无论是史诗还是长诗,对当下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因为那种游戏、“养小”的思维无力维持一部宏阔的作品的始终如一的吸引力。爱伦·坡作为一个“高明有力”的作者和读者坚持认为:“一首诗必须刺激,才配称为一首诗,而刺激的程度,在任何长篇的制作里,是难以持久的。至多经过半小时,刺激的程度就会松弛——衰竭——相反的现象跟着出现——于是这首诗,在效果和事实上,都不再是诗了。”或者仅仅是“一系列无题的小诗”,伴随着“刺激和消沉的不断交替”。而对于史诗,他的评价就更加尖刻了:“纵然是天下最好的史诗,其最后的、全部的,或绝对的效果,也只是等于零。而这恰恰是事实”。“荒谬”的“史诗狂”“认为诗之所以为诗,冗长是不可缺少的因素”①〔美〕爱伦·坡:《诗的原理》,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第1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如今你还会重读海子、杨炼、昌耀、周伦佑那些庞大的长诗或史诗吗?我们的生活太冗长,冗长得没有尽头,最终导致我们对于长度、对于诗性往往缺乏真正的耐心,这对读者和作者是一样的。
韩东所忧虑的“保守态度”和“现代思维环境中所处的不利位置”,对于小海来说是命定的,与其早期的抒情诗人的确立相关,也与其近期创作的复杂、混乱相关。小海在工作上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写诗了,但他因此更孤独了吗?大量的书写、大量的展示只会损伤孤独,真正的孤独是有其“凄厉”、“邪恶”的一面的。小海是一个公认的“好人”,这对一个抒情诗人而言是可怕的障碍。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还想保护好亲人,维护与朋友们的关系……那么多的写给亲人、朋友的诗,那么多急切的短章,那么多庸碌的生活流,那么多塞满日常生活的短暂疼痛的吟哦,复活的是面目一致、整齐划一的“兵马俑”而不是“末日刺客”:“无畏,是因为丧失痛感/岁月不再眷顾/无法感知疼痛的一个孩子,一个士兵/贴着封条,出土/成功预言你的出生:——末日刺客”(《人物志:兵马俑复活》)。这个刺客只有勇气指向自身,兵马俑倒地,引发的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最终延迟或扼杀了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庄重地为孤独的‘自我’说话”的“强劲的”抒情诗人的产生。“白白浪费十年/被废话活埋/搬运风景的侄子/被敌人搜查到的文字/——最后的家”(《十年》)。“我老了,不再是一个人/曾经折磨过的人性/像随波飘荡的柳叶儿/在人世间陷得如此之深”(《宇宙的律动——悼念陈敬容先生》)。
自我戏剧化
当小海谈论“国家”、“民族”、“传统”的时候,韩东说他“反动”,“以老诗人自居”,表现的是“老了的心态”②《小海·韩东·杨黎:关于小海》。。在年初的一次聚会中,顾前说:我不愤怒了,不生气了,老韩(韩东)也一样,我们现在心态都很好!显然,韩东也老了,不复再是断裂时那个愤怒的人了,第三代诗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集体走向衰老。欧阳江河这样为“中年写作”辩解:“整体,这个象征权力的时代神话在我们的中年写作中被消解了,可以把这看作一代人告别一个虚构出来的世界的最后仪式。”③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第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但他们真的告别了吗?没有,他们与这个艳俗的尘世缠绕得更紧密了,告别只是一个仪式,一个不断开场、花样翻新的“戏剧”。在关于“中年写作”的论述的结尾,欧阳江河引用了孙文波的《散步》:“老人和孩子是这个世界的两极,我们走在中间。/就像桥承受着来自两岸的压力;/双重侍奉的角色。从影子到影子,/在时间的周期表上,谁能说这是戏剧?”可这的确是不断上演的中年人恐惧于步入老年的“自我戏剧化”。
艾略特在研究莎士比亚的时候,“指出了莎剧某些主人公的一个为人忽略的共同特点:在悲剧性的紧张关头,为鼓起自己的劲头来,逃避现实,于是出于‘人性的动机’,采取一种‘自我表演’的手法‘把自己戏剧化地衬托在他的语境里,这样就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悲剧人物’”①《莎士比亚与西奈卡的苦修主义》,转引自江弱水《抽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第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这在当代中国很多诗人的生活和写作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的诗歌与他们的生活不一致,前者存在强烈的“自我戏剧化”;他们关于诗歌的谈论、参与的诗歌行为与他们的诗歌又不一致,前者比后者的“戏剧化”更为严重。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无法回避自己在一个提前到来的艺术的晚期所遭遇的绝望、无助、衰败、死亡,这在小海近期的作品中俯拾皆是:“被击瘪的脑袋”、“灭顶之灾”、“和跳离的死亡不期而遇”、“漫天飞翔的/尸体上的白幔”、“枯萎的老妇”、“寿衣依然挂在风中”、“雨水棺材”、“你死后,夜降临”、“没有铁轨,把你放在我/枕头般的灰烬上”……随手打开一本刚刚收到的、“新鲜出炉”的诗歌刊物,诗行中同样是漫溢着“衰老”的诗人们的徒劳感喟,“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惭愧,徒然,忧心忡忡”(宋琳《给臧棣的赠答诗》)、“每个人都困于自己的处境里……/捕获同样的猎物/网住唯一的自己”(韩东《蜘蛛人》)、“性感的时间又一次朝我逼近/而那些孤魂野鬼/还在继续寻找着爱”(芒克《一年只有六十天》),还有唐晓渡的《哀歌》、梁晓明的《死亡》、朵渔的《唯有死亡不容错过》……可在诗人与尘世的拥抱中,这些“死亡”都是表演,这些“绝望”都是虚构,这一切都是梦境。如《圣经》中所说:你们中的年轻人将见到天国,而你们中的老人则只能做梦。
小海说:“悲哀、绝望也能带来‘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创作者是消解也可能是抗争。”②小海:《诗歌寂寞的力量——苏野专访诗人小海》。可对于一个读者而言,我看到的只有消解,没有任何的行动,一个诗人仅仅只需要“忠于自己的诗歌”吗?恐怕没那么“形而上学”。事实上,小海在离开“北凌河”之后,一直在寻找一个完满的、替代性的“自我”,以确立自己写作的目的和意义,只是这种探寻永远在一个夭折的轮回中。在《自我的现身》里,找到的最佳方式就是“禁闭自我”,“随后而来的,蚕食铁锹的雨水/而形成一个自我独自留在外面/无人问津”,“我为我所见的事物/现身”。在《秘密的通道里》,“许多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从睡梦中抹去/就像依然在草丛中游动的灯光/回复空寂的深处/——那通向自我的路上”。也许如小海所认为的,“诗人的自我定位解决不了诗人面临的根本问题,个人才能无论怎样发挥到极致也只是诗的一部分问题,因为真正的诗歌一直在那里。我对诗歌心存敬畏,我指望我在写作中消失,包括所谓的才能”①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 ,第884-8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但这种自我辩护的说法仍旧是一种回避,一种特殊的“自我戏剧化”。诗人一如诗歌,对于世界而言只是影子,而一个主体的自我问题事实上关系着诗人面临的“根本问题”。诗人绝无充分的理由进行一种威胁环伺的“抒情自娱”,而我们一直这样做的原因是过多地忠实于一种片面的、消极的“自我”。
克里希纳穆提认为,自我是邪恶的,“因为自我分裂性——自我是自我封闭的——的活动,不管有多高贵,都是分离性和隔离性的”。“对此你一定曾经扪心自问过——‘我看到‘我’始终在活动,并且总是带来忧虑、恐惧、挫折、失望和痛苦。不仅对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我周围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有可能令自我完全地而不是部分地消融吗?我们能够触及它的根部然后摧毁它吗?”②〔印度〕克里希纳穆提:《最初和最终的自由》,第66-70页,于自强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克里希纳穆提指出的方式是“整体性地有智慧”,是爱,或者统一起来讲就是一种“整体性的爱”。中国当代诗人往往因为怯懦,因为某种程度上的世故,在“自我戏剧化”的表演中把诗歌的功能封闭化、抽象化,这实质是对自我的溺爱,根除它的方式虽然简单,却很危险。希尼引用赫伯特的话说,诗人现在的任务是“从历史的灾祸中至少拯救出两个词,没有了这两个词,所有的诗歌都将是意义与外观的空洞游戏,这两个词就是:正义与真理”,写作“弃绝抒情品质的抒情诗”,“享受诗歌吧,只要你不是用它来逃避现实”③《希尼诗文集》,第229页。。在中国当下,诗人们在生活中失去的,绝不会在诗歌中实现,除非我们的诗人继续耽溺于“自我戏剧化”。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抒情诗人,这就是我可以与小海分担痛苦的原因,这种分担的片面(刻意回避了对小海那些抒情杰作的赞美)最终把诗歌的问题又扩张为一个关于“正义”与“真理”的问题,这种削足适履式的“误读”也许会让小海感到“厌恶”,但这的确是我“向心致敬”的粗鲁却诚实的方式:“这信仰的玻璃山/还有瑕疵/就无法漂浮起来/我害怕对镜/意味着要过/严厉而羞怯的一生/依然归于昏朦/我说过的话/摆脱的爱/变成了呼喊/和忍辱、死亡一样/活着是对诚实的测试”(《向心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