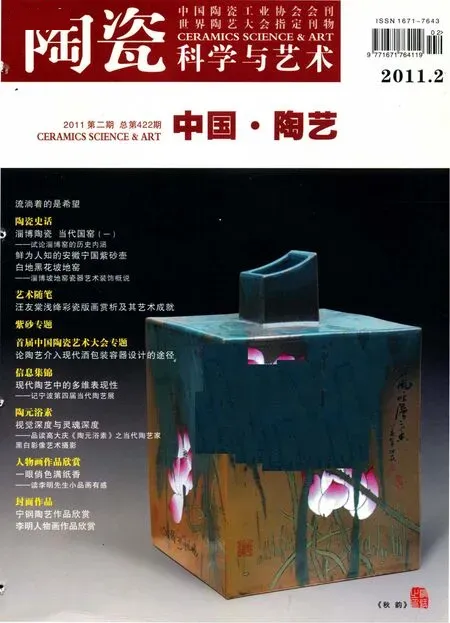归真返璞
——马士达先生印款摭谈
郑付忠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西安710062
归真返璞
——马士达先生印款摭谈
郑付忠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西安710062
我不想说马士达老师是篆刻家,因为我怕这样会掩饰了他其他方面的成就,但出于叙述的需要,又不得不姑且称马老为篆刻家。这个“家”不是自诩的,更不是沽名得来的,而是大家对马老历时多年的教学耕耘和对篆刻的潜心研究成果的肯定。马老在篆刻方面的一些观念在其印款里有明确的记述,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印款比印面更能综合反映和承载他的印学精神和学术价值。他拙朴苍茫的印款风格一反明清工整妍美的格调,印款与印面相得益彰,极大地提升了款识在篆刻艺术中的地位和功用。马老的印款觉醒意识给当代印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篆刻家;印款;学术价值;
我来自鲁西农村,选择艺术这个行业完全是出于喜欢,也算是“半道出家”吧。说来惭愧,那年夏天接到南师大(书法篆刻专业)入取通知书时,居然没听说过马士达老师!反倒是我一个老师的赞美之词让我欣喜:“你能考入南师大,真是很幸运啊,马士达先生在那里……”。我赶紧上网查询了一下马老师,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来到南京的第一年,有一次我去浙江美院,他们正在上篆刻课,我的贸然闯入让他们很不高兴。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来自南师,他们马上改变了态度,热情起来了:“你们南师大有个马士达,篆刻搞的真不错!我今天还看他的印章来着……”。这是我第二次感受到马老的影响力。作为一个艺人能做到让同行认可是很难的,让年轻一代认可就更难了,马老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人之一。
很多人都喜欢马老的印章,厚重质朴,不为繁饰之笔。但相比较而言对其印款的关注就不够了。作为一个篆刻家,马老的印学观在他的印款里有更为清晰的论述,而且由于款字刻在旁边,印面较大,更便于刊刻更多的文字,这无疑是其印学思想在方寸之外的绝佳延伸。
艺术家刻印款的习惯是近500年才有的事。明代中期始有艺人刊刻印款之事,且多用“双刀法”,先写后刻,可能是受刻碑的影响吧。可能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亦或是与款字抒发心性、应急刊就的需要相悖吧,继“双刀法”之后“单刀法”产生了。较早采用“单刀法”的人是何震,他不用写款,直接操刀,一刀一笔,挥刀如笔;乾隆年间丁敬刻款全“单刀法”,后蒋仁、黄易随之。应该说相对于“双刀法”而言,“单刀法”简便易行,更有利于抒情达意,但由于这时“单刀法”尚处于早期,一方面印人对刀法不熟,另一方面可能还与篆刻家对边款的艺术定位不够准确有关,故此时印款还有明显的“记事、记时”性质,所以总体上刊刻地比较整饬,艺术价值不高。虽然后来的赵之谦在印款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但也多出于形式的翻新,而没有凸显印款的艺术地位。清代西泠八家虽然也主张“印宗秦汉”,但过度理性的思维却使得他们的作品最终失去了生机,印款也没有太多可圈点之处。民国时期的王福庵,赵叔孺等人也是提倡“印宗秦汉”的,但王氏主要成就集中在其朱文印,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里说:“(王福庵)尤精于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者。”[1]赵叔孺也有“上窥汉铸”之誉[2],他们汲取了汉印流美的一面,专务小巧而失大匠风范,因此体现在印款上也同样是隽美一路,艺术价值远不足以与其印面相提并论,也可以说印款并没有从篆刻中获得独立的身份。
马老作为当代印坛的一员巨将,他具有高度的印款审美和意识和创作理念,把印款创作纳入到了篆刻美学的构建范畴,获得了印款和印面相辉映的高度统一,从而把印款从以往作为印面的补充和附加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所以马老是创造了印款美学的一个典型,并且由于边款空间的相对宽裕,给他进行印款创作、阐述其印学观点提供了很好的空间。所以对其印款的探究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印款一:
是作趣则已然入古,古者何是?盖言真朴。老马。(图1)首先,对于“入古”的问题在该印款中马老说的很简洁,只说“真朴”二字。这样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只道其风格指向而不明其根本。秦汉印章可谓“真朴”,如此则一味追仿“秦汉”罢了。马老并不是一个“守旧派”,他是有极强时代感和创造欲的,“醉心秦汉”并不是为了留住秦汉、复原秦汉,而是要“化古为今”,说到底,“入古”就是为了“出古”、“开古”这有点类似于李可染先生的“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理念。马老钟情于“入古”,但更着意于“创新”,他曾说:
我在今年五月患肺疾治疗期间,经常对艺术与人生进行思考,但更多的是对艺术的思考。书法家常常思考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总体归于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我认为传统是变化的、活的、发展的。巴蜀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说:“任何创造都是继承,真正的创造就是最好的继承。死守传统,做个孝子,只有给老祖宗送终的份儿,恰恰是最坏的继承。”以此语与大家共勉!王羲之书法好,但大家都写王羲之,哪怕水平再高那也俗,多而俗之。一个人就怕保守,人千万不要被尿憋死,应早一点学会自己做主。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继承是手段,而创新才是目的[3]。
言简意赅,这段阐述给我们年轻一代以重大启迪。其实马老的艺术创作理念是十分鲜明的,记得前几年一次观看展览时,马老指着一位学兄的作品说:“你看,你的作品放在展厅没人能识得出,我的作品不敢说好,但大家一看就晓得是我的。”这话当时听起来像笑话,细品起来确实马老对我们的委婉鞭策。
印款二:
刻印以工整见长者,多流于有手无心,予甚恶之。老马。(图2)
可能是我拙于见闻,到目前为止还不曾见到马老刻过“圆朱文”之类的“工笔”章,这也是他不太喜欢明清人治印的重要原因。马老“印宗秦汉”的核心旨意即他把秦汉印之“拙朴”、“率真”的意趣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气魄不是每个人都能为、都可为的。这个印学审美观可以从他的另一印款中(印款三)进一步看出。
印款三:
雅饰乃作印之大弊,时人多不知,故大失旨趣。老马。(图3)
这里所说的“雅饰”并非泛指篆法的装饰,它一方面指一些不必要的“繁饰”,比如“叠文”印;另一方面指一些无谓的“巧饰”,明清印人多有此弊。其实必要的装饰是治印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因为篆法本身就是一种装饰,细究起来马老的印作中也有“装饰”,不过用得绝妙,毫无做作之态。
印款四:
“马外公“三字已刻三过。此印异趣在不失真气,无恶俗气,无迂腐气。老马白。(图4)
马老刻印特别注重“真趣”、“朴拙”,而最忌“恶俗”、“谄媚”之气。这一点也可从他的书法中看出。马老书法喜做行书和隶书,有人会问,既然是篆刻家,为什么不写篆书?其实这是对马老的误解。我们看其行书用笔恣意率真,字势奇正相间、险趣横生,初看似蓬蒿乱飞,实则杂而不乱。可能有人会以为这是标新立异,其实马老的书法之所以“新奇”,关键在于他采取了“以隶作行”、“以篆作隶”的创作手法,他并没有把笔法与相应书体对号入座,而是在笔法上求“返祖”,在形式上求自得。因此马老虽然看似很少作篆,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篆书的旨归。此外,马老喜欢作隶,其隶书创作观是“务得古拙、朴厚,得古气”,忌讳甜俗、姿媚之风和柔弱平庸之气。其隶书不比汉简之流便,也无汉碑之完实,而是巧妙地在古拙劲爽的运笔中融以行草笔意,开阔洞达的结字中掺以砖铭、摩崖的率意。这种“师古意而遗古形”的精神气质在其篆刻中有明确的体现,可谓书印相映。我们看到马老的印章多有隶书面貌,这与他对隶字的钟情是分不开的。
印款五: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此作神趣,自谓兼得汉印铸之朴厚,凿之峻畅,菊山得之有幸也。予事篆刻重秦汉而轻明清,决非无故。盖前者自然质朴,后者多人为雕琢,难见真性耳。甲戌三月,士达。(图5)
马老是一个对篆刻艺术脉搏和时代走向把握非常清晰的人,他所说的“重秦汉而轻明清”一句话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马老是对明清篆刻的成就不屑一顾的,其实并不尽然。对于明清篆刻家好的方面他是表示赞赏的。比如丁敬是不满足于“墨守汉家文”的,其“思离群”的艺术精神马老就很认同。又如邓石如在篆书书写上的突破性进展和“印从书出”创作理念,就给了马老有益的启发。所谓“轻明清”者,很大程度上是批评丁敬、邓石如的后学,他们把明清篆刻引入了一个“死角”。关于这一点,马老在其《“印宗秦汉”辨析》一文中有明确表述:“可悲的是,丁敬以后的西泠诸家一味套用丁敬的刀法、印法,使之日趋僵化和装饰化,‘流’而为‘派’,导至衰亡;邓石如之后的吴让之、徐三庚诸家,则竭力继承邓氏的流美、婉畅,远离‘真朴’又陷入了‘媚俗’的恶道。”[4]
同时,马老对“重秦汉”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自古以来,篆刻家无不以“印宗秦汉”、“印从书出”相标榜,这似乎和书法家习惯于讲“书宗二王”一样,成了一种荣誉。
这些做法是有悖于创作实践的。马老曾对“印宗秦汉”有过详述:
作为一种艺术主张,“印宗秦汉”提出之初,含义并不明确。随着篆刻艺术的不断发展,这种主张也不断演变、不断丰满,逐渐确立为篆刻艺术的美学原则;整个明清篆刻创作风格史,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支配之下逐渐展开的。因此,对‘印宗秦汉’这一印学主张作一历史的考察与辨析,不仅是我们研究篆刻美学史所必须的,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明清篆刻艺术实践的认识,以指导现今的篆刻艺术学习与创作……就篆法而言,以秦篆为宗,汉篆通隶,唐篆古法渐废,宋后篆大谬,都是不足以为法的。但就印法而言,白文印以汉魏为宗,朱文印以唐为宗,因为吾丘衍认为“三代无印”,汉白文印、唐朱文印都是当时知识的最古范式。显然,在吾丘衍那里,篆法和印法是分离的,因此,他虽然有笼统的“宗秦汉”的主张,但落实到篆刻上,都是“宗汉唐”。以今人的知识,“印宗秦汉”的“秦”,乃是指先秦古鉨。但是在元明之际,人们并不认识古 鉨 ,以为“三代无印”,甚至将古 鉨 归录于汉印之后。这个误会,造成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宗秦汉”只是一个残缺的概念。直到朱简降世,独具慧眼,才道破了“印宗秦汉”的言之所指。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印宗秦汉”的明确提出,实是清代的事。[5]“印宗秦汉”在元、明、清各个时代人们的认知并不一样,由于认识上的差别造成了他们“宗秦汉”有名无实的缺憾,就像书法家说“书宗二王”一样,实际上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诠释和践行。“印宗秦汉”是一个庞大而完实的体系,是一种有益的创作指导观,而非一个教条的口号和对历史的个别人物和风格的对应。这种博取的情怀使得马老的印章既富有时代气息又不失传统根基,即似随意布局又能别具匠心,我想这也是他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吧
印款六:
古云:言易招尤少说几句,书能益智多读数行。丁丑之冬老马制。(图6)
正如所说,马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讷于言而勤于行的人。在一次访谈中她回忆1987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之初时说:“进校之初我不是万分欣喜而是万分焦虑唯恐力不胜任。怎么办?按古人‘书能益智’的训导,只能把读书作为应急措施和必由之路。”[6]

图6
我学习马老的一个惯常方式就是品读他的印款,我的体会也许并非马老所想,但通过对其印款的学习,我似乎获得了治印的一个全新理念,尽管这种理念还不够清晰,但已经足以让我品味一生了。马老的成功得益于他对艺术的敏锐感知,得益于他对篆刻艺术的痴迷和其人格的阔达,他的成功成为了启迪后学的一个典范。所谓“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是篆刻艺术的至高境界,也是马老鲜活的艺术生命的真实写照。
[1]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2]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263页。
[3]摘自马士达《2010江苏·新疆书法篆刻展——首届“龙神”书法家论坛》讲话,2010年9月。
[4][5]马士达《“印宗秦汉”辨析》,《书画艺术》2004年第01期,第30-33页。
[6]孙向群《老骥伏枥——马士达艺术生活访谈录》,《东方艺术·书法》,2008年第21期。
郑付忠(1982~),汉族,男,山东聊城人。本科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师从尉天池、马士达等老师。现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艺术中国》杂志特约记者,论文曾先后发表于《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赏评》、《金陵书画》、《中国文物报》、《艺术百家》、《艺术中国》、《艺术探索》、《青少年书法》计十余篇,入选“全国首届楷书论文论坛暨名家邀请展”,书法作品在《书法导报》作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