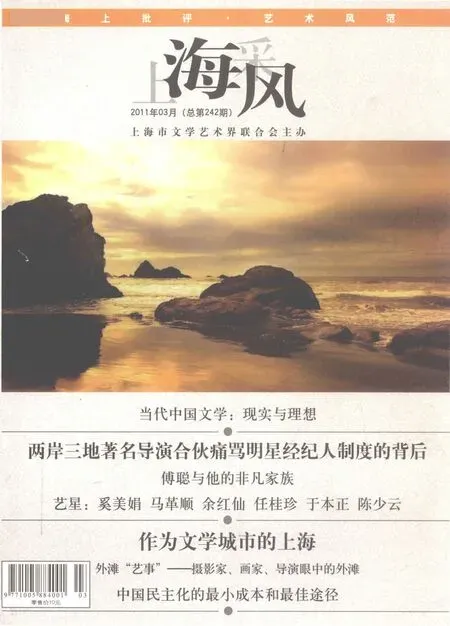一个文学流派的消逝
文/金 星
一个文学流派的消逝
文/金 星

“山药蛋派”主将胡正
从报上得知,作为“山药蛋派”的最后一位主将,作家胡正已于2011年1月17日在太原去世,享年87岁。“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领衔人物是赵树理,紧随其后的是人称“西李马胡孙”的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和孙谦。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都有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和共同的艺术志趣及追求,一时佳作迭出,颇受广大农民读者的喜爱。胡正的代表性小说有《奇婚记》《汾水长流》《几度元宵》等。但随着他的离世,已在文坛上淡出许久的“山药蛋派”恐怕是真的要画上句号了。倘若由此及彼,消逝的又岂止是一个文学流派。
西风落叶之叹,看似无奈,但更多的应是一种怀恋。“山药蛋派”这一称谓,确是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但集结在这一派下的作家都有着难能可贵的朴素而真诚的农民情结,这就超乎了一时一地,即使时至今日,也值得赞叹与推崇。他们没有发表过什么明确的创作宣言,但在写农民看得懂的书(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和出农民买得起的书上,却是有着惊人的一致。赵树理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不想上文坛,只想把自己的作品挤进庙会上摆满《封神榜》《施公案》《三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和两三个铜板一本的小唱本的小摊里去,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说、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如此清醒而自觉,这就使他们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深切关注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在体验生活时从不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而是努力成为“生活的主人”。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尤其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时,都以农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从而使作品中的人物与思想始终来自所处生活的底层。当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山药蛋派”的诸位作家在语言的运用上虽各具个性,但都有着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特点,“说书一般”,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的作品吸引住了。孙谦在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惟妙惟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所以,像《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三里湾》这类既深刻反映时代又影响深远的作品,显然都是创作者忠于生活而又对家乡父老的最真诚奉献。
自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任何的文学流派也总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应该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山药蛋派”的辉煌时期,但解放后,一些作家的农民立场或民间意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品的影响力渐趋减小。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出自山西的一些青年作家在起初也大都以农村题材见长,如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一度被称为“小山药蛋派”。但也许是世易时移,他们的创作虽很见功力,可作品的影响或感召已明显不如前辈作家,于是,悄然改变或貌合神离也就成为大势所趋。久而久之,兴趣的转移,热忱的消歇,加之越来越多原本出身农民的作家不断地“洗脚上岸”,“山药蛋派”文学风光不再乃至日趋沉寂也就不难想见。与此类似的,就有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新时期以来四川在农村题材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自从领军人物周克芹英年早逝后,也是鲜有这一方面的大作。艾青有一句很有名的诗,那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一片土地爱得深沉”,可像他那样对脚下的土地俯首向心的诗人或作家已经不多见了。单就“要出让农民买得起的书”这一点,如今的作家就已与当年的赵树理诸人大为不同。出身农民并以农村题材起家的贾平凹曾多次写到自己年少时喜爱看书,有时为了向人借书而不得不忍辱负重。但据报道,他于去年11月出版的总数21卷本的第三套文集,竟是创下了2980元的天价。正走在致富路上的农民兄弟估计是很难消受得起的。凡此种种,不断地两相背离,终究可哀的就想必不只是一个方面。
胡正人虽已去,但言犹在耳,他曾谆谆告诫道:“写农村题材小说,自然要熟悉农村生活,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干部。同时还需了解农村政策,了解现行政策,过去的政策,并且还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想到以后的发展。因为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干部,不能不受政策的影响,人物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政策有关联。写农村题材小说也就必然要考虑农村政策问题。”如此金玉良言,倘铭记在心并勉力而行,或可继往开来。
——关于戏曲流派传承的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