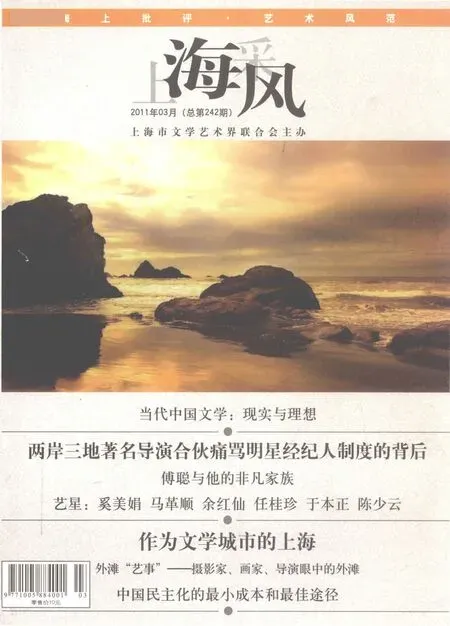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
采编/刘莉娜
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
采编/刘莉娜

2010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文学大系丛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精选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活动过的270多位作家的近6000万字代表作品,汇编成131卷。这套在世博年出版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可以说充分展示出上海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志向与视野。近代以来上海文学曾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繁荣的城市发展吸引了许多重要文学家长期聚集,成为“中国文学的大码头”,移植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结合使上海文学成为一股巨大力量。
众所周知,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南移,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峰期,其余脉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就如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所喻,“那是一次文学地质层的造山运动,移来或就地崛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或最奇特的一些峰峦,如鲁迅、巴金、施蛰存。有的作家虽然后来如大雁离去,但雁过留声,他们在上海创造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如茅盾、郁达夫、丁玲、叶圣陶、钱锺书、张爱玲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几乎都集中在海拔几乎为零的小小的上海版图上,仿佛要通过长江的出海口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世界。”这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地理学上的奇观。
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文学不再占据领先的地位,由于新中国定都北京,首都吸引和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在文学上同样执其牛耳。当时的文艺政策继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因此基本上以写工农兵为主,讴歌共产党、讴歌新中国、讴歌革命英雄主义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主旋律。然而,包括上海作家在内的所有中国作家,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受狭隘的文艺路线的支配,都被要求为政治服务,因此那一阶段在上海的文学地图上少见名山大川,多的是高低起伏的丘陵与沼泽地——但与除北京以外的区域文学相比较,上海仍然可以称之为文学发达的地区。
再看八十年代以来的上海文学地图,近三十多年来上海地区创作精力最旺盛、产量最高的是“知青”出身或比他们资历较早的一批作家。他们受全国性的反思和创新的文学潮流的影响,同样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等阶段,在艺术上逐渐形成写实和先锋等多元的格局。更多的作家在叙述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历史或现实时,从一个具体的阶层个体、里弄、单位切入,注重具象和细节,显得更具文学性,但往往被指责不够大气或未能直接反映城市变革的大现实。前者涉及创作格局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敏感性或文学功能的问题,多数上海作家不愿意作配合形势的宣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震撼人心的作品,艺术上的创新也相对薄弱,作家的人数不少,但整体水平不如北京、南京、武汉、西安等地。
但上海是有信心的,或者说,是自信。在经历如此潮起潮落的大背景下,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联合主持并策划编纂的这套《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可谓应运而生,很快就在专家和学者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的讨论,正如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所说,“一个城市面积有多大,多么珠光宝气,都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一个城市真正站得住,应该有巨大的文化底蕴。出版《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其实就是在创造、积累或者培育上海城市文化上可以‘压仓’的东西。”
诚然,一个城市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压仓”是非常难的,一套文学大系的出版虽然工程浩大、意义不凡,但如果由此我们还能得到更多的思想碰撞,得以擦亮一面镜子,找到一个方向,就真正是完满了。
上海与中国文学的都市书写
中国的都市书写一直面临着多重难处。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则常常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国外优秀小说即使有乡土文学传统,都市题材也从来没缺位过,如狄更斯写英国中下层市民,巴尔扎克写巴黎“上流社会”,德莱塞写美国的进城妇女……而对于有乡土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学,都市题材小说在主流文坛的位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现代都市的组织形式和交往方式培养着上海市民新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现代出版、交通以及电讯等新的手段的介入又使得这种新的市民观念和情趣普及化,其“现代性”的特质吸引着各个学科和领域学人的目光。从文学角度讲,“都市书写”是上海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样,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上海书写”则更是都市文学中的重要一环。
当下的上海都市书写,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作家群体:以王安忆等为代表的中生代作家,他们更多地关注社会性都市,其写作的社会含量比较丰厚,社会批判性比较强;以棉棉等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更多地关心个体性都市,其写作的个体感性含量比较重,对都市主流文化——市民型消费文化有一定反叛;以于是等代表的“70年代后”作家,他们更多关心消费性都市,其写作对当下都市消费性指认比较明确,认同度也比较高。此外还有部分来自外地如今寓居上海,以边缘叙事的态度面对上海的作家,这部分作家对上海都市生活的封闭性、排他性、与中国土根文化的差异性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这些也因此成了他们描述的重点。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之一,是中国都市文化的重镇,应当说,它也是当今中国的都市书写的重镇,就许多方面而言,它处于中国都市书写的前沿,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文学自觉,也不等于说,它获得了批评界的同情式理解。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我们少有看到对都市持肯定态度的正面描述者留下成功范例,反面的倒是不少。20世纪上半叶的新感觉派,他们对都市的感受是矛盾的,海派都市的繁华、热切让他们着迷,但是海派都市的重商、物质、快变、骚动又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对都市保持着既爱又恨的感觉,最终后者占了上风。20世纪中期,典型的都市叙事的代表作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作品中,都市是诱惑性、腐蚀性的,它是革命精神的对立物,这里充斥着使革命者堕落的种种危险。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生代作家开始正面描述都市生活,如卫慧、棉棉等,他们有些是农村出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毕业留在都市,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都市中的余零者地位,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变型、由封闭社会向全球化开放社会转型、由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向社会商品意识形态主导转型的关节点上,新生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关节点上,并不能真正融入急剧变革的都市生活,他们大多成了都市新变的旁观者和多余人,因此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观察是有保留的,带着和20世纪初启蒙作家相似的思乡病。如今看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给中国的都市书写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成功范例和经验。
最近以来,韩东、毕飞宇、红柯、李洱、魏微等向乡村叙事转型,并且在乡村叙事上获得重大突破,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新生代作家虽然大多以都市叙事出场,最后却大多只能在乡土叙事中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成功的都市作品,但是,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玉米》、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乡村作品都堪称杰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观察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视野理解都市。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和茅盾的《子夜》,形成互补。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在中国城市经验中,采用史诗性写法的,《子夜》是规范,是标准;而张爱玲虽然缺少对城市的宏观把握,但她最大的贡献是把上海写“活”了。而今,张爱玲的衣钵有一些人在努力继承,但还没有出现一个代表;而《子夜》这种史诗性的城市文学作品却更加后继乏人。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福布斯咒语》跟《子夜》的结构很像,写新世纪资本运作的结构转变,可作者王刚生活在北京。
以《子夜》开篇吴老太爷进城的细节为例,当吴老太爷看到黄包车上被风吹起旗袍露出大腿的女人,一下子崩溃了。茅盾通过一个细节就把当时城市的感觉写出来,写活了。现在的上海作家,绕来绕去的很多,那没有一种真正对都市人性的体察和都市状况的体察。《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死去时,上海事实上没有死去,而是重生了。现在的上海,有无数“王琦瑶”的孙女在大街上活动着,像狐狸一样。可对上海城市生活的新形态,很多作家都缺乏整体社会结构上的把握。
上海与中国文学的南方写作
中国文明一直是以北方文明为主导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因为诸子百家及儒家的兴起而兴盛,中国古代史上,北方文明的影响随着氏族贵胄的南迁而逐渐向南方浸润,最后逐步在中国文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南方文明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现代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即使是以南方人为多数的现代文学作家们,其写作的北方性依然是明显的。解放以后,普通话的推广更是造就了北方方言及北京语音的一统天下,使得写作上的南方几乎消隐不见。
然而上海文学的存在,让我们终于可以追问:是否在中国,有着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南方文学?一种南方精神的文学、南方审美的文学、一种南方意识的文学?也许是肯定的,也许是否定的,但是,只要上海文学的存在让我们有如此之问,那么也许上海文学就是成功的。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从当代上海作家开始一直追述到钱锺书,乃至更早的南方作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书面语写作应该是南方知识分子确立的。可是最近我在做一个关于《围城》的调查,发现它里面的人物身份包含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但进入小说之后,他们都不说或很少说自己本乡本土的话了,而是跟作者一起(或者说被作者安排着)“学说”中西合璧南腔北调的“国语”。他们不是自然地说着本乡本土的方言,乃是基本放弃各自的方言土语,学着说作者要他们说的话:正在生成中的超乎方言之上的新的民族共通语(官话)。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看,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本来应该作为国语运动中坚的北方作家,因为自身方言被容忍的方便,以及历史上共通书面语与北方方言天然贴近,而倾向于方言文学;加上1940年代以后延安方面的大力提倡,不仅来自北方的作家如赵树理等纷纷归回自己的方言世界,一些南方作家也放弃“五四”以来确立的现代白话书面语写作传统,转向方言写作的新范式。主要以北方方言为根底的乡土/方言文学,由此长期占据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个势头虽然在1950年代大力推广普通话之初有所遏制,但直到1990年代新的都市文学崛起,在从小接受普通话教育的新一代作家身上才真正有根本的改变。与此相反,国语运动中本来处于被改造被压抑地位的南方作家,却依靠千百年来成熟的共通语(官话)写作传统,同时也借助这个群体所处地域在近代以来日益显著的经济文化优势,成为“五四”以来“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中坚。为现代国语书面语做出更大贡献的不是北方作家群,而是南方作家群,但后者因此不得不模糊乃至大量放弃自身的方言土语资源,成为在方言上无所属的作家群,他们在写作中更多学习和创造中西合璧、南腔北调、超乎方言差异的现代中国书面共通语。
虽然南方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上有一个很特殊的贡献,就是统一了文学的书面语,但在确立北方话为国语时,虽然作品还是不时出现,但他们已经交出了“方言主权”。将来作家用方言写作的身份可能会越来越模糊,等到贾平凹这一辈人过去以后,将来还会不会有很纯的方言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保留下来,是当今文坛需要急切考虑的问题。
葛红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北方和南方的对立。例如,北方文明的壮美系统对南方的秀美系统、北方的政治主导话语系统对南方的休闲生活话语系统等等。这个对立,我们可以从当初赵树理写作的南方影响中看出来——左翼领导人从解放区带来北方气息的赵树理作品,南方上海作家立即无比佩服。这种佩服是哪里来的呢?难道真的存在一种生活上的真理性的北方高等级?一种语言上的真理性的北方高等级?不是的。正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流露出来的潜意识一样,南方都市的生活及语言,被低估了,甚至被看做了真正的中国式写作的反面。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发祥地,现代白话小说诞生在这里,现代绘画艺术也诞生在这里,现代印刷业传媒业主要也集中在这里。《海上花列传》,一部用上海话写的小说,几乎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肇始之作。但是,我们发现,上海的写作此后并没有被当做中国写作的典范,甚至命运恰恰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海上花”式的写作是不成功的,即使是张爱玲,她那么喜欢上海和《海上花列传》,她也不得不有所保留,她甚至担心别人根本看不懂,要把《海上花列传》翻译一遍。
这里体现的根本问题是风格和语言的割裂:文学上的中国有两个,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北方的;南方的中国成了支流并逐渐断流,使得南方中国的审美不被理解和接受。南方的方言写作,如今已经不再存在——这是整个中国地方性写作不再存在的一个缩影,但是,显然,上海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上海文学的存在,让我们依然可以问:是否在中国,有着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南方文学?一种南方精神的文学、南方审美的文学、一种南方意识的文学?也许是肯定的,也许是否定的,但是只要上海文学的存在让我们有如此之问,那么也许上海文学就是成功的。
“海上文学”与“海派文化”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展示出有容乃大的胸怀。工商业发展,出版设备优良,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学家首选上海作为聚集地。文学家沈从文就是一个特别的代表:沈从文在上海居住三年多,小说产量却占毕生创作的三分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洪涛指出,上海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彻底改变了沈从文的创作面貌,使他获得了国际一流现代作家的称号。
而作为中国现代化典范城市的注脚,上海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史,更为中国思想者提供了认识都市文明的材料。从乡土文化过渡到都市文化,上海在全球化进程中展出的地方性经验,意义重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作家,在极短的时空范围内一下子聚集起来,这就是现代化城市展示出的巨大文化生产能力。当然,有时候流动性对文化不一定就是一个长处,并不是不同地方的人汇集在一起,这个地方就好,有时候我们亦应该反思过于流动性对文化积淀产生的影响——如果没有文化积淀,那一个城市的文化就会像“无根的移民聚在一起”。
王纪人(上海师大中文系教授):“海上”是近代上海的别名,如近代作家韩邦庆小说《海上花列传》第一回:“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这里所说的“海上”就是上海,当时习惯上都喜欢这样说,“海上文学”指的就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正如“海上画派”是指近代上海画派。但海上文学不等于海派文学,它所覆盖的面远远超过海派文学。可以说,囊括了在上海地区曾经产生的所有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是后来成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他在上海时期写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我认为都是“海上文学”。海上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因此,海上文学并非仅有上海籍作家所创作,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出生在上海的近现代作家仅有张南庄、陆士谔、朱瘦菊、陈伯吹、傅雷、张爱玲等人,人数在《文库》中占第三位,人数最多的是来自浙江和江苏的作家,其他来自四川、广东、安徽、湖南、福建、东北等地。可以说,海上文学是由上海本土的作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共同创造的。
较之以往,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具有震撼力的作品,这始终是大家的一块心病。但我相信,随着上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作家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大气、汪洋恣肆一些,甚至脱胎换骨一番也是可能的。移民作家的进入将会改变作家群体的固有结构。回想一下三十年代,那么多移民作家从乡村、小城涌入,或海归,不仅使上海的文学地图大为改观,也利用上海的文化优势使自己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星空上的巨星。当然,如果想赶上三十年代的红火,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李伦新(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新崛起的中国大都会。他和传统的城市,比如西安、北京有所不同。因此这个城市的本身接受了内地的移民所带来的各地的地域文化中先进的部分,同时也吸收了更多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海派文化,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它来者不拒,但是又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创造新的东西;它也不是照单全收,它有自己的选择,在选择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它是很创新的,不是墨守成规的,同时它的文化又不排外,因此它见到什么新鲜文化都可以吸收进来为我所用。可以这么说:什么叫海派,海派就是无派,无派就是海派,因此海派文化的本质就是无派,海派无派但是有文化。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如果说欧洲哪个城市是移民城市,那个城市有身份的人会觉得这是对他们城市非常不好的描述;但我们说到移民城市的时候,好像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在中国,我们总是以为移动是好的,固定于一个地方是不太好的。实际上不是。有时候流动性对文化不一定就是一个长处,并不是不同地方的人汇集在一起,这个地方就好,有时候我们应该反思过于流动性对文化积淀产生的影响。如果没有文化积淀,那一个城市的文化就像“无根的移民聚在一起”。的确,有一些移民为主的世界大都市,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自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上升社会,外来移民都会慢慢向那个社会靠拢、依附;但上海还没有真正形成像巴黎、伦敦这样的社会成熟文化,所以上海只有真正形成自己一个文化积淀,才能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优势。有时候拘居于一地也很好,有的作家过着非常封闭的生活,例如哈代和勃朗特姐妹,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家乡为基础,照样富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城市化进程的得与失。我有时候想,与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相比,上海的历史还短了一些。上海历史上没有真正的上流社会,如果巴黎只有众多的于连而没有贵族与教会,那将如何?假如一个都市的文化可以比为一条巨轮的话,那么船舱里必须有一定分量的压舱物,这样大船才能平稳航行;没有这些看似多余的压舱物,轮船就非常容易倾覆。我们要问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巨轮上,是不是已经装载了适当的稳定力量?
从另一个方面说,文化的过于移动会导致小地方的文化滋养被城市精英文化冲淡,比如美国文化,真喜爱它的人就会觉得美国文化的精华不一定在纽约,尤其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南方的庄园文化里有很多代表人物,比如华盛顿、杰克逊,他们有很好的私人图书馆,他们跟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些在当时的纽约就没有。像美国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中记录的,很多乡下人到了纽约,纽约有很多机会,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当了作家、做了演员,但他们在人性等很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能是失败的。其实中国小说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中国原来的小地方文化的滋养是很丰富的,但随着城市化发展,我们发现小地方文化的精英慢慢被冲淡,慢慢集中到流动的城市去,流动到所谓的海派文化中去——其实所谓京派文化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中国文学在世纪初的时候发生巨变,集中到大城市演变成多元文化,这也许恰恰是我们应该反省的。
葛红兵:上海文学在全人类的都市化进程中,提供了特殊的东方都市化类型,上海文学呈献了左翼创生、发展、高潮、极端化以至于消隐的经验,东方都市现代性描写的经验,东方都市文化亚文化描写经验,现代都市启蒙文学经验,现代都市消闲文学的经验,等等。上海作为文学类型:它让我们知道上海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都市——地方知识依然存活,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而且提醒我们要用相对性的态度,从其内部来理解它,而不是从其外部,用外在逻辑去解释甚至规训它。因为正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国家在“现代性”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留下了空间,这种多样性的空间里驻留着我们自身的祖传,一种文化基因,呈现着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独特的理解世界、展现世界并和世界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