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铁生神侃
邢 仪
与史铁生神侃
邢 仪
我和史铁生是中学同学。1969年我们一同去陕北插队。史铁生在陕北干了两年农活养了一年牛就生病回京,惊人的消息传到我们干活的大山里,说史铁生瘫痪了。后来史铁生为活下去找个理由是写作。人活着总得有点意义,我们那会儿干什么事都要问意义,不像现如今干什么都问能给多少钱?所以当史铁生不能“战天斗地”后,他从追问自己如何残疾却不苟活,直追问到生命的终极意义。如果说生命是上帝(说神也好、自然也好)的杰作,他一生在与那个创造者对话。史铁生的身体在炼狱,史铁生的头脑在天堂。
感恩上帝,让我做了史铁生的同学和朋友。我们几十年在这个世上用健全的腿,跟着世俗,随波逐流。是他忍受着炼狱般的身体,用心灵“诚实、善思”,为我们在头顶点燃一盏灯,一盏通向“爱愿”的永恒之路的明灯。
第一次看到史铁生的文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叫《午餐半小时》的短文登在西北大学简陋、粗糙的校刊上。时至今日我都清楚地记得,我被文中那份真实和人性像子弹一样射中了。从此史铁生的书就是我的最爱。
近些年史铁生的身体每况愈下,近些年史铁生的哲思愈加的空灵和高远。
近几年与史铁生的聚会和神侃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
我们哭铁生,不是因为他走了,而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他。
一
史铁生一周透析三次,透析后第二天上午还好,他要看点书,还要写点文,这个时间得留给他。午饭后史铁生已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傍晚前后他又有一小段时间状态还好。他的时间真的很少很少。以前大多数时间,我们与史铁生在他的水碓子的家见面。他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地摇着轮椅迎接我们,为着能与我们聊天的一个半个小时,之前史铁生要躺在床上养精蓄锐大半天。
2009年的4月,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去见铁生。我们一一与他握手,落座后问他的身体。他调侃说医生预计他只能活到四十岁,已经赚了二十年了,够本了。现在又查出乙肝、丙肝(透析过程中被传染),不管它了,都没关系了。铁生说他鼻子以上,脑子非常好,一点没坏。以下都坏了,给别人捐献器官都不能用了。又看看我们羡慕地说:“你们的器官还能捐献。”
我先提出想说的第一个话题,我说,活到这个年龄慢慢悟到:其实精神就是物质,因为精神也有能量。不要以为信仰是虚的,信就有。
史铁生马上表示赞同说:“有人以为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爱情是什么呢?人不是什么都能看得到摸得到的,精神力量太大了。”
我提出最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我说我对人的生死问题,人活着的意义什么的,百参不透,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史铁生很注意很有兴趣地听我说下去。想到史铁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说过:“当别人问到我曾想过的问题时,我就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也许此时他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说我怕死。
他问我:“怕死的什么?”这个问题我问过许多人,没有一个人如此一针见血。史铁生曾用几年的时间把死的问题好好想过,他在《病隙笔记》中这样写道,怕死的心理各式各样,有人怕地狱是真,有人怕天堂有诈,有人怕来世运气不好。
我说,怕没了。史铁生说:“没有没了,不可能没了。‘有’,怎可能没?佛家说的“空”,不是无。”
见我懵懂,他掰开揉碎讲给我听,“你想你死了,去了一个没有的地方,没有的地方怎么去呢?再说,一旦你去了,那个地方就有了。不是吗?”一番努力后他说道:“这太深奥了,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个体的意识没了,但集体的意识永恒。”
我说关键是接不上,接不上我怎么知道我的灵魂一直没死?我还说,我从小就问自己我是谁?史铁生说:“我以前也问这个问题,现在问的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是史铁生?为什么不能是别人?”
二
铁生曾说,植物多动物(高级动物)少的地方就是好地方。于是近两年我们常接史铁生到“植物多动物少”的位于郊区的我的画室来玩。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瓜棚下吃自己包的饺子,大家都说这是何等的享受和自在。然后史铁生回到屋内躺着,我们大家则把椅子拖过来围着他神侃。
我说:你认为人在世上只活一次吗?
史铁生说:我不这么认为。你看人是从虚无中来的,死后又回到虚无中去,你怎么肯定你只来过一次呢?你如何知道你没有来过两次以上呢?虚无是什么?虚无不是无,虚无是你从这个角度看不见了,只是角度的问题。
我说:在网上看过一个东西,说我们的外面是一个大宇宙,但如果从我们手上的一点看下去,那里面的微观世界也是一个大的宇宙,所以说我们只是站在中间这个点上,站在这个角度上。
铁生说:我们活着就永远是站在中间这个位置上的,死了是不在这里了,但不是无。既然有就不会没,事物是循环的。人其实也一直在变,没有固定不变的你,人体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会替换一次,旧的细胞死去,新的细胞诞生,几年以后一身细胞全部换掉。也就是说,在生理上我们每过几年就是另外一个人。最终不变的可能只是你的记忆,人活着只能证明记忆是连续的,人死是记忆的中断。记得有个哲人说,学习就是回忆。
铁生夫人希米接着说:是柏拉图说的,学习就是回忆。
三
2009年的三九天史铁生闯了一次生死大关,着实把朋友们都吓坏了。2010年的春节史铁生夫妇都是在医院过的,铁生患了肺炎,高烧不退,医院下了病危单。天气转暖的时候,史铁生居然病愈出院了,死神又一次放过了他。
于是在史铁生去世前的一年里,我们又有过几次与他在乡村的聚会。
史铁生跟我们聊绘画、聊电影——
他的眼睛一直看住挂在墙上许多画中的一幅:是三个女知青张嘴笑着在延河大桥上的留影,人物和远处的宝塔山都沐浴在金黄色的晚霞中。史铁生对我说:“这张画你好好留着,我愈看愈觉得那感觉太对了,就是那种单纯的没有一点杂质的笑,那时的我们就是这个状态。”我说:“事后人们说插队的种种,比如流放,比如政治的权宜之计等等,可我们当时是浑然不觉,所以才会有那种没一点心眼的纯粹的笑。”
史铁生说:“只要是人们围在一件作品前说三说四,这件作品就是人们关注的好作品。”他又说:“以后你就画这个题材,时间情节都可以错位,比如画知青拉犁,可以叫‘纤夫曲’。一幅一幅画下去,十年八年地画下去。你现在这样的退休状态是最好的了,什么也不为,只是自己想画,卖不卖不用管,只要有饭吃就行。”然后他又特意加上一句:“你每画个五六幅就把我们叫过来给你看看。”我最高兴听到的是他说的这最后一句,我真的希望我总是在画,总是能叫他们来看,总是能叫史铁生来看,那该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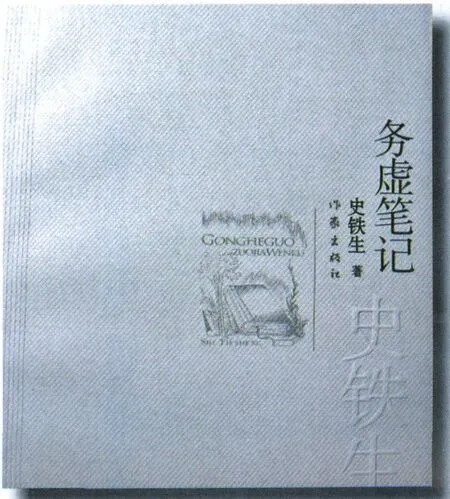
四
那是最后的聚会,傍晚我们来到位于顺义的意大利农场。夏末,天空蔚蓝,太阳给出最后的金黄,温暖地洒向大地,果园墨绿,草坪散发着清香,小狗在撒欢,小孩在嬉闹。史铁生问我:“能抽烟吗?”我环视了一下四周,草是水绿水绿的也没见什么禁止吸烟的牌子,就说,抽吧,没事。史铁生点燃一支烟,我们对视了一下,他洞穿我的欲言又止,平静地微笑着说道:“我们等着吧,等我们走到那儿,就会知道那边是什么,反正不是无,放心吧,没有‘没有’的地方。”
现在想来这是他最后给我的安慰和启发,我心领神会了吗?
那天,我们和史铁生像是坐在天堂里的一处,安心、放松地围坐在一起漫天的神聊。我忘了别人都说了些什么,我记得我跟大家聊到最近看的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这本书是毛姆在远东的游记,毛姆在游历中更关注的是途中所遇各类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给我很深印象的是毛姆记述的一个故事,那是毛姆跟当地人聊天时听来的,一个关于来生有记忆的故事。那人说这事是他们村子里老人讲的:说一个人死后又出生,居然找到他原来的那个村子,那个家庭,一切的一切他都说得极对,他的老婆相信了他。你想年老的妇女又有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当然很高兴。但他的已经长大了的儿子们却不认这个号称死而复生的父亲,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怕这个人来分他们的财产,于是就把这个复生的人轰走了。
我的故事复述完了,大家都笑着说,看来记忆连接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事,还是上帝的设计有道理。铁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微笑,我明白他是在跟我说,你那个“接不上”的问题这下有解了。
希米摸了摸史铁生的脊背,说,“冷了吧?太阳落山了就凉了,该回去了。”我们站起身,随着史铁生的轮椅,穿过草坪,走过园子里碎石子的小路,走向汽车。
太阳彻底落山了,太阳的余晖像是从舞台后面打出的灯光,均匀、明亮,有种笼罩的意思,有种圣洁的味道。在马路的十字路口,一前一后相跟的两辆车停下来,我向后探出头挥手,我看见史铁生伸出的手臂在摇动,还看见他坐在副驾驶位子的车窗玻璃后模糊的身影,还看见他眼镜片的反光,告别了。告别了。这就是最后的告别。
但不会是永别,不知在哪个时候,在哪个空间,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聚,对此我深信不疑。
作者系著名知青画家
责任编辑 刘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