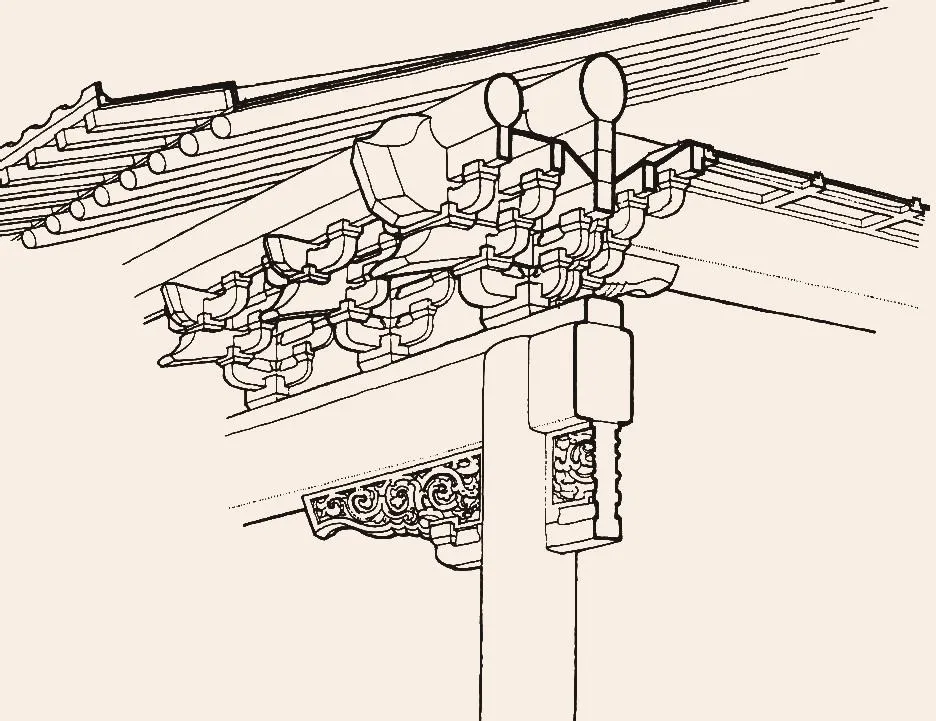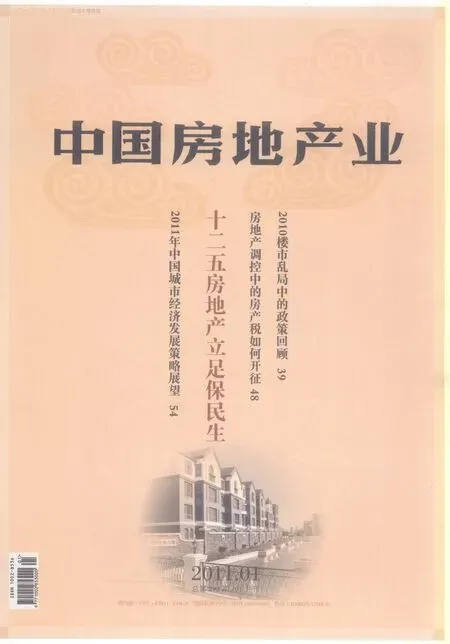“民富”的基础在于市场的活力
○ 孙立坚
“民富”的基础在于市场的活力
○ 孙立坚
今天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持续低迷的状态给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了重重的阴影!它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回避的“双重”制衡作用:一是扩大自身消费需求的压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二是克服金融危机的困扰,更要发挥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 “战略合作”机制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理念,来“最大化”相互支持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和全球“社会福利”不断改善和提高的效果。为此,“十二五”规划中所强调“两条腿走路”的重要性就是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重视目前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以及最大程度地去提升“民富”水平所需要的市场支撑能力。
具体而言,“十二五”规划的“新意”就在于努力实现基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它具体表现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两大方面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在“改善民生”方面,首先它是想从“三个层面上”发力来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没有钱消费”(民不富)的问题——即一是想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城镇化来推进农业现代化,来建设农民生活的美好家园,从而创造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空间;二是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区域发展结构失衡的问题,达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的效果;三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其次是通过强化社会保障的功能等公共服务机制的完善和优化来解决“有钱不敢消费”(民“富”而不乐)的问题。比如,“十二五”规划中会涉及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并正确处理好这方面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切实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只有百姓各种的“后顾之忧”得到缓解,大家才会乐于使用自己宝贵的财富来改善自己生活的质量。
最后是通过发展高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来充分激活高收入阶层在国内消费的巨大潜力,从而解决“有钱没处安心消费”(民富而不“和”)的问题。这次特别提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一方面它是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积极向上齐心协力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也能很好地满足高收入消费群对“精神粮食”的旺盛需求。如果无视这种消费潜力,那么,很有可能在贫富分化的格局中,中国过剩的流动性会走向金融投资领域,造成大宗商品通胀严重、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问题,从而不可能通过高收入群体资源的消费行为来将财富自然转移到为他们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低收入阶层的手中。于是,富者显富的投资行为让富者更富,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一般大众会“被”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的环境而逼得自己的消费变得更加“拮据”。于是,“仇富”的心态日益膨胀,就很难营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活力”。当然,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的效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都出现了“官员腐败”和资本外逃的不良现象,从而使得“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效果大打折扣。
另外,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也能从“四个方面”看出国家的主攻方向: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是让我们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二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路线,强调科学发展观。通过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明晰的发展思路,来提升市场经济的活力,打造“包容性增长”战略中所追求的“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理想环境。我认为在这方面一定要重视让民营资本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不打破市场垄断的格局和不重视战略产业的政策扶持,企业是没有动力去自己承担巨大的“埋没成本”来推进社会所需要的“结构转型”工作。
三是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这就牵涉到中国鼓励创新的制度完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技术专利制度的完善等。尽管今天社会上对“山寨市场”的就业吸收能力和社会消费意识的引导上所发挥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创新类企业承担风险的高额成本如果得不到市场应有的认可,那么,中国是很难出现世界一流品牌的企业和高端的产品,从而,也就不太可能让中国高收入的消费群体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立足”。
四是“做强金融”服务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重要的支撑。虽然这次在十二五规划中没有将“金融创新”放在特殊的地位加以强调,但是,它还是反映在规划中所强调的财税金融深化改革的内涵中。我也注意到,中央高层领导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增加直接金融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贡献比例的建议,要让银行依托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平台,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务。否则,不要说金融机构的活力受到严重制约,而且会影响到上述的社会保障功能目标实现所需要的庞大金融资源的支撑问题。
总之,“十二五”规划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反复提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尊重中国经济目前发展阶段所存在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扬长避短。即使我们现在“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不需要地方政府再搞过去的那种GDP增长的竞赛机制,但是,如果我们对“民富”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那么,还是无法避免过去那种“树标兵式”的“形象工程”出现。同时,长期习惯“政策市”的中国经济也可能因为“努力目标的不确定性”而会迷失方向,或者对“民富”的价值判断的偏离而削弱了我们对“有限资源”配制的“效率”。所以,关键一点我们还是要处理好“量”变(比如,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和同等条件享受社会福利的程度等)与“质”变(“民富”、“民乐”与“民和”)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