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与《荒原与人》中“荒原”意象比较
⊙张彦同[江苏科技大学,江苏镇江212003]
《呼啸山庄》与《荒原与人》中“荒原”意象比较
⊙张彦同[江苏科技大学,江苏镇江212003]
《呼啸山庄》和《荒原与人》都选择了荒原为背景,并以此为主干构成了作品的意象群,呈现出整体象征性。本文试比较“荒原”意象的异同,以“一点”透视全部,观照中西方文化和美学观念的异与同。
《呼啸山庄》《荒原与人》“荒原”意象比较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当代作家李龙云的大型剧作《荒原与人》虽诞生于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但无论在意象象征、原型蕴涵、人物塑造,还是情境结构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把写作的出发点定位于诗,用诗的语言和情绪尽情展现了刻骨的爱恨情仇,并表现出对爱恨的独特理解和人性复归的思考,从而使它们超越了传统,达到了行而上的哲学层面。两部作品都选择了略显苍凉又充满诗意的荒原为背景,并以此为主干构成了作品的意象群,呈现出整体象征性,也给两部作品提供了独到的可比性价值。
一、“荒原”镜像:“天堂”与“地狱”
“象”必须有“意”的融合才能成为“意象”,“荒原”作为“象”在两部作品中有着诸多相同的象征意蕴。两部作品中荒原都作为“自由天堂”的象征,构建了两个对立的典型环境意象:地狱与天堂。
在《呼啸山庄》中,呼啸山庄是环境恶劣的古宅,气息阴郁窒息,充满着压迫、歧视和虐待,活似一座人间地狱。对于从小在荒原上成长的希思克利夫和凯瑟林而言,荒原才是他们真正自由快乐的天堂,他们的心灵深处与荒原有同质的精神联系,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荒原,荒原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离开了荒原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命的欢愉。离开荒原的凯瑟琳备尝煎熬,热切地倾诉着对荒原的呼唤,渴望着回归自我,再变回那个荒原上的小女孩。回归荒原成为她最后的心愿——“在荒野里,立上一块墓碑……”①希思克利夫在凯瑟琳死后常常一个人在荒原上奔走到半夜,荒原成为他和凯瑟琳的灵魂再续前缘的唯一精神家园,他离奇的死以及关于两人常在荒原上散步的传说更使荒原染上了一丝神秘与唯美的色彩。《荒原与人》②中也有这样一组对立的典型环境意象:“落马湖荒原”和“于家围子”。于常顺的童年是在于家围子的痛苦压抑中度过的,父亲的软弱、妹妹的死、耻辱的婚姻使于家围子成为于常顺永远的“梦”。落马湖荒原才是于常顺“自由的”的天堂,有可爱的毛毛,有忠心耿耿的大狗——黑子,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
两部作品都有意安排了这种对立的环境,并把感情的重心放在了世俗社会看来相当蛮荒之地,究其内因,可能主要都源于他们对原始生命力和自由的渴望。爱米丽深爱着荒原式的大自然,她就像那荒原上的精灵,只有在荒原上才感到自由。李龙云作为一个作家更加渴望和珍视自由。他说,“我喜欢我的职业是因为这种职业的自由”③。其次,根源于两位作家共同的生命意识。《呼啸山庄》是爱米丽“反叛社会、返回自然”思想的体现,荒原寄寓着她对“自然与人类文明”问题的深刻思考。作家李龙云在北大荒插队十年,荒原对他充满了诱惑。两位作者正是通过对荒原的着意刻写,寄寓着他们对生命、自然、人类、宗教、爱情、人性等命题的思考。
二、“荒原”身份:角色与背景
虽然“荒原”在《呼啸山庄》和《荒原与人》中同样作为象征性意象存在,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寄予着作者的生命意识、人类意识、宇宙意识,但从荒原在情节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上来看,二者则显示出了更多的差异性:《呼啸山庄》中的荒原作为背景而显出更多的客体性,而《荒原与人》中的荒原则时常化身为角色,与作家、与剧中人物展开丰富多彩的心灵对话与交流。
在《呼啸山庄》中,荒原更主要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存在的,作者很少直接对荒原进行客观描写,而是通过他人的叙述来勾勒大致面貌,荒原主要是以一种客体身份存在的,“它本身并未直接参与到情节线的构建和延伸,仅仅是作为一种人物所向往的心灵自由的象征,对情节的发展起到某种启示作用”④。荒原只是故事展开的舞台和背景,是蕴含主题意蕴的象征性意象。而在《荒原与人》中,荒原更是鲜活的,有灵性的,是一种人化了的自然。从题目“荒原与人”上便可看出,荒原本身便是剧中的一个角色,是所有人物(包括作者)对话的一个对象。荒原(荒原中的景物)与人的情感、时间发展是一种同构的动态结构,荒原是作为人物心理变化的一种外在暗示,渗入到情节设置中来的。剧作家擅长对荒原进行直接的描绘,拓荒者们常常面对荒原倾诉着各自的诗情、梦想、痛苦和怨恨,荒原见证着拓荒者们刻骨的爱与恨。荒原是变化的,是人物微妙心理的巧妙暗示,荒原及其景色和情节内容有机融合,人、事、景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
从两部作品里对荒原的不同处理方法可以看出,西方文学更倾向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情感,情感往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景物与人物之间没有内在的心理联系,不注重景与人的互映观念;而中国文学往往不直接抒情,更喜欢含蓄地把人物心理通过景物传达出来,讲究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三、“荒原”意蕴:人、自然与命运关系的哲学思索
荒原在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毕竟有着各自的风貌,以至在诗意、苍莽的底色上,《荒原与人》中,古老的落马湖荒原是最圣洁、最本真和最纯粹的,是未开垦的“处女荒原”。荒原中连那疯长的茅草、黑色的沼泽也是诗意的,更别说那鲜红的、亮丽的,附着美丽传说的达子香花。《呼啸山庄》中的荒原长着坚韧的石楠,粗犷、蛮横,透着硬气,更趋向“蛮”的意味,更多了些哈代笔下荒原的阴郁意味。
两部作品对荒原的书写使作品蒙上了一种迷茫、神秘的色彩,从而成就了作品的丰富与博大。正是以荒原意象为主干的意象群,使作品整体上超越传统哲学实现根底的诉求,并且这种诉求是超越作家个体的,是“全人类式”的。如伍尔夫所说:“她要通过她的人物来倾诉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而是‘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⑤而李龙云是一个自我意识更强的作家。《荒原与人》这种哲学根底的诉求更深挚而自觉。作者“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而是站在上帝的高度”⑥,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心胸,去探索荒原、自然、命运与人的关系,思考人生背后的、带有宗教意味的哲学意义。
《呼啸山庄》已经拂去蒙尘,成为世界公认的杰作,被称为“文学中的斯芬克斯”、“人间情爱的最宏伟史诗”。也有评论家这样评论《荒原与人》:“这个戏的追求,是要架起一座桥梁。首先从戏剧界过渡到文学界,当然也想通过这座桥把中国艺术送到世界。”⑦我们期待着《荒原与人》能走向世界,震撼更多人的心灵。
①爱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李龙云:《荒原与人》,《李龙云剧作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李龙云:《杂感二十三题》,《剧本》,2000年第12期。
④曾欢:《〈原野〉与〈呼啸山庄〉的情境模式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⑤[英]弗吉尼亚·伍尔夫:《〈简·爱〉和〈呼啸山庄〉》,刘文荣译,《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⑥⑦《李龙云戏剧作品研讨会纪要》,《剧本》,198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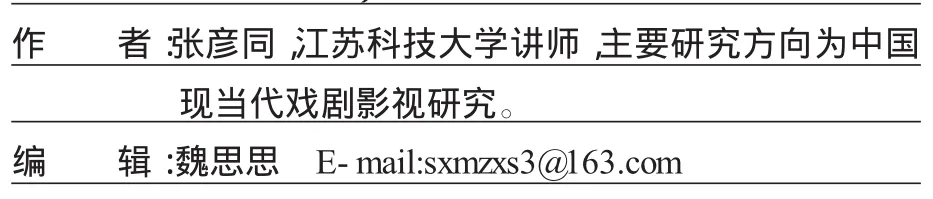
作者:张彦同,江苏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影视研究。编辑:魏思思E-mail:sxmzxs3@163.com
本文系江苏科技大学高教研究项目《理工院校公共艺术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K TY2009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