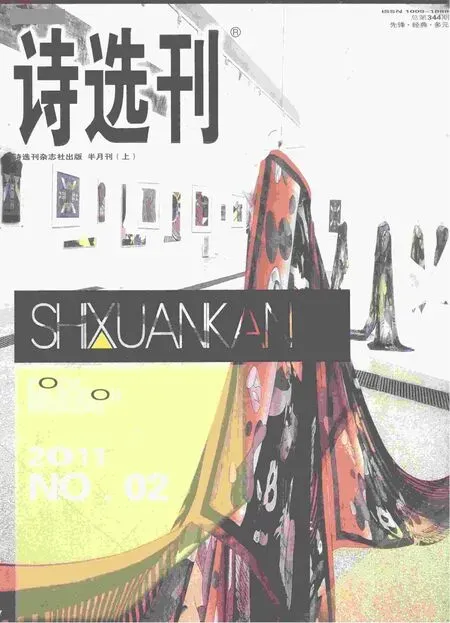刮在耳后的风
□赵云江
刮在耳后的风
□赵云江
第一缕:我理解的文学与写作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写作?
答案可能有以下若干种:生活——生存,爱好——兴趣,天赋——特长,思想——信仰,声音——发言权,功名——出人头地,抑或包括理想、使命、道义、功利、荣誉,等等。
那么,我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吗?
我能够或者敢于回答我自己吗?
哪种答案(一种或者兼有)才能代表真实的我?
纯粹的阅读和文学、写作当然是两回事。
相对于人类必须要面临的更加严酷和粗粝的生存课题而言,文学与写作应该是第二位的。但如果人类要清醒地获取有质量、有尊严的生存,文学与写作,包括阅读,或许就变得不可或缺。
有人说愿意选择一种“诗意”的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的选择。
有人说,他生下来就是为写作活着。
还有人说,写作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对这些没心没肺的说法,我全部都不予认可。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写作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性表述。
一个写作者所选择的生活,很可能与他的写作姿态有关。或者说,一个写作者的写作姿态,也可能会界定他的生活模式。
一个写作者的社会定位,很可能与他的灵魂姿态有关。
但是,一个写作者的社会定位,应该与他所选择的生活无关,更与他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承担之类的灵魂姿态无关。
我愿意选择“诗意”化生存,但诗意的生活却从来不会主动选择我、你、他或者我们。
如果这个所谓的“诗意”中不涵盖着“恐怖、血腥、残忍、罪恶”以及“丑陋、卑鄙、阴谋、欺诈”等黑暗色彩的背景,而一味地“阳光、沙滩和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甚至饰之以“公平、公正、欢乐、美好”等表象概念,那么,这就能够证明所有的“诗意”化表达都是伪命题。
尽管我们愿意接受没有任何杂质的“诗意”,但事实上那样的“诗意”并不存在。如果非要寻找那样的“诗意”,一如鲁迅先生所说,就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第二缕:生活与作家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学的源泉来源于生活”——这无疑是对的。因为没有生活,或者说连生活的基本元素都不具备的人,怎么会选择文学与写作?
当然,生活和文学及写作也并不划等号。懂得生活或者善于攫取生活的人,也许并不垂青文学与写作。
做梦(梦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想像是虚构文学的基础,想像类似于梦境。
所以“想像”也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不止一次地例举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中那个“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说“那个人”哪怕是并不知诗为何物,抑或连字也识不得,但却不妨是个真正的大诗人、大作家。
《江雪》全诗只有二十个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这首短诗表现的就是“蓑笠翁”奇高的精神境界和他遗世独立而又冷眼观世(批判现实主义)的人格姿态。在这里,我更多指的是精神意义上的东西。
现在来看,这说法不免过于片面。因为只字不写或者连句打油诗也吟不来,一句梦呓般的话也不会说,如何就会成为一个诗人或者作家一类的人呢?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不光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拿高文凭的人也都是车载斗量了,诗人作家这一行当中难道还会有目不识丁的人吗?我再坚持这种说法,怕是要遭到别人弹嫌的。
其实,我的原意也并不在此。我只是表明了自己在某一向度上的推崇和标榜而已,是和现实中作家与创作的关系不太挨边的。但既然是诗人或是作家就该有作品,用作品说话,道理就像母鸡用鸡蛋说话一样,也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每一年都会收获每一年的粮食。
每一代人也都会有每一代人的收获。
今年的粮食仅仅是对去年种子的更新和模仿,而非“创新”。虽然这种“更新和模仿”也会付出心血和汗水。
而我们的生活大抵就是如此。
我们对生活的认知更是如此。
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应该也是如此。
时代的演进并不标志着历史的进步。
有时,盲目地“超越”说不定正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沿着一个圆弧不断地重复着自己或者别人。
就像一个婴儿,他每天的发现和每天的新奇感受,虽然也是生机勃勃意趣盎然,但那只是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很难说哪些生活是作家自己独特的发现。
很难说有哪一位作家在一生中能有自己真正的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发现了别人的发现,而又拿着这些发现去展示给别人。有鉴于此,他的价值或许仅就是给予了别人一束手电光,或一支蜡烛而已。

所以,能够独特地发现并挖掘生活的作家才显得可贵。如果说作家还能独特地表达自己的生活发现,那么,这样的文学与写作才是最有价值的。
第三缕:好作品与好作家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向人类提供一个接近永恒的价值标准。它对人性提供判断,对时代有所鉴别。在灵魂上,它反对轻浮和木讷,并且还应该拥有尽可能高尚的审美趣味。
它可以不代表真理,但它应该接近认识真理的标准。
胡萝卜可以论堆、论斤卖,而人参却是论颗、论克去称。
但是,胡萝卜却可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粮(日常消费品),而人参却只能是药材。
生活现实就是如此,胡萝卜与人参并存,疗饥和治病并不偏废。
如何才能写出传世之作?
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勉力为之。这不可能是上报了计划,而后又被规划了的工作。在主观上,这也不是那种刻意去做了就能接近的一种行为。因为文学的现状已经告诉了我们许多这方面的不幸,这就是事实。
一些作品,是作者从一开始就当作“传世之作”去写的。结果弄出来之后,放在整个人类文学历史的长廊里,却显得苍白无力。对于写作者来说,固然有才情上的不足,但更为重要的可能是见识上的不足,是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与人格素养上的欠缺,甚或也有时机、条件等方面的原因。
有鉴于此,我应该时刻警惕着。
有了作品的写作者抑或被称为“作家”。但是,获了奖或者取得了不菲发行量并获得了优厚版税的作家,就是有了“影响”的作家吗?有影响的作家是按照奖项大小或“财富排行榜”的顺序来确定的吗?
从深厚的历史角度看,当时有过一些“影响”的作家不见得将来一定有影响。
有影响的作家应该尊崇着一个崇高的标准——那就是“人格魅力”,他从骨子里就会透着生命的激情和来自人性的感召力。这种作家不仅从语言上独有领悟,而且在人格向度上也自塑自成。
在这里,个性并不标志着人格,因为有些所谓的“个性”是病态的,病态的个性表现在文学与写作上,往往会导致价值标准的错乱。
因为人格的亮丽、情趣的高致,才会照彻他赖以审视并肯于表现的精神境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那种离弃了人的生存本质以及对人性的理性关照,而只是因为自己在生活层面上的诉求,抑或包括在语法修辞方面的“炫技”等等,是不可能真正打动人的心灵的。
我曾经产生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能够超越时空,我们的组织部门要是能把曹雪芹、蒲松龄、施耐庵、金圣叹、冯梦龙,甚至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邀请到当下,给他们开开笔会、评几个奖次,或者许愿擢拔其中善于跟风者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他们会怎样?
他们也会像当下的诗人、作家一样地功利和浮躁吗?
好作家一定要有人民性。
好作品一定要有历史观。
所谓“人民性”就是良心;
所谓“历史观”就是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看人性。
说什么话,总是与说什么事有关。
怎么写,永远服从于写什么。
“写什么”是动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库藏)。“怎么写”是动用自己的才情。
什么样的作家积累什么样的生活素材。
拥有怎样才情的作家所选择的表现手段更是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
作家的才情似乎与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操守无关。
对于读者来说,欣赏美女的笑脸,好像也无关乎她放不放屁。
作家和作家的写作动机可能大不相同。
能够传世的作品好像也不是特别计较作家的写作动机。
不同写作动机的作家可能都会有传世之作。
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多身影伟岸,挥斥方遒的人中俊杰,并不见得就一定留下鸿篇巨制或佳作华章。也许相反,更多时候,作家仅就是一个时代(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体验者和见证者。
负有使命的作家是用“话语”说话,而不是“噪音”。
尽管这个时代不缺少“强音”,但还是缺少“话语”。
第四缕:借鉴与创新
因为不断地有人在号召“创新”。
因为不断地有人出来呼吁作家们多出“精品力作”。
还有人应声出来表态要当“大作家”。
——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常常为了上面这些说法(号召、呼吁、表态)莫名其妙地发笑。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但不见得就是一个特别充满“诗意”的时代,更不是一个以文学为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个时代虽然缺少黄钟大吕般的史诗,但并不缺少大师。
这个时代虽然不缺少大师,但是缺少大作品。
这个时代虽然缺少“主义”或主张,但并不缺少“山头”和旗号。
只要一进入创作,我就得时刻注意躲避那些割据或自封了的“山头”。
我必须要警惕,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走到谁的阴影里面去。
因此,我只能在夹缝中寻觅着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或“山头”?
文学的现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语言的道路真是太狭窄了。
有一个时期,有人讲到“创新”二字还幽了一默,说是被“创新”这条狗追着,连站着撒尿的机会都没有了。想来,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可笑的事了,甚至说,这倒是个值得庆幸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还有那么一条“狗”追着。而且,还有一些那么在乎被“狗”追着的人。
但是现在,那条“狗”消失了,倒是多了许多寻找“狗”的人。
我理解的“创新”,同样不能刻意去追求。尤其是不应该由那些惯于文过饰非的人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创新”。
创新只能是形式和内容相互和谐中油然而发生的那种写作意识,是一种不经意间选择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的才是自然的,才是天衣无缝的,只有这样,才会使有修养的读者浑然不觉。
鹦鹉学了人说话,还是鹦鹉。
猴子穿上人的衣服,还是猴子。
如果猴子进化成人是“创新”的话,人再变回猴子就不是创新。
人们看惯了鸡下蛋、鸟下蛋,都不觉得稀奇。但如果驴能下蛋,那就是奇迹。如果老虎下蛋,就更了不起了。
事实上驴和老虎是不下蛋的,如果它们真的下了蛋,那它们无疑就是怪物。但在文章法度上却并非如此,千古文章贵在创新。在这里,我是特指各种文体写作的“杂交”优势,或者也与作家如何以自身独特的创作观念去发现生活熔炼生活有关。
只有自己的心智健全了,目光独特了,观察事物的角度独到了,自然就会产生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而后用合适的文字把这些带着“体温和脉跳”的感受记录下来,自然就是一篇独有见地的文章。
如果我们面对的事体足够大,我们“钓”到的才有可能是一条大鱼。

如果我们的心智足够强,我们才有可能追逐到那只更狡猾的“老狐狸”。
写作自然有其规律可循。我也相信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作家最终都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写作方法。
语言的借鉴或者摹仿永远只是表面的,就像我们披上羊皮却不是羊,吃了牛肉不会变成牛,吃了苹果也不会变成苹果一样。我们自从出生以来,小嘴就不停地吃,我们把能吃的东西吃下去,就只管吸收营养只管长大,身体的骨肉发肤就再也分辨不出是吃了什么长成的。所以说,营养就是营养,永远不会变成本体。
剩下的还有一个创作激情在具体操作上的应用问题。
创作激情当然是指一个作家对社会问题和生命感情及生命智慧的一种自然关注后的冲动。他有所思考,他已经思考,他不吐不快,是他本体生命力的一种折射,也是他生命本身留给无限空间的一道光影。这是机缘,也是必然。
这与那种应景式的写作截然相反,他洋溢着的是生命本身焕发出的激情和感召力。
第五缕:我的困惑
我警惕那些“竞技式”的写作比赛与取巧式的卖弄。我承认这中间也会有所成就,但这并不代表文学的本质。
既不可以把文学与写作神秘化,也不可以把写作程式化,更不可以繁琐化。
林林总总的“主义”也好,“旗号”也好,它总该诞生在作品之后。只不过是作者用了自己的思索,重新解释了生活的含义而已。同时,程式化或繁琐化的倾向也是有的,但只能是把语言越用越死,自己把自己推向极端的死胡同而已。
语言僵化之后,其表现尽管能够做到不动声色,但也不再会关乎痛痒;尽管是鬼神莫测,但也只是故作高深。作家自己想像力的缺失,也必将会殃及读者的想像力。
文学和写作与商品经济的必然汇合,给我带来沉重思考的同时,当然也给了我许多选择的空间。
上帝总是这样,他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这就像许多留下千古名作的古贤面对当时的仕途经济等烦心事一样,我们不能试图逃避一个文人或作家所固应承担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试图比古人更少地承担些什么。
如果不能承担,那我就只能选择放弃。
因为在我选择文学与写作的同时,我还选择了一个不断放弃的过程。
放弃的原因只有一个:或许还没有具备承担的力量。
文学艺术的目的是圣洁的,我们应该站在人类全部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审视自己所处的位置。
如果我自己的站位并不那么高,那么,我最终的选择就是闭嘴。
我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并不满意。我觉得我的创作理念就像是一颗饱满的种子,但在播入土壤之前,在遇到雨水浇灌之前,也就是说在发芽之前,它却经常莫名其妙地死在了“梦乡”里。
反省自己的创作,我觉得自己“减法”多,而“加法”少。
自己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内省和互否,这些直接导致了我更多的打量、犹豫和冲突。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玩一场追逐地平线的游戏,总有一种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到达的感觉。
这让我困惑,更让我苦恼。说到底我是在怀疑我自己。
我不能用盲目的自信混同于勇敢,不能用麻木来代替内心的挣扎,更不能用别人(社会)的奖赏来麻痹自己并糊弄别人。
没有到达和没有出发固然不同,但没有到达却向别人示意成功,就是盗名。
第六缕:创作之外的思想碎片
在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环境里,人类正在渐渐远离天地自然所赋予的空灵与虚幻,而愈加变得“现实”与奢华,我们还会很容易地接近最朴素的真理吗?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史。发现其中关系的神秘性——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相对于人类的文化发现与发展来说,许多因果关系都是不可解释的。
我坚持这样的说法,并不怕有人说我“虚无主义”。
阴阳殊路,生死相隔——既是人生中的一个主题,更是人世间的最大迷踪。
人生为底事?人死为何物?生生死死难道仅仅就是几十年的一个时间演进的过程吗?在其中,人与人又有多少可能的交汇点?
在整个人文背景之下,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包括每个人物各自造就的命运——这些极富神秘色彩的生命轨迹也正是展示文学魅力的所在。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人类全部生活的一个局部。
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是人类全部思想的一部分。
人生犹如樊笼,自囿其中而又不觉。
我们常常是这样,时刻观察着别人,又时刻防备着别人的窥测。结果总是相反——别人的窥测无时不在,自己的隐私又总是成为“公开的秘密”。
生活中的尴尬无处不在。
生活本身就是永不谢幕的幽默剧场。
在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在生存意识中补充钙质,在神话传说中打通脉络,在神秘氛围中营造故事,在寓言效果中还原生活——这就是我的全部文学追求。
归纳起来,我愿意将个人的创作理念命名为:神秘现实主义。
故事与故事的不同,是因为发生故事的人物、地点、时间各有不同。
寓言之所以区别故事,就在于寓言“抽象”了故事,之后又还原为故事,最后又“指代”故事。
现在的文学作品中“故事”多了,而寓言少了。
会讲故事的作家多了,肯用“寓言化”的视角反观生活并提纯故事的作家少了。
“寓言”在文学作品中就像是“灯盏”或者“盐”。
有才情的作家就像是一个好厨师,或者是一个在黑夜中肯为我们点亮灯盏的人。
我们的现实生活从来也不缺少故事,但缺少文学中的寓言。
如果“故事”需要去发现,那么,“寓言”就需要去提炼——这就像是煤和铁的关系一样。
生活中的故事就像是煤,需要我们去挖掘;而文学中的寓言就像是铁,需要在“熔炉”中提炼。
2010年12月
于邯郸·连城别苑·翠园
(此文节选自赵云江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似的耳朵》的代跋)
(本期封面用图选自《艺术与设计》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