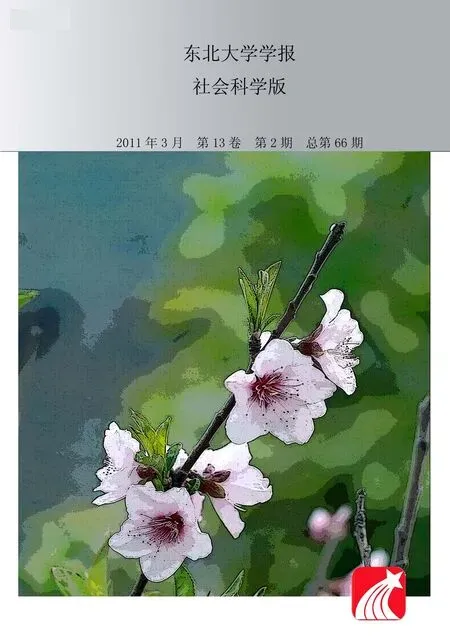沉默的颠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解读
颜晓川,冯 溢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是典型的后殖民作家。他的小说一贯的主题就是关注主流话语之下的个人叙述,关注被压迫者的痛楚与心路历程,努力发掘被历史宏大叙述所掩盖的个人历史,进而反思殖民者的“自我”与边缘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就是其中一部检视殖民关系、抵制殖民主义的力作。故事以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卑微的生命在充满战争、军队和种族隔离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渴望寻找生命绿洲的故事。天生弱智但心地单纯的黑人园丁迈克尔·K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打算带着患病的母亲离开充满战乱的开普敦,到乡村去过宁静的生活。在颠沛流离的途中母亲离世,K独自漂流在路上。在政府、军队等各种残暴势力的压迫和驱赶下,他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话语,一次又一次被投入营地,无法逃离受他人掌控的命运。但他的逃离之心并未因此改变,最后逃入了空无一人的深山,过着动物般的原始生活,却也因此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作品的主人公迈克尔·K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智力残缺、沉默不语、离群索居。库切如此再现殖民地他者形象却并非出于白人固有的种族偏见,而是库切特有的叙事策略:保持他者的他者性,从而展示权力系统的运作过程,揭示叙述背后的霸权话语来颠覆和解构政治权威。诺贝尔奖授奖词精辟地评价这部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离了日益严峻的动乱和将要降临的故事,却陷入无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现对权力逻辑的否定状态。”[1]228同库切的其他作品中的被压迫者一样,迈克尔·K的沉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令人窒息,然而恰恰是从这种沉默中显示出一道真理的曙光,抵抗并颠覆了殖民话语与政治权威。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表现的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最为猖獗的时代。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是“自我与他者”对立的二元论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指出:“后殖民理论家们将殖民地的人民称之为‘殖民地的他者’ (colonial other),或径直称为‘他者’(other)。‘他者’这个概念,主要是根据黑格尔和萨特的定义:它指主导性主体之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2]即自我身份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
在逃亡途中,由于身体状况很差,迈克尔被送往一家康复营地,在那里K遇到了医官。许多批评家把这个人物看做是白人的代表,医官对迈克尔·K的态度像许多南非白人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一样非常矛盾。他照料K,使他恢复健康,是希望“有朝一日他就能够重新加入营地生活,有机会穿过跑道来回大步走,喊口号,向国旗敬礼,并且练习挖坑再把它填上”[1]62。这里显示出殖民主义的目的:帮助被殖民的他者是为了他们能够“喊口号,向国旗敬礼”,换句话说,就是为帝国服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医官才竭力保全K的性命,在慈善的名义下,殖民得以继续。医官虚假的、伪善的、家长式的作风同白人话语中白人的“使命感”一脉相承。白种人把非白人想象为未开化的、没受过教育的人,把他们看成不会自己走路的孩子,需要成人(白人)的监护,白人肩负着“拯救他者”的“使命与责任”,这反映出白人盛气凌人的掌控欲望。在库切的另一部小说《福》(又译《仇敌》)中的叙述者苏珊·巴顿对星期五也表现出这种家长式的态度。当船来接他们去克鲁索的小岛,苏珊坚持把星期五也带上:“我请你把你的人再派到岸上去,因为星期五不只是个奴隶,更是一个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能把他自己留在孤岛上,这比让他去死更糟糕”[3]39。实际上,白人殖民者的所谓责任只是花言巧语的托辞,以遮掩镇压被殖民者之实。
医官“好意”要恢复迈克尔·K的声音,这样K就不至于在历史上“默默无闻”,而医官掌控的欲望隐藏得更深。“谈谈吧,迈克尔斯,……否则的话你就会白过一辈子,根本没人注意你。……让你的声音被人听到,讲讲你的故事!”[1]171然而,迈克尔没有回应医官的“好意”----“为什么对我大惊小怪呢,为什么我这么重要?”医官的话语反映出殖民者的焦虑,他想要迫使K去屈服他的掌控意愿,他和苏珊·巴顿帮助星期五恢复发声一样:“我告诉自己同星期五讲话,去教他走出黑暗与沉默,但是那是真相吗?有时仁慈离我而去,我使用语言是用最简便的方法让他屈从我的意志。”[3]60同样,医官要把K带回到语言世界的努力实际上也是让K屈服于他的意志。如果K说出他的故事,似乎他的身份认同问题给他带来的痛苦就都可以解决了。因此,医官要“使你(K)的生活有些内容”实际上是在要求他作为主人的身份有些内容。然而,K看破了“好意”的面具,他顽固地保持沉默,医官的身份认同因此受到威胁。只要医官不能把K整合到自己的故事中,他主人的身份就是不合法的,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令人生疑的。Michael Marais在《帝国的诠释》一文中对于库切作品中的沉默的作用,阐释了相同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权威者的)统治地位取决于他(被统治者)对于他们的主人地位的承认,他的沉默否定了他们的地位,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份以这个地位为前提条件,因而他的沉默挑战着他们的现实”[4]75。沉默具有积极的意义,变成了反抗权威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沉默便不是屈从于他人话语的表示,而是他者所具有的反抗策略,这样就可质疑统治者的权力结构。因此,尽管医官再三劝说K讲话,K就是保持沉默,以这种形式抗拒当权者对他掌控的企图。
话语实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压制边缘意识形态的场所,人类的语言就是在不同的权力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被社会使用的话语其实是夺得统治地位的力量的话语,相反的话语则遭到压制,不同的话语被排挤,在话语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权力展示。历史的叙事即是权力的展示。新历史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其实是像文学一样,是一种叙事,“事实上,叙述始终是,而且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主导模式”[5]。库切提出“历史是将意义强加于时间和事件之上,但那时间和意义实际上是语言,它们是语言”[6]。库切明确意识到在历史的描述中意识形态被编码入语言:
“历史并非现实:历史是一种话语,小说也是一种话语,是另外一种话语。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文化中,历史将以不同程度的力量,试图占据首位,宣称自己是一种主人的话语形式;而像我这样的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宣称历史只是人们彼此讲述的故事。”[7]
历史因为其叙述性不仅不可能体现真实和真理,而且往往成为拥有权力的人以历史之名压迫异己的手段。因此库切把建构历史看做是暴力的叙事,一种暴力的再现。历史暴力的再现模式表现在承认同者,排除他者。因此,为了不再重蹈“建构历史”的覆辙,库切用沉默去再现他者。他的小说总是呈现出“再现无力”,对他者的拒绝再现或无力再现即是对“历史暴力的再现模式”的挑战。历史再现模式是通过把他者故意降低为客体而否定了他者的差异性。通过写作的行为,作家可以叙事再现的形式反复地进行历史再现的暴力,因为笔的力量同历史的权威相似,如果叙事再现也是基于原来的社会关系,文学就变成了历史话语的重复。
如果没有了语言,否定的意义就无法建构起来。失语的他者不能为自己言说,自我就无法进入他者的经验,K的语言缺失像一道墙一样把K同他人用语言去获得权力的愿望隔绝开来。医官无法理解K,他不仅不能通过语言了解K,他的多舌使得K的他者性变得更加显著,K的意思却越发让人难以捉摸了。医官越是想搞清K的意思,K就滑得越远,所以医官把K称为“一个了不起的逃跑艺术家”[1]203。医官努力描述K的故事,通过言语捏造K存在的意义,他是想把K纳入语言系统,剥夺K的实质内容。贯穿于这部小说始终,医官所做的就是通过语言让K的存在变得有意义,给K“一些内容”,这样他就不会默默地死去,并被埋在跑马场的某个角落的不知名的坑中[1]186。然而,语言并不能给K任何内容,也不能为其创造任何意义,因为K已经超越语言的媒介,而他的存在也超越了语言的否定。与医官不同,K不依赖语言去交流,也不需要语言去建构他的存在。
库切认为,文学的责任在于恢复他者的他者性。他在小说中致力于让缺席的他者浮出历史水面,让不可见者重新可见,因为沉默和破损的躯体已经作为无声的语言为他笔下星期五、维库埃尔、迈克尔·K等被压迫者言说。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反抗力量,是拒绝纳入权力话语体系的一个表征。因此,再现沉默----他者最显著的特征,事实上起到了“尊重他者,为他者负责”的作用。库切虽然不能使用他者的内部语言为他者言说,但对自己使用的语言权威进行颠覆的行为本身,对他者建构文化的自我意识具有重大意义。
在迈克尔·K的时代,个体身份远没有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社会身份和地位重要。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选择是否可以在此生活的时代,没有可能全然蔑视历史的桎梏。然而迈克尔·K把自己贬低到如蠕虫一样的生存状态,通过这种生存方式,至少可以逃避“掉进历史的大锅”[1]185。正如迈克尔·K在小说结尾处所想:“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1]219《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暗示着总有一个角落可以躲开历史的范畴,在那里生活以自由的旋律流淌。
在后殖民文学中,大多数作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肯定并恢复他者声音的价值,这样他者就可以同藉由语言建立起的权威和压迫作斗争,再现他者的唯一方法就是赋予他说话的权利,即使这意味着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所以“为了能够进入政治领域,把语言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来改造和使用是极其必要的”[4]73。在这个意义上说,沉默就变成了他人语言的被动的牺牲品。然而,库切的策略“同大多数后殖民作家所传达的感觉都不同”[4]73。因为正统语言是殖民者惯用的压迫工具,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步就是对正统语言的弃置、颠覆与瓦解。他者一旦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来重塑自我,便失去了帝国界限之外的身份,再次把自我纳入到帝国话语中来。在库切对沉默他者的再现中,赋予沉默以力量:沉默是他者保持他者身份以抵抗西方同化的手段。尽管沉默在表面上使得他者在“正统的”“权威的”语言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却是对正统语言的弃置,起到了保持他者的他者性的作用,沉默变成了抵制殖民者语言的手段。迈克尔·K超越语言而存在,语言的缺乏帮助K逃脱外在的压迫。“K令人难以捉摸的另一面即是他的沉默,沉默既是被剥夺公民权的标志,也是抵抗的表现形式。”[8]库切没有引用他者的声音来反抗权威,而是把沉默作为一种消极抵抗。支配性与否定性总是与语言相连。K的沉默,同《福》中的星期五和《等待野蛮人》中那个蛮族姑娘的沉默一样,充满了不能言说的故事。“这些人不能说话或拒绝说仇敌的语言,但他们的沉默就好像千万人在一起的呐喊。”[9]正如《福》中苏珊·巴顿所观察到的:“在每个故事中都有沉默,一切视线被遮蔽,一切话语没说出口,直到我们说出没被说出口的话,我们才进入故事的中心。”[3]141换句话说,承认他者的非语言存在是理解整个人类故事的关键。因此,在南非语境中,迈克尔·K的沉默被赋予了抵抗的政治意义,他的沉默是逃避主导话语的策略,也是抵制殖民者语言的策略。迈克尔·K的沉默“塑造出一个机警的、不断被边缘化的叙述主体,他灵巧地穿过权力的缝隙,保持了他民族的完整性,但却并没有大声呼吁统治者的包容,也没有夸大他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统性”[10]。
库切意识到抵抗帝国话语的方法并不是通过给予他者一种声音作为“政治武器”来创造一个反对的力量,因为这样做,他者仍然被放在权力话语结构之中。正如赛义德所说:“如果权力用于压迫,用于宰制,用于操纵,那么任何抵抗权力的东西都不能在道德上与权力处于平等的地位,不能简单地成为抵抗权力的武器,抵抗不能与权力势均力敌。”[11]因此库切对于权力抵抗的观念,不是要赋予他者另外一种声音,创造一个“势均力敌”的权力,而是对于权力的让渡。K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沉默去抵抗,才能瓦解和颠覆语言系统的界限与规则。沉默并不是言说的缺席或言说的无能,而是另外一种语言,像音乐一样,是替代有声语言可行的选择。迈克尔·K的沉默含义丰富。我们可以从叙事者的描述中看到他有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园丁),有自己的判断(是去参加游击队还是留下来侍弄花园),有自己的幻想(使得荒芜的农场重新繁荣起来)。他的故事是所有南非黑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非常宏大,远非官方正式语言所能传达。尽管迈克尔·K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但他可以像星期五一样用音乐和舞蹈的“符号”表达自己。“他(星期五)只用音乐和舞蹈表达自己,对于言语来说,他的言语就像叫喊。”[3]142这就是星期五同世界交流、诉说他的故事的方式。“用艺术的方法,他的真实的故事才能被听到。”[3]118通过艺术的方法,我们才能够接近星期五,也只有用艺术的方法我们才能看清迈克尔·K的本性。
“艺术”是解读K的关键。迈克尔·K的园艺也是一门艺术,他以这门艺术手段静静地同外界交流,通过耕种土地,K表现了自我也发现了自我。我们须要去倾听他的沉默,去关注他的园艺意涵----K表达自我的符号艺术。在无处不在的语言暴力中,艺术为沉默的人们提供了表达自我的出口。尽管他们沉默不语,星期五的音乐与舞蹈、迈克尔·K的园艺艺术继续以自我的方式发出声音,叙说他们自己的故事。
迈克尔·K对政治压迫的抵抗不仅展现在他的沉默中,而且展现在他的园艺中。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这部小说中,K与土地的联系意味着自然是被压迫者恢复自我和独立性的地方。土地对于迈克尔·K来说具有多重象征意义:首先,土地是母亲形象的象征。在土地中K可以获得一种归属感:“我要住在这里,他想到:我要永远住在这里。这里是我母亲和姥姥生活过的地方。”[1]122其次,在自然与文明截然相反的两极,自然是人们可以逃避所谓“人类文明”的地方。在南非社会,自然界是K得以逃避被奴役的厄运的地方,大地象征着拯救人类之地。
在南非文学的传统中,土地,尤其是南非的卡鲁高原是神话的一部分。阿非利肯人总是用饱满的热情描绘神秘的平原和丘陵,把这片土地写成神话。神话中的英雄总是远离人类,远离人类的堕落。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迈克尔·K与土地的亲近暗示了逃避奴役与战争。卡鲁高原不仅为迈克尔·K提供了逃离社会压迫的场所,也为他提供了施展艺术的地方。只有作为园艺师,他的生命才有意义。迈克尔·K似乎继承了阿非利肯人田园生活的传统理念:“从一面的地平线到另一面的地平线,满眼看到的都是空荡荡的大地貌。他爬上一座小山,仰面躺下,谛听着茫茫的沉寂,感觉着和煦的太阳温暖一直渗透到他的骨髓里。……他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人们会撤到这里来,把自己隔绝在方圆多少英里的沉默、静谧之中。”[1]57
但K无须将土地拟人化,也无须神化,因为对他来说,南非的地貌不会带来任何迷思,没有神秘感。K住到一个洞穴里,与自然合而为一,同时他也放弃了任何人类建构:他不想“把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竖起一道道围栏”[1]120,把大地分割开来,他认为“试图再建立一个新家,开展一场竞争”[1]128的想法是错误的。K开始把大地看成是大地本身,无须费力把它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之中,“他像一条蠕虫一样开始向自己的地洞蠕动,他一心想的就是:让黑暗赶快降临吧,让大地把我吞下去吧”[1]133。K回归土地,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开始瓦解。在荒野中,像动物一样地生活,K逐渐远离了人类社会,从这时候开始,K逐渐抹去自我,这样他就可以逃脱主/客二元对立的范式。他不想证明他存在的意义,他在世界的存在同土地本身的存在一样,无须人类的解释和释义来确定他的实体性。库切发现人与土地新的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并不须要通过征服土地来证明,人与大地可以合而为一。虽然库切用黑人来表达这一含义,但并不是要把土地归还黑人,而是归还给土地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土地没有种族、性别、阶级,属于所有在上面居住的人。因此,库切所构建的土地是超越政治、历史的界限,而从普世的高度、生物的层面来关注人与土地相互依存的关系。
园艺的理念同人类生存相联系,同人类与土地互惠的理念相联系。迈克尔·K决定留下来伺候土地,而不去参加游击队叛军,因为他意识到园艺的重要性:必须有人留在后方,使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继续存在。一旦这根线断了,大地就会变得坚硬,就会忘掉她的孩子们。K找到第一颗种子,“他想起那正在拱出地面的南瓜种子,明天就是它们的末日了,他想到:我走后一天,它们就会枯萎。再过一天,它们就会干死了。……有一条温情的线,从他这里延伸到那块水坝旁边的土地。……”[1]81。
这根线就是人类与土地的互惠关系。大多数的人都忽视了人与自然的这根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毁损土地。叛军游击队在水坝旁安营扎寨,毁掉了K辛苦培养的秧苗,还浪费掉了K储存的水,把水放到了田里。与游击队的浪费行为相反,K把水看做是上天赐予大地的宝物。“把从大地中流出的水储存起来,成了K最大的愿望,他只用水泵抽取他的园子需要的水,…… 他不知道地下水如何自我循环重新变得盈满,但是他知道挥霍和浪费绝无好处。他无法想象什么潜伏在他的脚下,是一个湖泊还是一股流泉,是一个辽阔的地下海还是深得无底的池塘。每一次他松开制动器,那个风车的轮子转起来,水就流出来。这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奇迹。”[1]7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K对自然的态度已经是宗教式的虔诚,他把大地的供给看做是奇迹。他认识到无论是土地里流淌出的水还是生长的植物,都是与大地母亲相关联的东西,是生命的源泉,人类应该珍视大地的恩赐。库切似乎在暗示:人类的意义不在于与自然的分离,而在于与自然的联系,尽管战争给地球带来大规模的破坏,但人类的冷漠会给它带来更大的破坏。园艺师迈克尔·K从与人类历史逐渐疏离到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过程是从被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的过程。K对自由的争取不是表现在对权力的争夺,而是表现在对权力的让渡。我们看到的K不是翻倒在“历史的锅炉”中,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一个“在改变历史的进程中,绝不比一颗沙砾有更多的奢望”的人[1]185。K并不把这片土地耕植成一个大农场,而是只培育了一小块地,以供他基本的生存之需,断然拒绝现行的秩序中生产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机制。K不想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希望被遗忘被忽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世界里,K独自一人,用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着自己作为园艺师的生活故事。他兜里的种子、他种植的庄稼都在叙说着他的故事,换而言之,他的故事不是通过语言而建构起来,而是由事物真实地呈现出来。尽管他不能融入他人的叙述之中,却能轻易地同自然融为一体。随着自然界的节奏和现象,他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存在状态之中。
迈克尔·K一无所求,无所期待,园艺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是它与生命相联系。他把自己降为如动物般的生命存在,因而逃离战争的摧残、社会的压迫,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土地的角度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感知自我。K坚信人与土地之间是互惠的关系,这个信念使得他生存下来,他口袋中的种子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在播种这些种子时,K完成了生存的艺术。
南非反抗种族隔离的斗士戈迪默这样评价这部小说的园艺主题:“在所有的信条与道德之外,这个艺术工作说明,只有一个信念:使土地保持活力,唯一的拯救来自于土地。”[12]尽管这部小说是对南非黑人所遭遇的痛苦与非人的境遇的描写,但小说开放性的结尾也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在小说梦一般的结尾,在K想象的飞机上,暗示出现实生存的另一个出路,另一种选择,昭示着自由的来临。库切在用K与自然的合而为一暗示我们只有放弃那种基于主体性原则之上的传统理性,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 库切 J M.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M]. 邹海仑,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 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 盛宁,韩敏中,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2.
[3] Coetzee J M. Foe [M]. New York: Penguin,1986.
[4] Marais M. The Hermeneutics of Empire: Coetzee's Post-colonial Metafiction[M]∥Huggan G,Watson 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London:Macmillan,1996.
[5] 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张万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4.
[6] Penner D. Countries of the Mind: The Fiction of J.M. Coetzee[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9:26.
[7] Coetzee J M. The Novel Today[J]. Upstream,1988(6):2-5.
[8] Head D. J. M. Coetze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98.
[9] Parry B. Speech and Silence in the Fictions of J.M. Coetzee[M]∥Huggan G,Watson 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London:Macmillan,1996:44.
[10] Attwell D. J. 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5-26.
[11] Said W E. 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246.
[12] Gordimer D. The Idea of Gardening[J]. New York:Review of Books,1984(3):6.